外公的葬礼

在漯河西站的出站口,我見到父親。他走路慢悠悠的,什麽都不著急,從口袋裏翻出了火車票,通過閘道。我同他正式碰面,很快鉆進了姨夫的面包車裏。姨夫說,母親在家裏準備炒菜,等我們回家,不需要在外面吃了。
(那是2019年12月。我沒有想到的是,很久之後,我才能回到武汉,再一次見到我的父母。幾天後,我和他們分別時,是一個明媚的晴天,在河裏,有人在遊泳,有一種春天的感覺。)
天早就黑了,我第一次抵達這個高鐵站,它四周空空的,有六年我沒有來這裏了。實際上,漯河同我無關,面包車要開往八十公裏外的一個村子。姨夫說,大概四十分鐘就到了,不知道為什麽,我們花了兩個小時。
我沒有想到媽媽會準備這麽盛豐的菜,只是為了我和父親。她喜歡服侍他人,也就是我和他的丈夫。她特意蒸了米飯,「只有你二姨家,有電飯煲,她家的媳婦是......「
媽媽為父親又一次加熱了紅燒雞肉,父親說,豆腐就不需要加熱了。
.....................
在前一天,在北京周末的客廳裏,我又一次收到了媽媽輕描淡寫地告知:「兒子」。我問「怎麽啦?」 半小時後,她回復:「你姥爺走了,和你說下。」
突如其來,我覺得非常的難過,趕快回到房間裏,躺了一會兒。我又重新的站了起來,出門騎上電動車,因為電影要開始了。片中講的一個比利時出生與長大的十五歲男孩,因為哥哥的聖戰而死,他想要成為「真正的」穆斯林。在路上,我想到厄普代克 寫的小說《恐怖分子》。說實話,我很迷思一種瘋狂的、宗教性的事物,可惜它們是邁向毀滅的嚴肅。我只是被其中的嚴肅所吸引。
我想著要如何向公司請假,我從中午一直想到了晚上,這讓我有些痛苦,懷疑自己有回避性人格。我一點都不想請假,因为不想告知我親人的離世。說到底,我不想輕易和人又產生某種親密性連結的可能。哪怕,對方不過只是說句寬慰的話。
早上,我又一次醒來,找不到自己的耳機,也一直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證。我很不喜歡身份證,我們好像必須要互相認識。最終,我又騎上電動車來到朝陽公園,它可以更方便到達北京西站。我隨身帶了本小書,處理工作用的蘋果電腦,還有三個免於饑餓的橙子。
我為外公感到可惜,他是一個非常沈默的人,個子很矮,我幾乎從來沒有和他講過話。他只是在一旁呆呆地閉著嘴巴,眼神也無法猜出他這個人在想什麽,他也許不抱什麽希望了,一輩子也沒有抱過太多希望,沒有決定過什麽,只是一旁觀看。那麽,我的外公就不過是一株野草吧,太多的農村老人都只是一株野草而已。唯一不同的是,其他男人会叫嚷,打罵老婆,在村口坐著閑聊,在成為野草之前,他們做出了乏味、無解,接近於無聲的發泄。我的外公,在我看來,只是木訥的人。讓我們無法通過他的內心,而是他的處境才能體會到他的痛苦。
好幾年前,我就沒有見過他,這一年多來,他住在漯河市的一個養老院。我和媽媽說,空閑的時候我們可以去看看他。媽媽告訴我,她太忙了,「你也不能自己去,因為沒有公交可以到,特別的麻煩」。我的舅舅是一個瘋子,他偶爾會從村子裏去養老院。前一段時間,他又一次把自己父親踢成重傷。所以,外公就死在了醫院了。在他進入太平間後,我才從媽媽的讯息裏,得知了他的離世。
在外公的彌留之際,舅舅在病房裏叫嚷:「趙子輝呢?趙子輝呢?他人在哪裏?」(我父親的名字)。這些是我媽媽同親戚談話時,我在旁边聽到的,她說:「他發瘋的時候,可會說話了。那幾天,沒人敢惹他,看他神智不清的。他突然說話了, 「俺爹死了,要埋在家裏面了,你們才會告訴我吧?」
關於我舅舅的事情,可以過一下再說。聽到媽媽說的這些話,我陷入了小小的沈思,就是說在外公彌留的床邊,我的瘋人舅舅竟然想到了我父親的缺席。我沒有問舅舅,為什麽這麽問?這個問題很失禮,同時更重要的是,清醒時的舅舅幾乎不會講出成句的語言,他最多是點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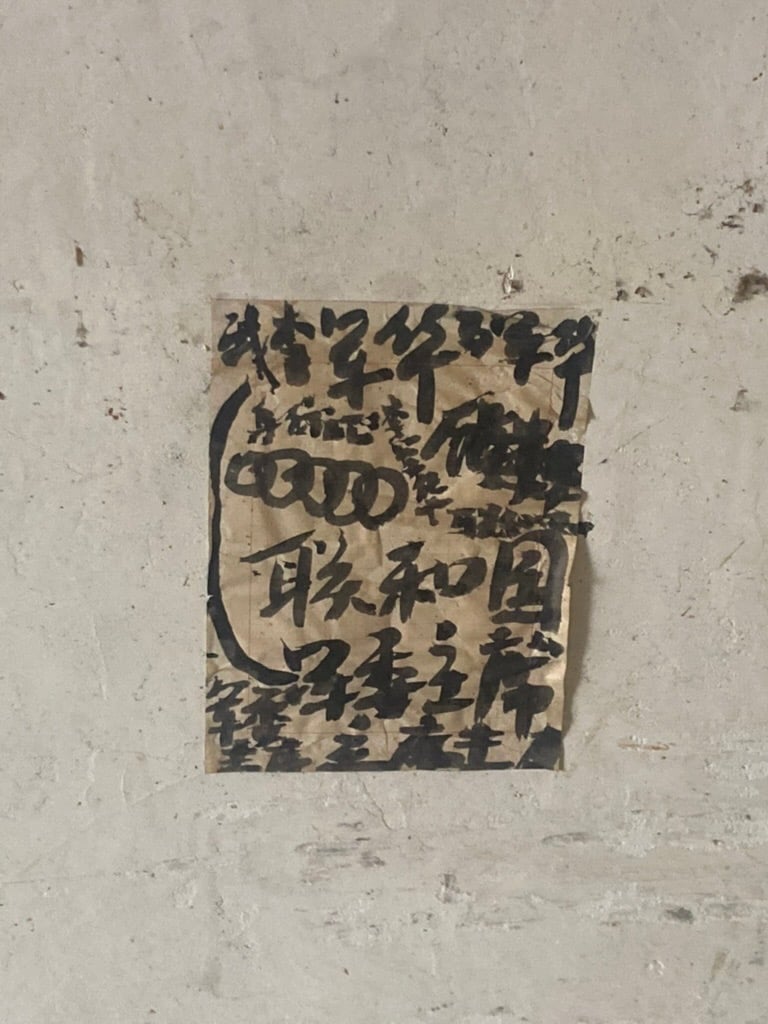



在我大約念初中的時候,農歷新年初三,我會隨媽媽來河南省的外婆家。讓我印象很深的是,外婆會給我很多錢做壓歲錢,比在城市裏的親戚給的都多,有時候比加起來的都要多。最後一次到訪,是在念大學,他們選擇在一片果園裏度過新年(離漯河市區不遠),他們給人看管果園,舅舅有時會從村子裏過來找他們。
比起外公,外婆是個強勢的人,很大程度說,她讓舅舅的老婆跳井自殺了,為此舅舅才變瘋的,變得無比怨恨母親的,變得會虐待母親的,讓外婆後半生變得痛苦而緘默的。在我快十五歲的時候,又一次回到河南省,見到了外婆,她給了我很多錢。以後每次到來,她同樣如此。但母親不來,我也不會去了,在這之後的五年時間,她終於也去世。
我沒有見過她最後一面,包括她的葬禮。
(母親是養子)(這讓我覺得血緣和親戚並不是什麽了不起的東西,而是我們所共同度過的時間。對嗎?我的瘋人舅舅。)
在過去,我就問過我媽媽,為什麽外婆會給我這麽多錢,媽媽說因為外婆喜歡我,這說不通,可以說我和外婆形如陌生人,唯一的紐帶只有我的媽媽。媽媽又說,因為我是男孩,這也說不通,因為她給另一個外孫的壓歲錢,只有幾十塊。媽媽又說,因為你長大了,你也是城裏人,你外婆希望你能經常看她。
在火車上,我又一次再想這個問題。我覺得外婆很驕傲自己的女兒,嫁進了大城市,同時她又覺得我的媽媽離開了她,以及媽媽並沒有真正地成為城市人。那麽我的存在,是最好的證明,她的後代已經融入了新的城市。但每到新年,她的女兒幾乎很少去農村,這肯定也有“婆家”的原因。外婆給我那麽多壓歲錢,為了不希望被我奶奶「輕看」,也是通過這個方式,想讓媽媽可以常看她。
直到,在我外婆病倒在家,進入彌留之際,最終的葬禮。她都沒有見到我的到場,我也許是她女兒已经進入城市的證明。但她沒有看到我的在場。我的外婆失敗了,在春節前她要和外公外出打短工籌得壓歲錢的辛勞,打了一場空。
當我想到瘋人舅舅,嘟嚷道:「趙子輝怎麽沒來?「,我又一次想到了這些。
END
此作品获 Nomad Matters 游牧者计划支持。
01.外婆,阿嬷
02.外公的葬礼
游牧者计划:陌生的河南:前往小鎮、工地、鄉村之旅
感谢阅读。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