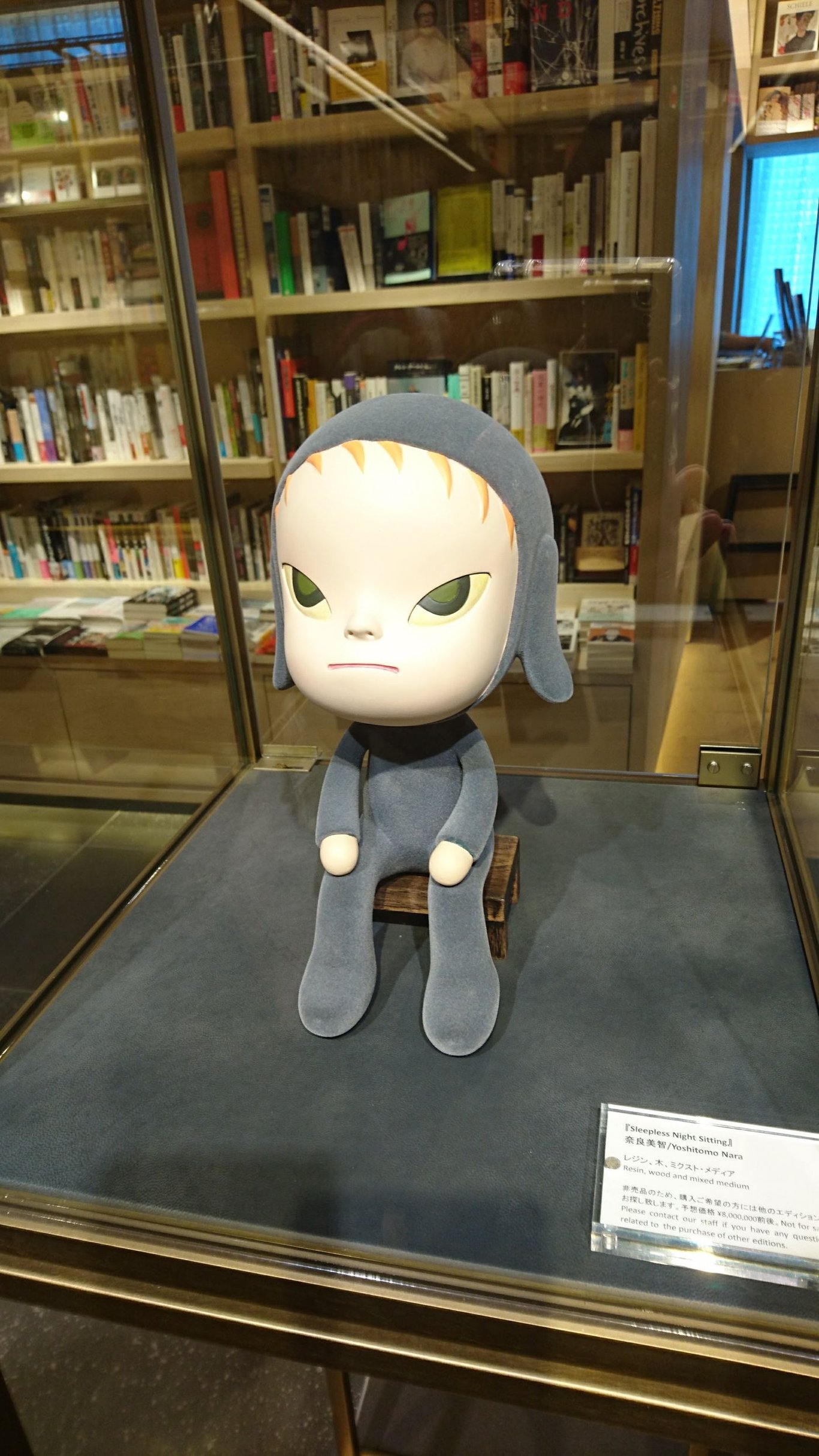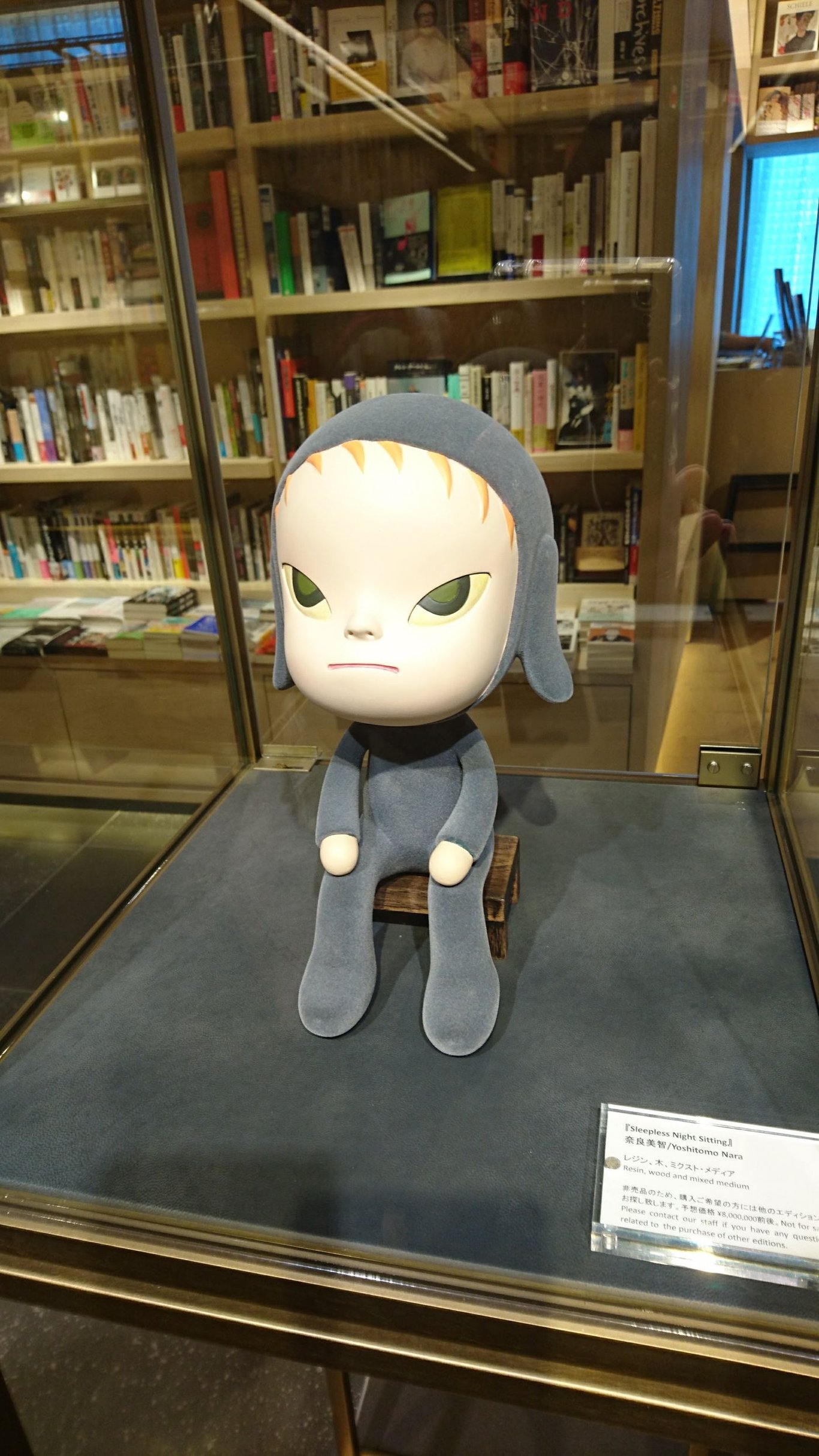外婆,阿嬷
今年三月初,清明節,我和媽媽在河南鄉村呆了好幾天。距離,我上一次,來到這裏,是2020年12月。這是我第一次,在這裏呆這麽久。
一天下午,我問媽媽,如何看待自己被遺棄的經歷。媽媽,是過繼給外婆的。她的生父母,是外婆的親姐姐。外婆家,媽媽是老大,還有她的妹妹,她的弟弟。(我的小姨,我的舅舅)。在生父母這邊,我媽媽排行老三,兩個姐姐,一個弟弟。那幾天,我們就住在,她的大姐家。
對於這個問題,媽媽並不想多做回答。
外婆也去世了好幾年。
(至於,她親生母親什麽時候去世的,我不了解,也從沒有問過。)

2019年,農歷春節假期過後,我乘動車來到上海,開始一年新的工作。沒過幾天,我在辦公室裏,收到了媽媽的微信:「你姥姥走了!18號出殯」
這消息多少讓我舉棋不定,如果要去參加葬禮的話,得坐十幾個小時火車回漯河,還得向老板請假。去漯河,最方便的方法是經由我家武漢中轉。但我剛從武漢離開,又回一趟顯得多余。我媽媽微信告訴我,「你就不過來了」、「遠」、「麻煩」,盡管在她告訴我外婆去世前,她問我:「這幾天休息嗎?」
我已經四年多沒有見過外婆,她在北方的村子裏,死前幾年還去外面小城市打過臨工。在國慶要回家的時候,我媽媽問我,「想不想看下你姥姥」。那次微信對話中,我才得知外婆得了癡呆癥,半身不遂家裏躺了半年。
我詢問了具體病情,她回答:「剛開始不知道她有那麽嚴重,在說我一直在忙,回家看她就不能走路了。去大醫院也沒有那麽多錢,她沒有醫保,她不讓我帶她去。」 「在家小醫院看了,也用不了多少錢。」 「早就大小便失禁」 「看能不能熬到過年」「我沒辦法照顧她」 「現在只有多給她買點她喜歡吃的!我只能做到這點了」我不知道說什麽,只是回復:「你不要太難過,很多事情也都是命運。」
在這些對話前,我媽媽第二次問我,「問你想不想看下她」。我說,「可以啊。」 這不是真的想法,過了幾分鐘後,「我其實還好」 「因為感覺我無法做什麽」 照片中,我的外婆睡在沒有席夢思的床上,蓋著帶鮮花的綠顏色被子,她微張著嘴,滿是皺紋,農村老人的黑皮膚。這個磚瓦房很簡陋,到了冬天很冷,因為沒有暖氣。
最後,我告訴媽媽,上班地方離上海華山醫院很近,可以問問這樣的病該吃什麽藥。她告訴我這些沒有用的。我甚至在支付寶上,找到了對應科室預約了一名教授醫生。後來幾天,我一直沒有去,最終也沒有去。
1.
媽媽問我想不想要去看外婆,可能是想給我一個機會,怕我留下遺憾。現在想來,我確實覺得這是一個遺憾,是生命中留有縫隙的遺憾,一種委屈,一種自我。
我覺得我的外婆很可憐,她只參與她後代(也就是我)生命中很小的一段。在我少年前,記事起,我只回過一次河南。那是個夏天,陽光明媚,暴雨過後,會有成排的蜻蜓經過院子,輕輕用手就能捉到一只,其中一個舅舅還是追鳥能手,他向我展示抓到的野鳥,雞能撲哧地飛到樹上,一口井很深。我趴著往裏看,心裏凝註,生怕被困進了裏面。大人們,在一旁說,有個女人就淹死在了井裏(後來我才知道那個人,就是我親舅舅的妻子,最後舅舅瘋了,後來一直折磨我的外婆)。那個時候我五歲多,但上面說的我都記得,不是現在追憶或想象而來。
但我不太記得外婆,除了我從家裏出門在院子外面玩,總是弄丟了火腿腸。發現時,又重新回屋子裏,找大人要。村民們都在笑話我。現在想來,不厭其煩給我火腿腸的人,是我的外婆。她可能是一個吝嗇的人,但她沒有太在意。不過外婆不知道的是,我當時根本不可能會吃便宜的雙匯火腿腸,「餵狗吃的」,武漢的街坊都這麽認為。
那趟去河南,除了我和媽媽,還有我的父親,奶奶,和奶奶從小養到大的堂姐。從微妙的變化中,我感覺奶奶對這裏和外婆不太滿意,這也是她第一次到河南,她覺得招待的食物太差了,外婆看起來不太衛生,沒有文化,「你姥姥很摳」,我長大後奶奶有次談到那次旅行。
那次旅行之後,我再也沒有見過外婆,一直到上初中。第一次,我媽媽帶我去河南過春節。我很詫異,為什麽幾乎沒有聯系過的外婆,她看起來非常疼愛我。順便一提,我的外婆是媽媽的養母。因此到了農村,她先帶我見了親身母親(但她只是說「見姥姥」),進了屋,我感覺久違和遠方的「外公外婆」對我很冷漠,給了我好幾百塊錢壓歲錢,就不再有任何言語。我很失望,感覺陪媽媽在外地過春節不是個好選擇。
意外之外,我們坐了一會兒,媽媽就同他們告別。我很納悶,媽媽說去見另一個「姥姥」(農村姊妹多,我以為只是另一個親戚)。不耐煩,和她往著同一個方向走,心裏想著什麽時候能結束。
瘋子舅舅來接了我們(讓我有了些記憶,因為小時候,我對這個又高又瘦的瘋子還有印象),他沖了我笑笑,穿過一條道,門前有棵小樹,眼下的房子比之前的顯得破舊又寒酸。怎麽會這麽窮,我心裏想。但我得知這就是我們要住的地方時,心裏更覺得無法接受。
這個時候,我的外婆從竈臺裏跑了出來。她瘦小、皮膚幹癟,但從眼窩、面孔等樣子,能看出外婆是一個專橫、強硬的人。她來到我們面前,手緊緊抓著我媽媽的手,眼裏布滿淚花。她松開了我媽媽的手,走到我跟前,同樣是滿是淚花的眼睛看著我。我當時心裏有些難過,或者是一種無法想出的情感,我感覺眼下的外婆和剛剛的外婆完全不一樣,那一秒,我覺得我們也是親人,便不再遺憾要住在這簡陋的平瓦房。
媽媽的村莊,在過年時也很無趣。外婆家沒有電視,我們去姨夫家裏看春晚。外婆不愛說話,只是抽煙。她不會說普通話,也不想要河南話為難我(可能只是寡言),在她家時(她幾乎從不去其他親戚家),外婆只是呆在我旁邊。我同她講話時,她安靜的聽著,用眼神看著我,像是一個聾人。
她拿出了紅包,遞給了我。當時我覺得,可能只是意思一下(至少在媽媽的村莊,人們基本只給幾十塊錢當春節紅包)。打開後,我很吃驚,裏面是一千多塊。在武漢,親戚們就相約後,各自都有小孩就不互送紅包。但姑媽常會塞我紅包,奶奶也會給小輩準備紅包,那一年春節,以及過往,都是一百塊或兩百塊。我很吃驚為什麽外婆給我那麽多錢。
同母親春節時回河南,從那年一直持續到我大學畢業。後來,我得知外婆給他後輩(一樣是外孫)春節紅包只有幾十塊,我的弟弟妹妹要比我小快十歲,小姨和姨夫都是一個鄉的,除了大姐,另外兩個孩子和他們在武漢長大。
我問了媽媽幾次為什麽?她給了我不同答案:「你外婆更疼你」 「因為你是城裏長大」 「你很少回去」
這幾乎是我和外婆僅有的交集,每年短短幾天的相處。她從沒有到過武漢,至少我沒有在武漢見過她,她也沒有拜訪過我們在武漢搬了三次的家,房子越搬越大。
2.
盡管我一直在武漢生活,二十歲前,幾乎沒有在外地呆過一周。坦白說,我一直對這個城市缺乏認同感,這有很多原因,同小時候要非常敏感有關。
沒有上幼兒園的時候,我無意得知,我出生時戶口屬於「河南漯河」,過了幾年,才隨著我媽媽的戶口一起劃進父親的城市口。當時我覺得很奇異,沒有想到我和農村沾上了關系(那時我還沒去過河南),戶口對我來說很新鮮,好像人的命運要被人為左右一樣。
媽媽在年輕的時候,算是個比較漂亮的女人(不是普通人稱「我媽媽當時很美」的那種),我父親年輕時還算很帥,但那時他已經離過婚了,他大我媽媽大概八歲。回到我媽媽,我媽媽漂亮但平日不會打扮,人的性格」大大咧咧,不在意別人開玩笑」,但那時已不像一個農村人了。由於我父親有些懶散,且日漸寡言,管教幼童的事情都在我媽媽身上。
她常拿著衣架追著我跑,有時我故意沖她喊:「回你河南,種玉米地去。」,她會很生氣,但我不以為意。我不知道為什麽當時這樣說,可能是也有鄰居偶爾這樣開玩笑,我只是模仿。也有可能,我潛意識覺得,這樣能和我媽媽劃清界限,抵消戶口給我造成的困惱。
有一次,我媽媽和鄰居訴苦,因為我年齡太小了,她對我的在場視而不見,「我兒子說什麽,要我回去種玉米,太不像話。」 這樣的時刻反而讓我今後的記憶更完整。當時我覺得,這樣做可能不多,我媽媽在這裏畢竟也是外鄉人。
這種身份造成的隔閡,其實本來可能完全不會存在,它很巧合地出現了,不僅是我幼年時敏感,最終是因為我的一段樓房生活。更多是因為奶奶,我感覺她一直對我媽媽很苛刻,她有三個兒子,我也偶爾感覺她對我父親更忽視,但最終因為他是長子,選擇住在了一起。她對另一個媳婦,表現得更尊敬,對我媽媽則很尖酸冷淡,甚至在兩個媳婦,包括我同時在場時,她也不掩飾這一點。
我很好奇哪裏出了問題。
3.
在我們家沒有徹底和奶奶家住在一起前。我一個人,離開了父母,搬去和爺爺奶奶住。那是一個七十年代建起的樓房,還算寬敞的二居室。
有一天,我的嬢嬢(武漢話,意指叔叔的老婆,姑且用阿姨指代吧)的母親,要來奶奶家拜訪。即使在武漢,兩個親家走動地並不多。阿姨是一個脾氣暴躁,愛打小算盤,指責諷刺別人。不過隨著年齡增長,現在的脾氣要好很多了。
在武漢,我們管外婆叫家家(姑且就說“家家”吧)。這個家家是上海人,她可能是下鄉,或者因為婚姻的緣故來到武漢。她戴著眼鏡,頭發很洋氣,只見過幾次面,但感覺她挺和藹。那個時候,我是一個小學生,在樓房生活非常無聊,所以我很喜歡有人做客。
小時候,我很禮貌,尤其對待大人,我和這個客人講了好幾次話,就要稱呼「家家」、「家家」。阿姨在一旁,她突然笑笑,開玩笑的說,「你看黑黑叫的幾親熱額,家家家家的,因為他沒有家家。」
聽完,我非常生氣,想要阿姨道歉,「我怎麽沒有家家,難道我家家死了嗎?」 阿姨無視我,「你本來就沒有家家。」 ,只有她母親試著安撫我,平息這個爭吵。這時奶奶過來,我慌忙說了原委,沒有想到的是,奶奶叫罵我,把我趕出了房間。阿姨用武漢話對奶奶講,「我說的是,他們那一塊又不喊家家。」
客人走後,我再提起此事時,奶奶也沒稱阿姨做的不對,只是怪我很不禮貌。這讓我多少對事情的看法持有一些失望。從我童年開始和奶奶一起生活後,一直到奶奶在我十八歲去世。奶奶對我並不算很友好,媽媽帶我出去玩,回到家裏時,奶奶的臉總是陰沈的,有時會當面斥責幹嘛回來這麽晚。我的堂姐,是奶奶從小養到大,她對堂姐很寵愛,因為她父母離婚,叔叔是個吸毒的人,常找奶奶要錢。我不妒忌這種愛,但堂姐小時候性格跋扈,加上奶奶在家庭裏獨斷、嚴厲,父親幾乎常年出差,這種以上微妙帶來的關系偶爾就遷怒我和媽媽。
細節不需展開,無關隱私,只是影響了敘述。因為這樣的緣故,我常常會懷疑武漢的親戚會不會太壞了,同時我同母親的親戚也無接觸。在初三時,外公和瘋子舅舅來了武漢,試圖幫父親在城郊開的小工廠打工,賺點錢,媽媽也在那幫忙,幾乎不回家裏。那個時候我稍微獨立了些,碰到周末,就會去城郊找父母。
我也碰到了外公,他很矮,不同於我外婆的好鬥頑強(她逼死了媳婦,最終跳井),外公看起來老實巴交的,是個沒什麽辦法的人。很快,他們離開了武漢,因為舅舅發瘋時那媽媽為難,媽媽打發他們走了。(記得小學時,陪媽媽去電話亭,媽媽很傷心,她說舅舅把老家的房子一把火燒了。)
很久後,我奶奶得知,我的外公來了武漢,她怪我媽媽沒有把外公請到家裏做客。很大緯度看,奶奶是一個寬宏大量、有決斷力、對他人很好的人,但這個尺度取決於她對事情的評判。我也很想知道,我媽媽為什麽從不請外公外婆來過武漢的家。
我感受到奶奶的善意很晚才出現。十七歲時,在外面參加補習班,發現有幾個同學擁有iPod touch3,他們遞給我,但我不會玩這個新奇的電子產品。回家時,我在飯桌上稱自己也很想要,說不定能學英語。我怕拒絕,稱iPod shuffle也可以聽東西。奶奶說,MP3好像早就過時了,你去買你說的小電腦吧,她給了我快2000塊錢買touch第四代。這是她第一次特別為我買東西。奶奶畢竟聽過叔叔很多謊話,她肯定知道我不是為了學英語,或者對我能好好學習抱有僥幸,但更有可能的是,她覺得我確實很想要,而我看到有人擁有了,奶奶不喜歡後輩在外面受委屈。
這些讓我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從來我都奶奶的總體感覺不是討厭,或有恨意的,很多愉快的時光我們一起度過了,但同時她的冷淡與對媽媽的排擠,讓我將這兩種感知綜合了,這讓我對奶奶留給我的「紀念空間」越來越空和小,現在來看我奶奶,我的情感變得平庸又單薄。
我很少和外婆接觸,我都沒在書面文字中稱她為姥姥。外婆給了我很多留白,也有一些遺憾,從某個程度,外婆(不是指涉個人的加粗漢字)可能是我與世界進行共處間的一個秘密。某個時刻,我想到外婆時,我越來越懷念她。我覺得她也代表了我記事時所開始帶來的很難說明的委屈,這個委屈已經變得越來越小,不可見,但一直存在。
但我的外婆已經死了。我很唏噓她坎坷的一生,盡管我不知道前因後果,以及豐富的細節。我的外婆在河南漯河一個村莊的墳頭,現在可能長滿了荒草。我不知道我的瘋人舅舅會不會偶爾去那發呆。
END
此作品获 Nomad Matters 游牧者计划支持。近期,将更新外公、与妈妈返乡等。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