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致力于介绍人类学观点、方法与行动的平台。 我们欢迎人类学学科相关的研究、翻译、书评、访谈、应机田野调查、多媒体创作等,期待共同思考、探讨我们的现实与当下。 Email: tyingknots2020@gmail.com 微信公众号:tying_knots
164 | 世界精神健康日,让我们来谈谈care

世界精神健康联盟主席Ingrid Daniels日前宣布,2021年世界精神健康日的主题为“不平等世界中的精神健康”。人类学在精神健康议题,尤其是对“不平等”这一面向的探讨中已经建立起强大的知识谱系——从Scheper-Hughes笔下农业经济瓦解的爱尔兰乡村中困于家庭的贫穷单身汉,到Desjarlais观察到的波士顿庇护所里罹患精神疾病的无家可归者;从Biehl揭露底层精神障碍女性如何遭遇家庭、社会和公共医疗系统共同的遗弃,到Han讲述智利贫民区脆弱不堪的经济状况如何演化为家庭内的毒瘾、酗酒和暴力;结构性处境在心理层面的映射始终是人类学家的关注所在。
然而精神健康议题中的“不平等”不仅涉及族群、性别、经济、政治对苦痛体验的影响,也关系到人们对苦痛的应对,获取治疗与康复的障碍,责任的分配与承担。因此,世卫组织就今年世界精神健康日的主题发出倡议:让人人享有精神健康服务成为现实(mental health care for all: let’s make it a reality)。这里的care尽管常被医疗领域视为一项专业的服务资源,但如凯博文发人深省的语义延伸,care的“关怀”与“照护”面向维护着人性至为关键的价值,这应当是一切精神健康服务的根本目的。
精神健康的care是一个身体与心灵、地方与全球、权力与主体、药物和其他技术相互纠缠的复杂领域,有效的care需要抛弃专业主义的居高临下,进入受苦者的生活世界,民族志恰恰可以在此“作为方法”。在世界精神健康日到来之际,结绳志准备了一份短小的主题书单,让我们暂时把知识建构的路径放在一旁,借助人类学研究近十年来对精神健康关怀/照护/疗愈问题富有建设性的探索,从系统与劳动、临床与日常、常规与非常规角度来谈谈精神健康的care何以失败、何以可能。
鉴于英文研究中care一词的语义多样性,与结绳志多物种关怀系列的翻译思路一致,本篇文章不刻意统一“care”的中译,而是依据语境来选择更符合中文理解的词汇:这些文章中,care依其具体含义可能被译为照护、照料、关心、保护、保健、服务等。在转译这些“关怀”故事的同时,我们希望能保存差异、保留“麻烦”,激发多语言、跨学科、跨地域的思考。
编写 / 安孟竹
01. 日常伦理与关怀体制
《日常伦理:来自社区精神医学前沿的声音》
保罗·布罗温,加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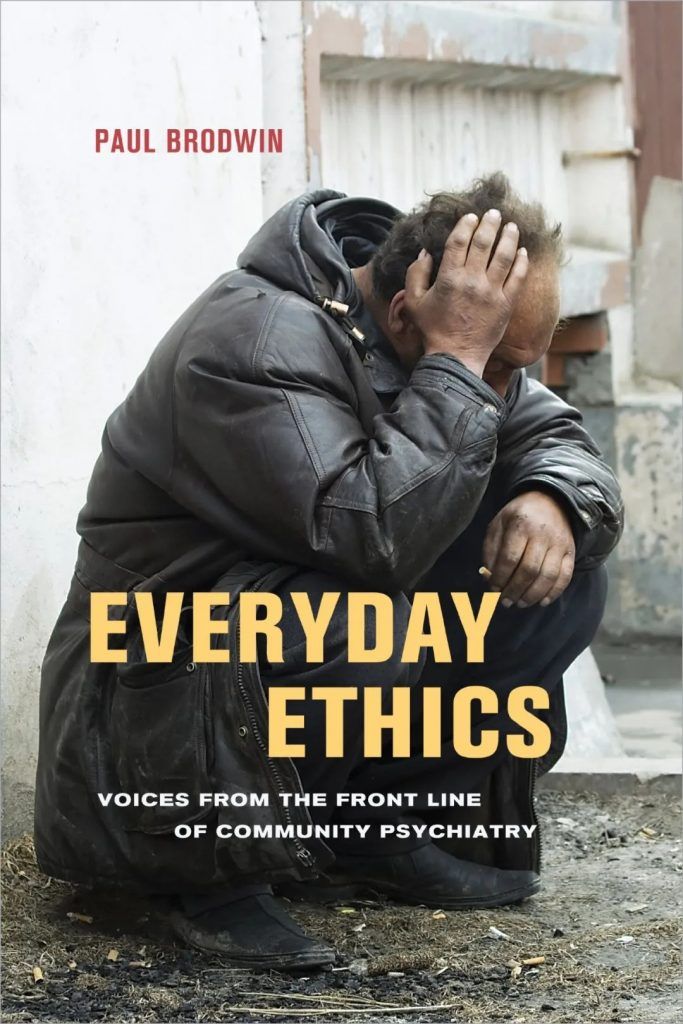
在西方精神医学去机构化的历史中,从收容所、寄宿之家,到中途宿舍、居家康复,社区精神健康服务逐渐崛起。在北美,积极性社区治疗(Assertive Community Treatment,ACT)被誉为最受认可的、有循证基础的社区精神健康服务模式。然而在这一模式的最基层,个案管理者们的工作体验却以一种“日常伦理”的方式挑战着ACT的规范性伦理准则。保罗·布罗温(Paul Brodwin)的田野调查聚焦于美国ACT一线工作者的遭遇和挣扎。他发现,在生物医学模式的主导下,尽管ACT一线工作者在与精神障碍个案接触交往的过程中需要并获得了一种策略性、情景化的知识,但他们对诊断、用药和住院的决定却没有丝毫的权力;尽管他们希望通过多种方式来促进个案的精神健康,医学专家却要求他们协助保障药物治疗的依从性、对障碍者进行基于“大脑神经化学”的病理解释。工作者们努力寻找微小的目标来动员个案的参与,以保证ACT模式获得资助,却难以在个案的能力范围内不急不缓地与他们一起工作。他们忙于医疗补助的审计、为服务机构和行政需要来撰写治疗计划,却常常遭遇个案本人对服务的拒绝。
布罗温在书中描述了ACT工作者如何在履行系统使命的过程中努力将抽象的准则落实成现实的行动(尤见在涉及个案财务管理与监督的章节)。他们的“日常伦理”被描述为仁慈、短暂、且容易被实践中的突发事件所淹没。由于生物医学以“大脑受损”为前提的伦理推断否定了患者的道德人格,因而也没有给ACT工作者在“手册”之外对个案处境的想象性伦理留出空间。然而这样的简化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个案一再地作出与自身利益相悖的举动?他们对服务的“拒绝”真的只是神经化学造成的缺乏洞察力或不尊重医学真理的结果吗?这恰恰是日常伦理的与规范性伦理的张力所在。在等级制度之下,一线工作者的日常实践极易走向官僚化,遵循着从大数据中提取的行动手册,像机器一样对他人的行动作出反应。而 ACT工作者的痛苦与挣扎则提醒我们,如果不去呈现和体会“做”的复杂性,一线工作者就只是在复制系统的意识形态;而日常伦理则迫使我们用不断的关切、反思与讨论来抵制一切形式还原论。
《无关生命的生命:在加拿大北极地区想象关怀》
丽莎·斯蒂文森,加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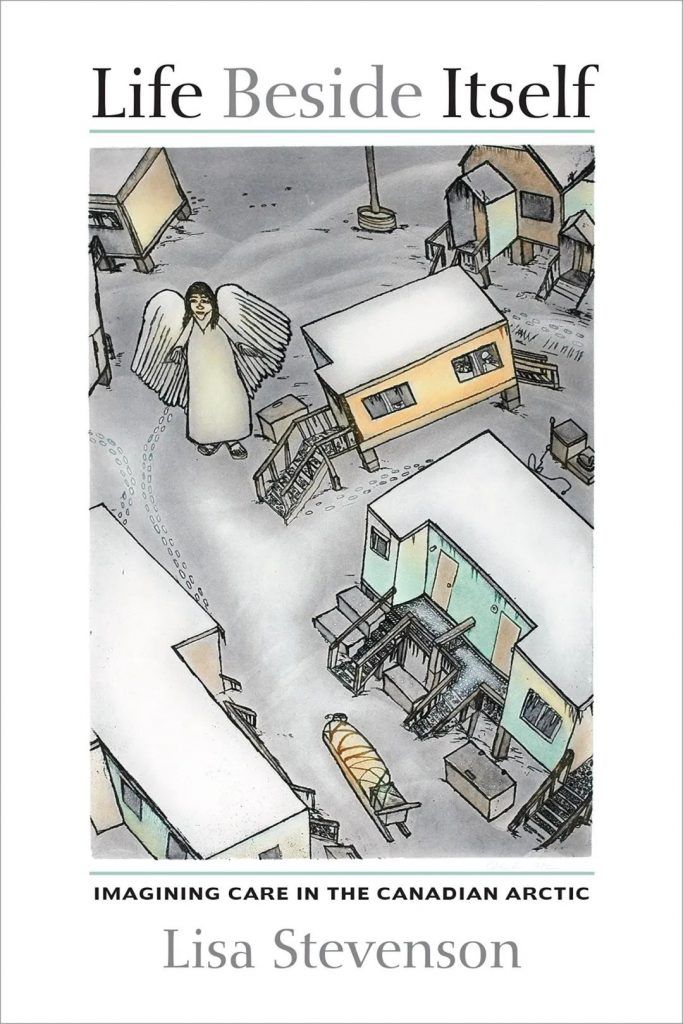
在工业化国家,对精神健康的关怀常常被纳入一种系统性的治理逻辑中,对精神健康问题的“识别”也常常是权力作用的结果。丽莎·斯蒂文森(Lisa·Stevenson)的田野地点位于加拿大北部称为努纳武特地区的因纽特人社群中,在这篇土地上一个关乎精神健康的持久悖论在于:为何国家投入了巨大的照护资源,该地因纽特青年的自杀率依然居高不下。斯蒂文森从国家在当地的官僚主义政策追溯至加拿大“福利殖民族主义”的历史,她将国家投入当地精神健康的关怀体制称为“匿名关怀”(anonymous care),这种关怀体制基于一种机械化、官僚化的行事原则,与因纽特借由“命名”而延续逝者生命的传统截然相反,用作者的话说,在这种制度中“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活着”。这一关怀体制可以追溯至殖民时代罹患肺结核的因纽特人被安置到南方疗养院、并在当地被匿名埋葬的历史。斯蒂文森揭示了历史上的结核病与当前自杀流行的相似之处,即国家与医疗专家关心的是因纽特人作为加拿大公民的“活”,但对因纽特人自己的生命关切、以及他们想要如何活着(或死去)并没有足够的关怀。实际上,在全球的自杀预防项目中普遍存在着这种匿名关怀的逻辑,这些项目首先试图定义所谓“高危人群”,并提供一套让志愿者远程应对“自杀危机”的协议,而不必直面他人存在的焦虑与苦痛的特殊性。这种基于普遍人性的关怀并不需要特殊的资格、也很少受到质疑。然而它所包含的匿名性在允许照护/关怀者与被照护者获得某种自由的同时,也产生了将承受苦痛的个体转化为一个抽象“案例”(case) 的效果。更为讽刺的是,这种干预方式在呼吁有自杀倾向的青年求生的同时,也不断地将他们询唤到一个“有问题”的主体位置上,去确认他们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因纽特青年们要如何在另一种生活制度中重建自我?斯蒂文森回到后殖民处境下因纽特青年的时间感之中,提出了所谓“有自杀倾向”和“不想过(他们要面对的那种生活)”之间的重要区别——对他们而言,自杀不仅是对没有希望的未来的反应,同时也是“跃入另一种存于时间中(being in time)的方式”。而这种对存在救赎的想象,正是目前精神医学自杀预防方法中所普遍缺乏的。
02. 另类的表达与介入
《翻译中的移民:当代意大利的关怀与差异逻辑》
克里斯蒂安娜·乔达诺,加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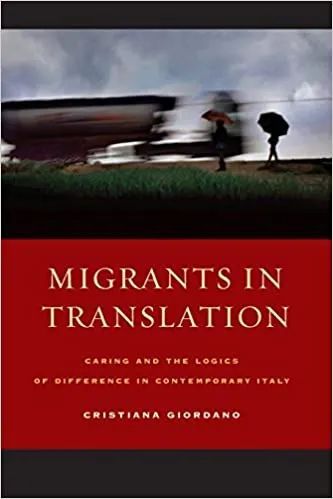
在意大利,一群来自尼日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沦为都市性工作者的移民女性被国家识别为“人口贩卖受害者”。教会、警察与公共健康部门一起被纳入了针对她们的精神疗愈和救赎计划。克里斯蒂安娜·乔达诺(CristianaGiordano)的田野主要围绕都灵西北部一家民族精神医学中心展开,描述了这家以哲学家、革命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之名命名的民族精神医学机构如何将政治介入与临床干预相结合,服务于移民女性的精神健康。在医学人类学历史上,民族精神医学(ethnopsychiatry)曾被批判为一套静态的文化观,试图通过去政治化的透镜来解释他者的苦痛。乔达诺则在本书中对民族精神医学的潜质提出了全新的看法。作者发现,民族精神医学的方法强调“文化能力”的作用,这种文化能力有助于“承认差异”(acknowledge difference) 而不仅像生物精神医学那样去“识别差异”(recognize difference)——“识别”对移民而言是一个异化的过程,而“承认”则给一种打破现存秩序的新的“生活政治”留出了空间。在作者所在的中心,医生关注移民女性面对的 “存在性危机”,即失去与社会、世界建立象征性联系的能力;在这一语境下,将“文化”本质化的做法——比如鼓励非洲移民去看非洲艺术展作为一种疗愈方式——只是民族精神医学试图重建这种联系的策略。同时,“文化”可以在临床相遇中打开一个空间,精神症状的类别在这里得以消解,一种不同于“医疗权威”与“病人”之间的倾听得以发生。正是在这样的场景中,那种将移民视为一个“到达——融入——成为新公民主体”的线性过程的观点,以及国家将“被贩卖、进入性产业”视为这些移民女性精神苦痛之核心所在的看法,都遭遇了质疑和挑战。在民族精神医学的治疗中浮现出的是,这些女性因种种与“贩卖”无关的原因而受苦——她们可能因确诊HIV而不安,因在意大利没有亲友而孤独,或在与寄养的孩子见面时不允许说母语而痛苦。这样的治疗叙事揭示出后殖民时代塑造移民苦痛经验的结构性不平等与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从而具有政治批判的潜质。当国家和生物医学以帮移民患者从“病态”转为“常态”作为目标,与意大利左派思想有着深刻历史关联的民族精神医学则呼吁一种“关怀”(care)而非“治疗”(healing)的做法,这也对国家如何应对移民问题中的矛盾带来了更广泛的启示。
《超常境况:精神疾病中的文化与体验》,
珍妮丝·詹金斯,加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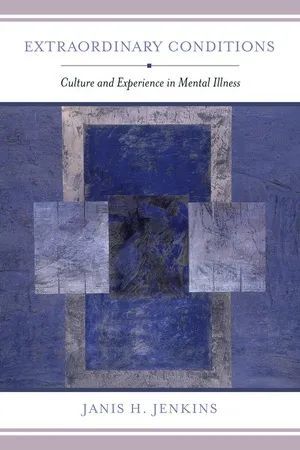
身兼精神医学家与人类学家双重身份的珍妮丝·詹金斯(Janis·Jenkins)用“超常境况”(extraordinary condition)一词取代了“精神障碍/疾病/反常”的通用表达。因为在她看来,一方面,那些在文化上被定义为精神疾病的状况实际上也包含着由社会条件、历史过程所造就的逆境,此外,“超常境况”一词也隐含这样的意义,即在受苦者生命经验的边缘以及他们和身边人应对精神苦痛的斗争中,存在着理解“做人”意味着什么的可能。詹金斯强调,当“大脑”和神经科学日益成为定义、应对精神磨难的基础,在受苦者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充斥着大量未被充分理解的苦痛,这些苦痛关乎一个人如何面向自我、他人与世界,也是作为照顾者的家人在亲密空间中面对的情感挑战。书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第二部分。詹金斯在这里将那些被标注为精神障碍的经验视为被社会、经济与政治所焚毁的生活现实在人们心理层面的映照。作者反思了 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这类诊断标签存在的问题;与文化精神医学的旧有路径不同,她用以挑战西方精神医学话语的并不是被“地方文化”所塑造的独特具身体验,而是一种更具政治经济色彩的脆弱处境(precarity):如波士顿萨尔瓦多难民女性承受的隐秘而断裂的战争创伤,以及毒品泛滥、家暴肆虐的新墨西哥州有过家庭遗弃经验的青少年们——他们的脆弱处境不仅源于自身所处的生活条件,也会在医疗系统中得到再生产。针对这样的情况,精神科开具的诊断标签往往是令人困惑的,它未能捕捉到人们所承受的精神痛苦的紧迫与普遍,而是聚焦于被生理性唤起的急性发作或是持久连贯的痛苦特征。实际上,现实中的人不太可能呈现出连贯不变的临床症状,反而会持续针对自身的状况采取策略、进行斗争。为此,詹金斯呼吁提出一种更为普遍的创伤类别来理解精神痛苦承受者的脆弱处境,让那些造成遗弃、忽视、创伤的更深层结构性条件浮现出来。
03. 照护的“伙伴”与“家人”
《未被遗忘:印度失智症照护中的爱与文化》
比安卡·布里杰纳斯,伯明翰出版社,201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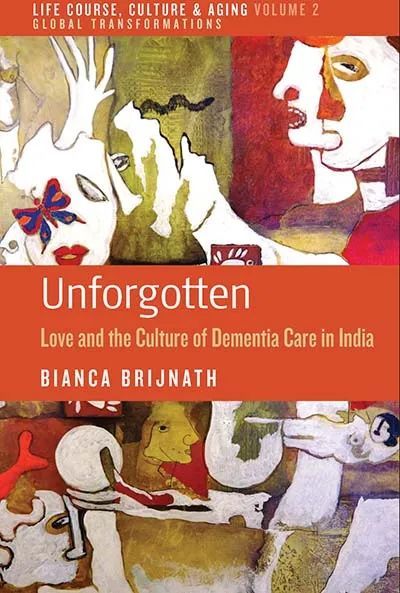
提起失智症照护,人类学领域最为耳熟能详的应当是Mclean在美国疗养院中对失智老人与疗养院护工的民族志研究,然而作为照护者的家人又在经历着什么呢?比安卡·布里杰纳斯(Bianca Brijnath)的这本书分享了20多个印度家庭的失智照护故事,在这些家庭里,女儿、妻子、儿媳扮演了主要的家庭照顾者角色,她们以做Seva(对老年人无私的尊重与侍奉)的方式竭力维护失智亲人的尊严、人格与生活质量,而她们自身作为照顾者的日常挣扎、希望与恐惧则嵌入在更广阔的全球化、人口结构转型和医疗范式变迁的背景中。从症状浮现的“看与被看”到患者最终离世,陪伴在失智者身边的家庭照护者也经历了一段完整的旅程:她们为亲人周旋在多元医疗的丛林与生活世界之间,体验着失智症照护的宏观经济与伦理责任、亲密关系之间的裂隙,同时也以种种“维护正常”的做法来应对蔓延到自身的污名与孤独感。布里杰纳斯的写作意图之一是唤起读者与照护者相似的感官体验,让读者想象照护者日常面对食物、排泄物、腐朽身体时的感受。作者捕捉到,这种“带走不需要的、给予想要的”物质交换过程正是日常照护的核心,药物也是这种交换的一部分,需要被编排进照护的逻辑之中。对家人而言,药是希望的象征,是规训的工具,也是迷茫与自我怀疑的来源。在确保失智者服用各种精神药物的过程中,家人也困惑于病患的表现与痛苦到底是因为失智症本身、还是因为药物的副作用。通过药物改善病情的希望通常会随着时间而淡化,逐渐为亲人减药、停药标志着照护者对不可回避的死亡的接受。尽管在印度的家庭中,亲属关系和代际互惠的强大纽带继续扮演着构建失智者日常世界的重要力量,但作者对家庭照护者的牺牲、痛苦与脆弱感的复杂体验的呈现已经表明,Seva的意涵早已超越了印度社会对该词的传统理解。
《灵魂的残障:一部当代日本精神分裂与精神疾病的民族志》
中村凯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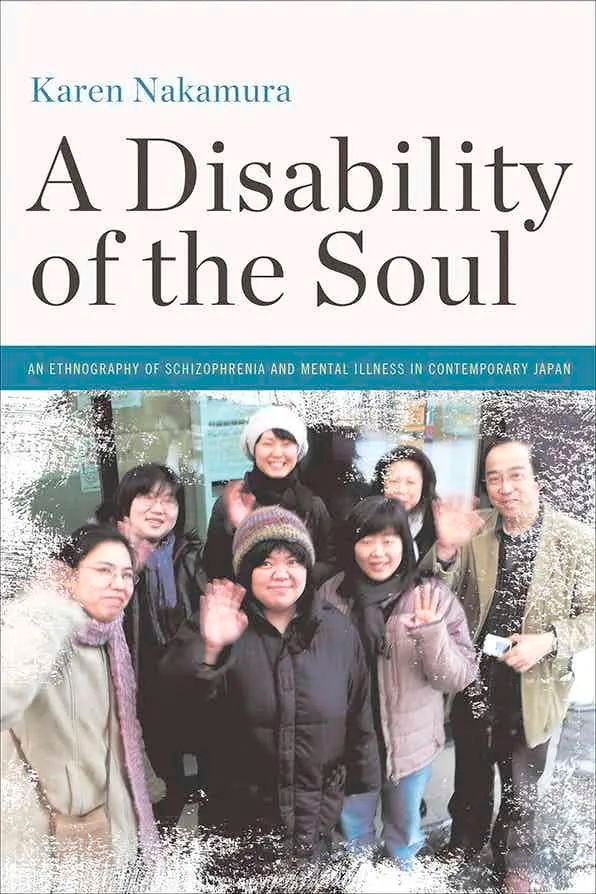
社会融合还是世外桃源?这是精神障碍康复领域僵持不下的争论。中村凯伦(Karen Nakamura)以民族志书写与影像相结合的方式描绘了日本北部一个专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提供服务、名为伯特利(Bethel)的小型独立生活社群。不同于人类学家笔下通常作为再生产社会苦痛空间的机构,伯特利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得到接纳、理解和照护的地方。它成立于日本特定的生命政治背景之下——二战后,私营精神病院在经济刺激之下崛起,但在医院里,病患被长久地收容住院、接受大剂量的多种药物治疗,且缺乏谈话治疗的方案和建基于社区的精神健康服务。伯特利则是由一位主张精神分裂症患者“接受疾病、学会与之共处”的精神科医生发起的乌托邦式空间,强调社区成员之间以合作方式共同维持一种有价值、被赞赏的自我意识。在伯特利,社区成员可以公开地表达自己那些在医疗场景之下被视为“症状”的想法和体验,比如告诉别人自己要去见UFO,社区成员之间会彼此协助进行“自我研究”,从而了解妄想、幻听这样的“症状”对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由于成员的“自我”首先被接受,而不是被否定,药物的需求也因此减少。伯特利的工作者多为伙伴(peer),即同龄的、有相似严重精神障碍体验的人。伙伴管理的组织培养了一种呼应他人的行事能力,并使人际间的亲密联系成为可能。成员们在这里以灵活的方式、在不过度逼迫自己的情况下参与庇护式的生产活动;他们并不被期待一定要“重返社会”,而是被鼓励在伯特利内部找到一个自己的社会角色。
中村并没有掩盖社区内外的张力,她指出,尽管伯特利被设计为一个成员可以随时离开的阈限空间,但那些离开的人往往又会回来,在对伯特利归属感增强的同时,他们与外部艰难现实之间仍有难以弥合的距离。这表明,在这个世外桃源之外,成员们的选择依旧相当有限。此外,作者敏感地察觉到照护的官僚化正在毁掉伯特利:国家希望用给薪的专业持证人员取代“伙伴”工作者,用种种规范和条例约束着原本宽松自由的社区,财务管理不善的外部指控纷至沓来,社区模式开发者面临退休,无人取代。尽管作者对伯特利模式在社会变迁中的存续持悲观态度,但伯特利的日常运作依然展现了一种对精神健康照护替代性方案的有益探索:在这里,生活、医疗与照护的空间连续性,伙伴工作者的作用,地方道德世界的构建,人际联系与成就感等,都对如何帮助人们发展适合于自身的康复版本提供了启示。
04. “康复”什么?
《康复边缘:一部精神健康照护与道德能动性的民族志》
尼莉·迈尔斯,范德堡大学出版社,201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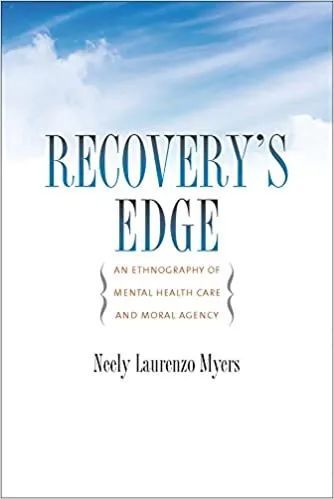
在中文语境里,康复本身总是会跟“痊愈”“治疗”这样的词发生语义混淆。实际上,精神健康领域近来兴起的“康复运动”包含全新的理念,它关乎精神障碍者个体的赋权(empowerment),关乎希望的培养,关乎打破生物精神医学的“家长主义模式”;它所设计的具体照护与服务提供都不只是为了“减轻症状”,而是为了帮助有精神痛苦的人实现更好的生活。这种实践取向超越了对精神医学知识的简单质疑,而是直指参与其中的障碍者与服务提供者“到底在改变什么”的问题。
尼莉·迈尔斯(Neely·Myers)在一家名为“地平线”的城市精神健康服务中心进行了多年的民族志研究,这家旨在提供以康复为导向(recovery-oriented)的机构将他们所服务的严重精神障碍者称为“成员”。迈尔斯参与中心员工的会议,在中心内外、抽烟和咖啡吃午餐时与“成员们”相遇,并从结构、组织、操作、临床与体验的角度探索了这种以康复为导向的服务的日常实践与困境。在书中,迈尔斯用一个个以地平线机构成员为核心的鲜活故事展现了“康复”何以成为一个关乎道德自我的问题,并揭示出“道德能动性”的修复如何成为康复的核心。这种道德感层面的挣扎、对“我能做些什么”的怀疑也挑战着机构里的服务提供者。在这个看似封闭的空间,人的具体遭遇与外部的社会处境有着持续不断的对话:试图通过就业、自我和独立的实现来塑造康复的努力常常遭遇日常暴力的阻挠,贫困、无家可归、性侵犯、谋杀与盗窃是始终伴随着康复事业的风险。迈尔斯没有回避服务中心里 “医学治疗”与同伴提供的照护服务之间存在的恒久张力:例如,同伴倡导者认为能动性意味着“成员们”的随心所欲,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放任却让中心里害虫滋生;临床医生则始终认为,过多的自主决策最终会伤害成员自身。迈尔斯对这样的张力与挣扎怀有强烈的同理心,她并没有落入医疗化批判的窠臼,或是将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简化为他制度化的社会身份(如护工、医生),她努力去呈现的是,在帮助严重精神障碍者的过程中,所谓“自主权”是个多么令人不安的问题,其中的冲突与挫败也让作者本人也感到深深的无力。这对所有关注精神健康议题的人类学研究者也是种忠告:即便在一个以“关怀”为取向的民族志项目中,研究者与报道人之间的主体间道德空间同样是脆弱的。
《饥肠辘辘:美国的进食障碍与失败的照护》
丽贝卡·莱斯特,加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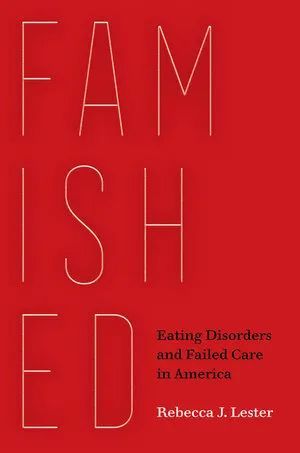
一个冷知识是,进食障碍是所有精神障碍中死亡率最高的一种。在过去,进食障碍常常被视为一个关乎欧美社会的文化与人格规范、但常常被错误地移植到其他文化中的类别。本书作者丽贝卡·莱斯特(Rebecca Lester)既是一位人类学家,同时也是有过进食障碍体验并入院治疗的病患,她的民族志工作围绕一家进食障碍治疗中心展开。莱斯特没有质疑进食障碍的本体论现实,及其病理学中包含的文化政治,让她困惑的是,尽管在美国诸多此类机构作出了种种专业上的努力,为何大多病患(书中称为客户)并未从进食障碍中康复?这种缺乏“成功康复”的情况也可以算是几乎所有精神障碍循证治疗方法在实践中的共同问题。追问治疗何以“辜负”了参与治疗的人,而不是询问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为什么没能痊愈,这个翻转至关重要。莱斯特发现,在资源导向、强调“管理”的医疗体系内,进食障碍者身体健康的危机会迫使某些干预措施成为必要,于是,患者体重的恢复、生理指标的稳定和治疗的依从性也就成为了“健康”的代名词,然而将生理性指标视为“康复”标志的观点也为各种支持服务的撤销提供了正当理由——当这些支持撤销之时,障碍者可能正在探索不同的生活方式并十分需要帮助。此外,作者发现,在寻求治疗的过程中,障碍者(常常是女性)会被置于矛盾的位置,康复的承诺与治疗的依从性一方面要求女性摄入必要的卡路里,另一方面,身体的性别话语又将她的饥饿感塑造为失控、贪婪、不道德、需要被控制的。因此,那些使障碍出现的结构性条件反而会在治疗过程的自我情绪工作、食欲和欲望的管理中得到再生产,而自我“于身存有(being in the body)”的方式则进一步沦为“病态”。而另一些无法被纳入临床治疗编码的转变却可能构成一个人疗愈的重要时刻,象征着有意义的生活变化、以及女性存在于世界的不同方式。对个人而言,混乱无序的饮食作为一种存在于世界的手段与媒介可能是有意义的,因此,“康复”更需要关注的是,所谓的“障碍”如何影响人际关系的配置、个人对自身的感觉、以及一个人与饮食相关的感受、观念与做法,而不是将解决方案聚焦于所谓的治疗可及性(即用更多的资金来保证长期的治疗)。这一去病理化的康复框架强调为病患寻找替代性的存在方式、生活的意义与目的,同时也让进食障碍的照护成为了一个超越临床场景的政治与生活命题。
Reference:
Brodwin, P. (2013). Everyday Ethics: Voices from the Front Line of Community Psychiatry.
Giordano, C. (2014). Migrants in Translation: Caring and the Logics of Difference in Contemporary Italy.
Jenkins, J. H. (2015). Extraordinary Conditions: Culture and Experience in Mental Illness.
Khan, N. (2016). Mental Disorder: Anthropological Insight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Lester, R. J. (2019). Famished: Eating Disorders and Failed Care in America.
Myers, N. L. (2015). Recovery’s Edge: An Ethnography of Mental Health Care and Moral Agency.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Nakamura, K. (2013). A Disability of the Soul: An Ethnography of Schizophrenia and Mental Illness in Contemporary Japan (Pap/DVD edi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tevenson, L. (2014). Life Beside Itself: Imagining Care in the Canadian Arctic.
最新文章(持续更新)
155. 哲学人类学 | 黑格尔与海地(上)
156. 酸的艺术:波斯视觉与物质文化中的柠檬
157. 开放获取:美国人类学协会期刊出版的未来
158. 哲学人类学 | 黑格尔与海地(下)
159. 动物农庄:垄断资本时代的动物园
160. 没有女人,你就无法理解古兰
161. 电力书单 | 一份应急充电宝
162. 结绳故事绘(2)
163. 在灭绝时期照护隼
164. 世界精神健康日,让我们来谈谈care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