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來石
關於PTSD
恢复心得
關於性侵倖存
創傷恢復筆記 情緒觸發預警 Trigger Warning: Sexual Assault and Suicidal Thoughts
关于中国户籍制度
复杂精神病患者正在慢慢找回失落的记忆,随意记述之,同时发布一些我认为有一点点值得被看见的价值的内容。
關於抑鬱症
一些恢復心得
三日書·山海塢 #3|等下!
我们的播客就叫做「等下!Wait a minute!」,因为这是最常用的插嘴用语,顺性别者的大家请等一下,你们已经说了很久了,请等一下,听听我们怎么说,听听 What we have to say.

三日書·山海塢 #2|人生與世界不過一場即興喜劇
我不认同「喜剧的内核是悲剧」,我认为喜剧的核心是释放笑的力量。当我对一件严肃的、宏大的,甚至惨痛的事情发笑,不代表我就不将这件事认真对待,只是我在用笑的力量捍卫自己的心,我不允许苦难的重压完全的掌控我,我不允许困境将我制伏在悲伤、痛苦、沉郁、恐惧、羞耻之中,我要主动地拿起幽默,消解苦难的重压,拥有片刻的轻松愉快。
三日書·山海塢 #1|Queer Stage
在中国本土,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也自然有那么多那么多个酷儿真实地在地生活着的地方,尚未有一个舞台让酷儿们得以讲出自己的生命故事,尚未有一个文化空间能够让酷儿们集聚,让讲述者来这里表演,遇见能听懂ta们的故事的观众;让渴望一刻连结的观众来到这里,看见与自己切身的故事。

北地遊記|從紅島到淮河
只觉得果然是在北方才会有嘶吼的、高昂的摇滚,才会有痛苦的信仰,才会有「直到大厦崩塌」,才会有「星河下 电子荒原」。而我们南方的摇滚乐则只唱「天色将晚 人潮渐散」,唱「寄生在这样的平原」。

短篇小說|小死亡
我是个爱女人的女人,然而我总是爱上不那么女人的女人。这个星球的巨大文化叙述里,女人是一种总是漂亮的、总是等待被得到的、总是关切的、总是在忍耐、总是在支持的生物,这样的生物性也有相当部分写进了我的文化基因里。所以我很明白,要当那样一个女人是要支付一笔不菲的代价的。

Freewrite Sep 15 2024
With them I'm free, with them I'm fearless, I'm sharp, burning, a tyrant of this life of mine, but also freezing, flowing, and incredibly soft and crispy.

七日書#5.3|親愛的哥哥
我觉得我是如此多的一个人,而仅仅是看到同样如此多的一个存在与我遥遥相对,就已足够令我慰藉,更何况他竟与我相知相爱,结为手足,这是何等的幸运,多么偶然的一次量子纠缠。
七日書#5.2|過載光束
我的孱弱与星辰的孱弱隶属同一种造化,我们在混沌里虚无地被不由分说地创生,我们振动、飞旋,囿于某一片星系中独特而复杂的引力关系,我们在公转与自转里无暇再顾其它,我们等待机缘,等待隐喻,等待蹊跷的变故,等待微妙而精巧的平衡被打破的一瞬间,然后我们被照亮,我们也许燃烧,凝成一束光,划破…
七日書#5.1|帶領一個孩子發現宇宙
我想关于人类,这就是我最喜爱的一件事,人有最纯粹的好奇,人有最纯真的发问,人有最纯朴的求知,亿万年的历史淘洗过我们这个物种,而我们正是在一句句的「有什么」、「是什么」、「为什么」里,将智慧的火种一点点传递,燃成文明的大火。正是在这一点点的可能性里,潜藏着变好的可能,潜藏着减少恨苦…

上海最后随记04|阿榕 in Shanghai
阿榕来我家小住!终于在我离开这座城市之际有了这样的机会,我快乐得想打滚。有许多读者喜欢看我与阿榕的故事,趁现在他在工作,我便把我备忘录里提到阿榕的一些随笔整理如下。

流亡集|二四年上旬的詩
最開始寫詩,是因為有話不能直說,無法直說,就只好編進隱喻裡。出於審查也好,出於文化中無處不在教人無法遁形的各類仇恨也罷,我的喉舌都在逐漸硅化,我感到我被我的母語放逐,當我向明白我的語言的人們說話,ta們不理解我在說什麼,當我向理解我在說什麼的人說話,ta們不理解我的語言。

七日書#4.7|後現代夫人
旧时代的「夫人」,总是指宴请文人雅客,留下故事传说的名媛女子,而我总觉得我仍在做这件事,只不过后现代的夫人连桌上的菜也要自己炒(这样才更酷吧),我仍宴请各式各样的朋友,ta们去各自厉害的领域做着厉害的事,或在这个阵痛的剧变的时代仍怀抱相信的事,立志要去做点发起和连结人心的事出来,…

七日書#4.6|給廣州的一封信
第六天 描述一個讓你印象最深的有關「吃」的空間,廚房、客廳、餐廳、街道都可以,說說你在那裏的經歷和體驗

我的頭像、酷兒性與同人文化
这恰恰是我想要面对世界的态度,你随时都可以毁灭我,但你无法销毁我,我将像鬼魅魍魉,永远萦绕,永远缠绵,永远掷地有声。

七日書#4.5|蝙蝠靈筆記
这一题对我而言很难写,因为在与厌食缠斗的这段时间里,每顿饭都极其难以下咽。小时候看过一本小说,里面写去世的爱人会化作没有记忆的蝙蝠来世间看你。那么就以蝙蝠灵的视角来写写对一名厌食症女性的观察日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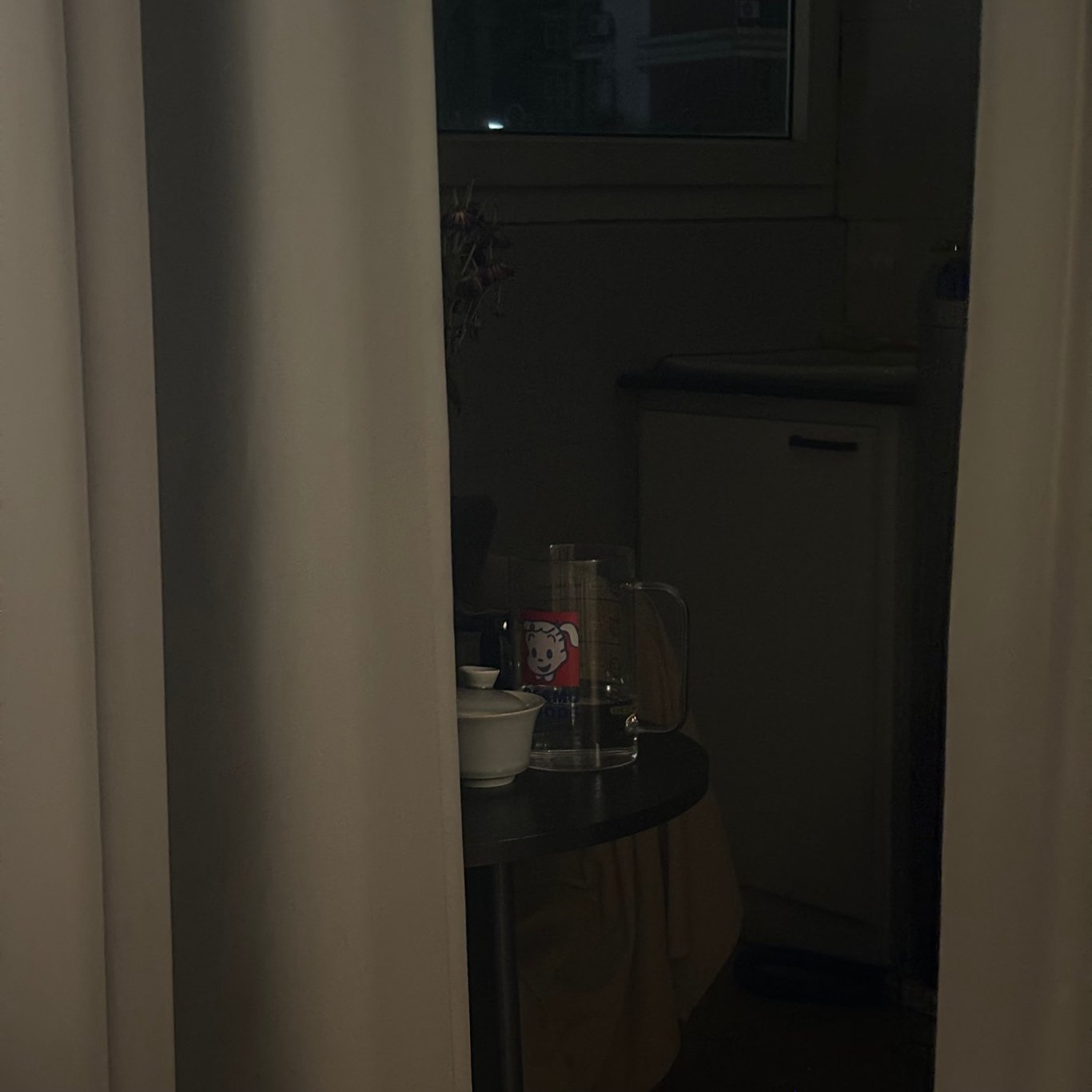
七日書#4.4|冒險者
我的双手早已经过无数次厨房的锤炼,现在它们复合了许许多多个民族的菜谱,意面、米饭、拉面、米粉、土豆沙拉、江浙菜、湘菜,这些菜谱来自妈妈和外婆,来自我喜爱的博主,来自我喜爱的餐厅,来自我喜爱的友人们,这些味道已经刻录在我的肌肉记忆里。而到了饭点,架起炉灶,我随时都能煮出我所需要的迷宫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