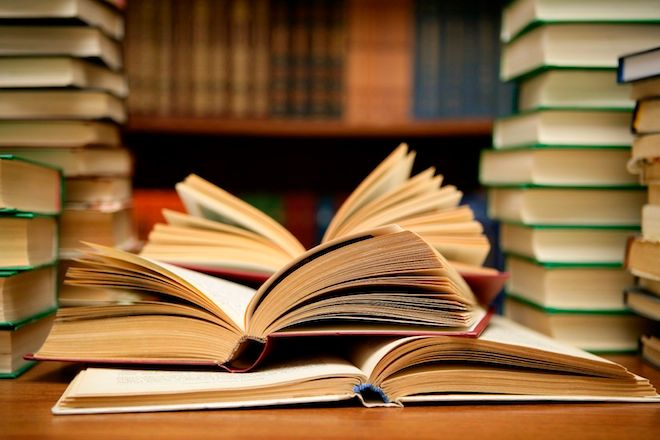花束
妳終將到來
拼圖
車窗恰容下馬尾蓬鬆的女孩 一樣黝黑但多她三分明麗: 不是她 捷運車窗 一片拼圖足以證明 頹然也慶幸 在她面前憔悴孤獨,情何以堪?打包散落一地的拼圖 下車捕捉車窗溜走的她的背影 上車轉乘 情侶拼圖自己的青春 窗戶上倒影他們的黃昏 牽手,平常不過的菜籃 更多車窗拼圖他們的 早晨、中午...

轉生
下輩子轉生為蘭

果子
關於惡果,每個人定義不同,於我不過是自作孽罷了,唯世代傳承的毀壞精神狀態則是較為特殊的存在。上一代不敢採摘的腐敗果子砸到我們頭上,讓我們從頭頂開始腐敗,他們再指手畫腳說:「草莓族」、「挫折容忍度低」、「精神病就是內心不夠堅強」諸如此類的廢話,指控我們的腐敗,明明是他們懸而未摘的醜惡無差別砸落,憑什麼我們是生病的世代?

繽紛
網破,蝶剩下清澈薄翅 無法飛翔 永恆的羽翼屬於鳥 :心之所向 開始喜歡蛛網與凋亡 無法自制深陷 暫時遠離飛花 (仍害怕被冬天擊落) 蛛網糾纏淪陷在死亡 是一種享受嗎 好冰冷,嚮往正常羽翼 莊周不再夢蝶 證明花蜜有效、不需要花蜜 也不是正統的鳳蝶 或許是翅膀的黑暗網絡 需要飛花的蜜...

無色之海
溺斃無色之海 黑暗靈魂壓下 天使光環於更闇的海 銘黃晨輝蒸散無色之海 天使光輝拆斷筆桿 黑暗靈魂停止代筆 ——時晨已到—— 飲晨曦更醉 又文醉 淺薄銘黃的海底撈針 不服古拙罈子純真 存在裂隙 沉醉的縫補古罈的 「針,酒醒了嗎?」親切因為 全身乾涸的只有眼 囚禁水牢看不見、無色之海...

我很快樂
刺痛喉嚨的氣泡水 踢走凌亂床下紙箱板 如何精緻出門而無睡意 「你也喝一口吧?」 不,酒是沈溺 氣泡水足以催眠胃一下午 我很快樂 不想午餐 氣泡水滋滋滋順流而下 啊,胃痛了 沒關係很快嘴裡有黑死病的甜 就以節食的胃痛優越 我很快樂 汽水味從喉嚨竄入鼻頭 心驚差點跌倒 虛弱,彷彿等待...

被閹割的腦-2
他已經被「文采」嚥下,化成這純文學的閹割焦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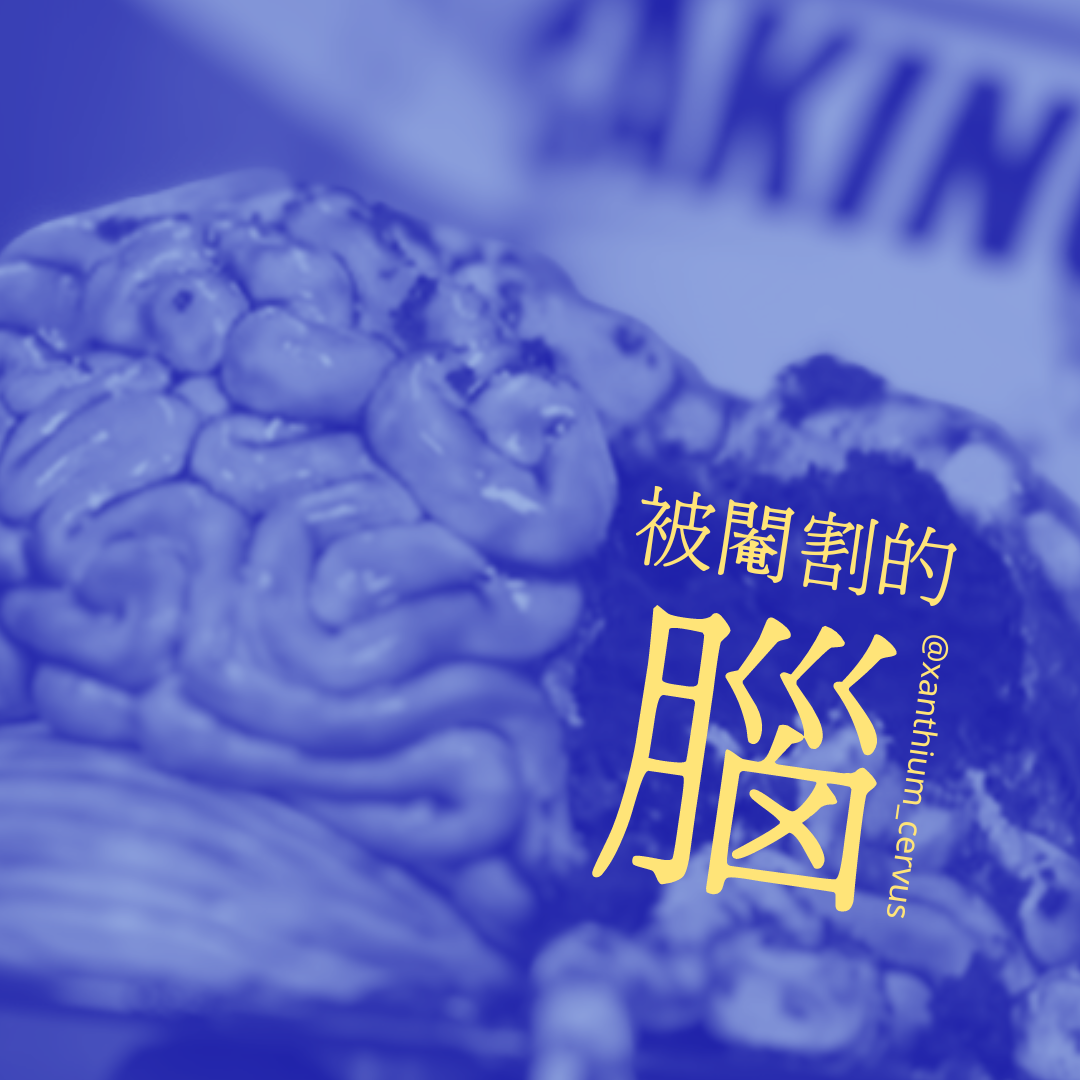
日記|關於小說的謎與謎底
小說之謎,謎之小說,其樂趣來自於沒有謎底,來自於無限增生的時間小徑,來自於破壞與重組。如同班雅明的星座史觀,在點與點之間,永遠有新的可能。
談波赫士《小徑分岔的花園》
我心想,一個人可以成為別人的仇敵,成為別人一個時期的仇敵,但不能成為一個地區、螢火蟲、字句、花園、水流和風的仇敵。
《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論點修正
在我眼裡,這個題目彷彿是夢境的畫面,輪廓模糊,可是真實性不容置疑。圖書館裡,學生在努力啃書,肥胖的館員兜著一個查圖書目錄的女孩打轉,我的論文題目甚至比這些人都來得真實。我心領神會,那是一種不待言語的知性。
談安妮·艾諾《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
我的人生,也許只有唯一一個真正的目標:將我的身體、感覺、想法轉化為文字,也就是某種清楚易懂、普遍性的東西,好讓我的生命完完全全融進其他人的腦海和生活。
關於純文學定義的一些想法
他認為給語言下一個定義是不可能的,而且那樣的思維會遮掩語言和意義如何運作。語言有無數不同的使用方式,為了了解語言是什麼,我們必須研究語言如何運作,而我們只能透過研究語言實際使用的例子來理解。
談艾莉絲·孟若〈蕁麻〉
未來的缺席我能接受,但那只是因為我還不明白缺席的真正涵義,直到邁克不再出現。我生命的領土將如何改觀,像歷經了一場山崩,所有意義隨著土石流被剝除,只剩下失去邁克這件事。
談談卡爾維諾《女泳客奇遇記》和《汽車駕駛奇遇記》
只要我們打電話找不到人回應,我們三個就會繼續沿著白色的車道標線來來回回,不再有起點或終點為我們單純的奔波往返附加各種感受和意義終於擺脫了人和聲音和心情的笨重厚度,簡約為發光的信號。想讓自己與所說的話等而同之、不再因為我們或其他人出現帶來雜音導致話語扭曲變形,那是唯一方法。
談卡佛的《大教堂》
都是沒什麼營養的筆記,不建議讀。
淺談班雅明《說故事的人——論尼古拉·列斯克夫的作品》
說故事者從死亡那裡借來權威,而他們所能敘述的一切也都已經過死亡的核可。換言之,他們都知道,應該讓自己所敘述的故事重新回到大自然的演變過程裡。
談朵卡萩的〈諸聖山〉
牛吃了垃圾,就這樣裝在肚子裡,無法消化。有人告訴我,這就是牛所留下的東西。身體消失,被昆蟲和掠食者吃掉。剩下的便是永恆,亦即垃圾。
談朵卡萩的《轉蛻》
變形從來就不是建立在機械式的差異上,轉蛻也是如此:它將相似性凸顯出來。從演化的角度來說,我們所有人仍是黑猩猩、刺蝟和落羽松,這些都存在於我們身上,我們可以在任意時候伸手拿取,而且我們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隔開彼此的僅有縫隙——存在的微小縫隙。
為何重讀?兼談不追求完整概覽的書評
重讀是很愉悅的體驗。如同RPG遊戲,你由一周目的重甲聖騎士,進化到二周目的拳師,動作行雲流水,不再專注於防守對方的攻勢,而是將對手的一招一式看在眼裡,或側身閃避,或輕輕撥開,如蜻蜓般遊走在招式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