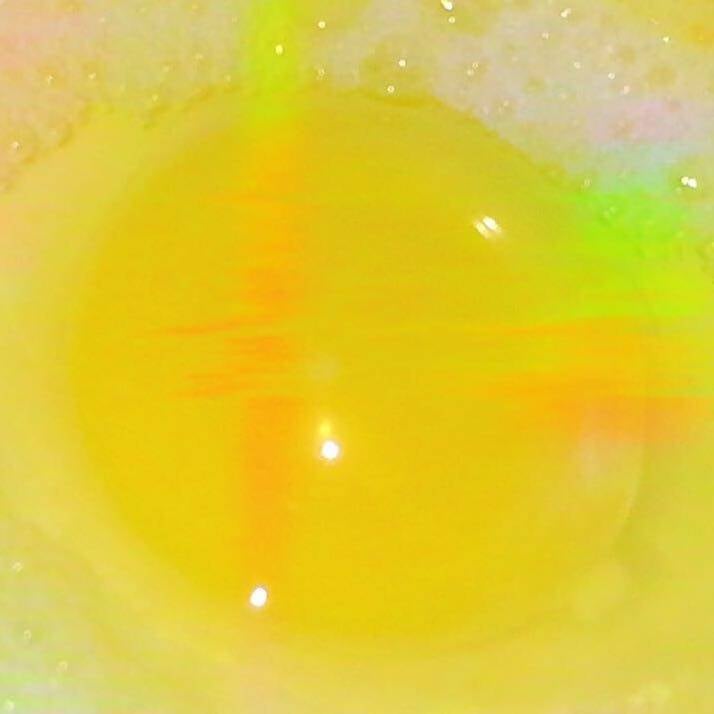翻转硬糖
such a trip
本篇彩蛋是周梦蝶的诗 :p

久违了七日书
吊床应该是很舒服的东西,此刻我在吊床上晃着、打字,由于双臂缺少支撑点,竟生出一些令人想摆脱的不适。但我想应该承接下来,把它当成我选择来到这里的一部分。至少等到30分钟的自由写结束。很难想象我确然是在一个岛屿上开启了这期七日书。那会我正处于不明晰应往哪里走的迷顿中,打开许久没查阅过…

七日书vol.7 |吃人
最后一天,和第一天如出一辙的心悸感。我再一次确认题目,尽管这个题目已被我粘贴到文档里。我不安着一些在阴处我以为很温柔,却是吃人的东西。我又想到《香水》最后的镜头里,发狂的众人撕扯着分食 Jean Baptiste,他逐渐浮出神启一样的笑容,光辉到刺目。

七日书vol.6 |想念嘎嘎
用标题直抒胸臆,嘎嘎是常德话里对外婆的称呼。对家庭的亲切感,几乎只剩和嘎嘎的这份遥遥相念了

七日书vol.5 |态
带着一个人所能最大限度随身的行装(一个28寸箱子、一个登机箱、一个富安娜大号床品袋-装被子的那种、一个藤编筐、一个塞得像炸药包一般的书包),我登上从成都出发经广通转乘至大理的动车。那将是人生中最长的一次高铁,转一下的好处是省钱,省钱的好处是能让我有余地在外面更久(没钱了自然要回家“充电”)。

七日书vol.4 |上海滩
想了又想,没有这样一首典型的歌谣跃然纸上。粤语、闽南语、宁波话、侗语、蒙古语……我都能想到对应的歌,常德话却没有,这让我有点失落,仿佛确证了我不完全属于常德。但由这个题目,我想到了另外的东西。儿时的印象里,常德是个“玩乐属性”蛮重、过小日子的地方。

七日书vol.3 |开枪
第三天的题目让我想跳过。在家庭网格中横竖撇捺看过去,每一段微分关系都太复杂,回想、组织、成型,仿佛需要用掉一生的时间。我突然想到站在暮年尾巴的外公。若顺着更为自然的节奏,他大概是家里最先离世的人。似乎我总爱从“死亡”开始,倒推着回味一段关系。

七日书vol.2 |被子
在正式书写前,我想先花一点时间纪念六四,点一盏维园的烛光。昨晚看《奇美拉》,Arthur发现的那个神迹一样的墓。当值得人们狂热地追逐豪掷千金的女神像在地底显露其容,我不可避免地想到了曾在广场与毛像面对面的自由女神的像;想到了港中文被推倒的女神像。

七日书vol.1 |清泉
家是轮回吗?家能仅仅如其所是,作为家本身吗?

自由写第七日 | 要去的地方是直觉式的显灵
行至最后一天,竟然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果然比起“自由写”,我更把它当成某种任务。若是不断地在强调自由,正说明我离它还很远很远

自由写第六日 | 这是恒久的
长大后,当有了自己的选择余地时,我通常会着眼于解决更“前置”的问题。比如这是一份显而易见的shit job,我便不会take,自然就不需要有一处用于“逃离”的地方。现在回溯那些只得框在程式里的时光,我想到的是高三时我的座位。那是一排有些“特立独行”的单排座位,我也不记得当初是什么...

自由写第五日 | 家或许是虚构的概念
离散如我,是不敢轻易畅想“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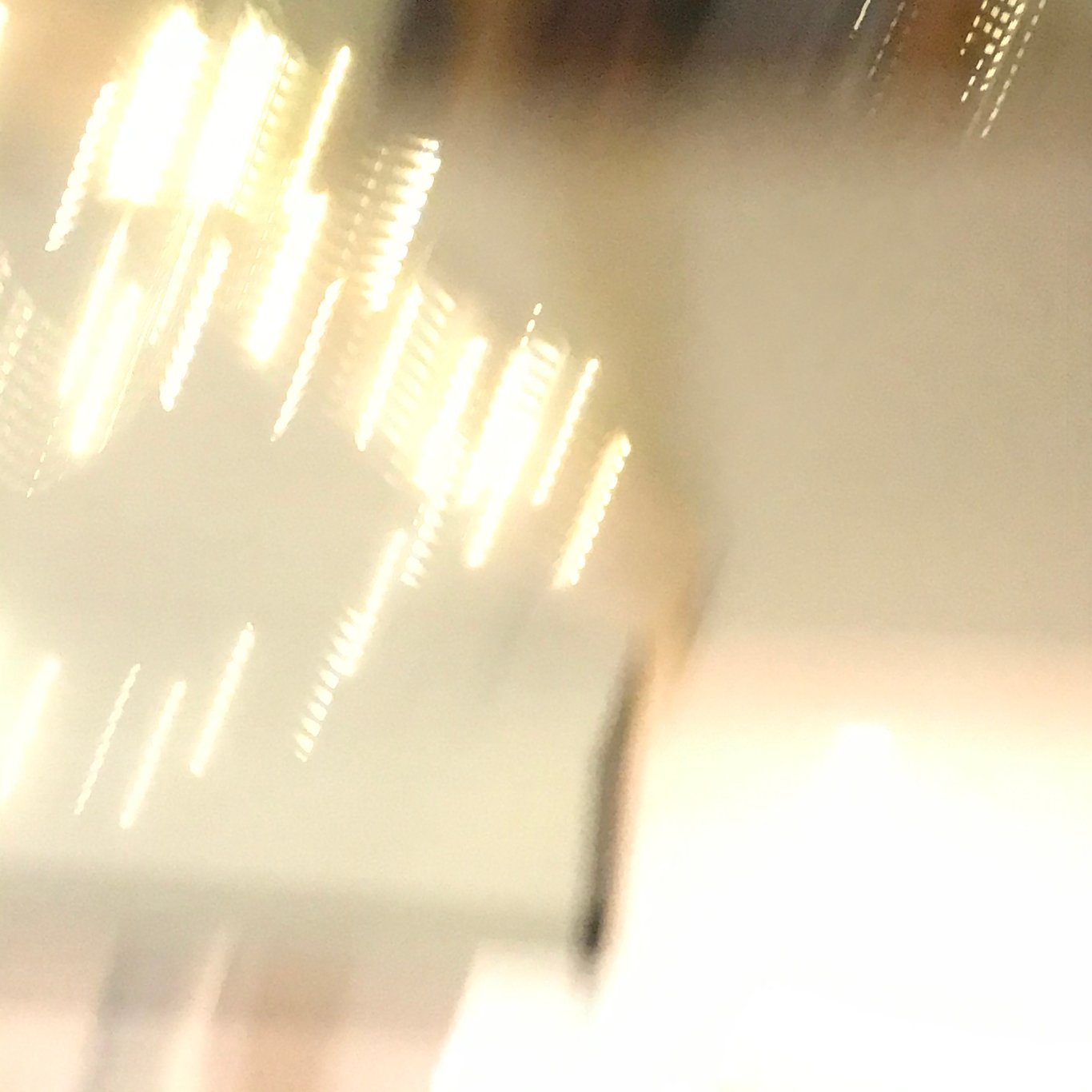
自由写第四日 | 不擅回忆事件 而恐惧的源头一直在那
这是目前感到最有“阻滞感”的一篇,我先是划出完整的上午试图书写,卡顿到不得不暂时放下;转至喜爱的咖啡厅,那是我感到安全的地方,但有限的时间让我不得不放下。直到次日清早。

自由写第三日 | 我喜欢 我接受 我拒绝
这里主要讨论“说” 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人觉得,广州其实地处于有些尴尬的位置。历史上曾被视作“南蛮之地”,自身的语言-粤语必定不登大雅之堂;新中国成立后投票“国语”时又仅以微弱的差距败落给普通话。我料想每个广州人(此处不用广东是因为每个城市又有自己的方言,广州人或许会认为其讲的粤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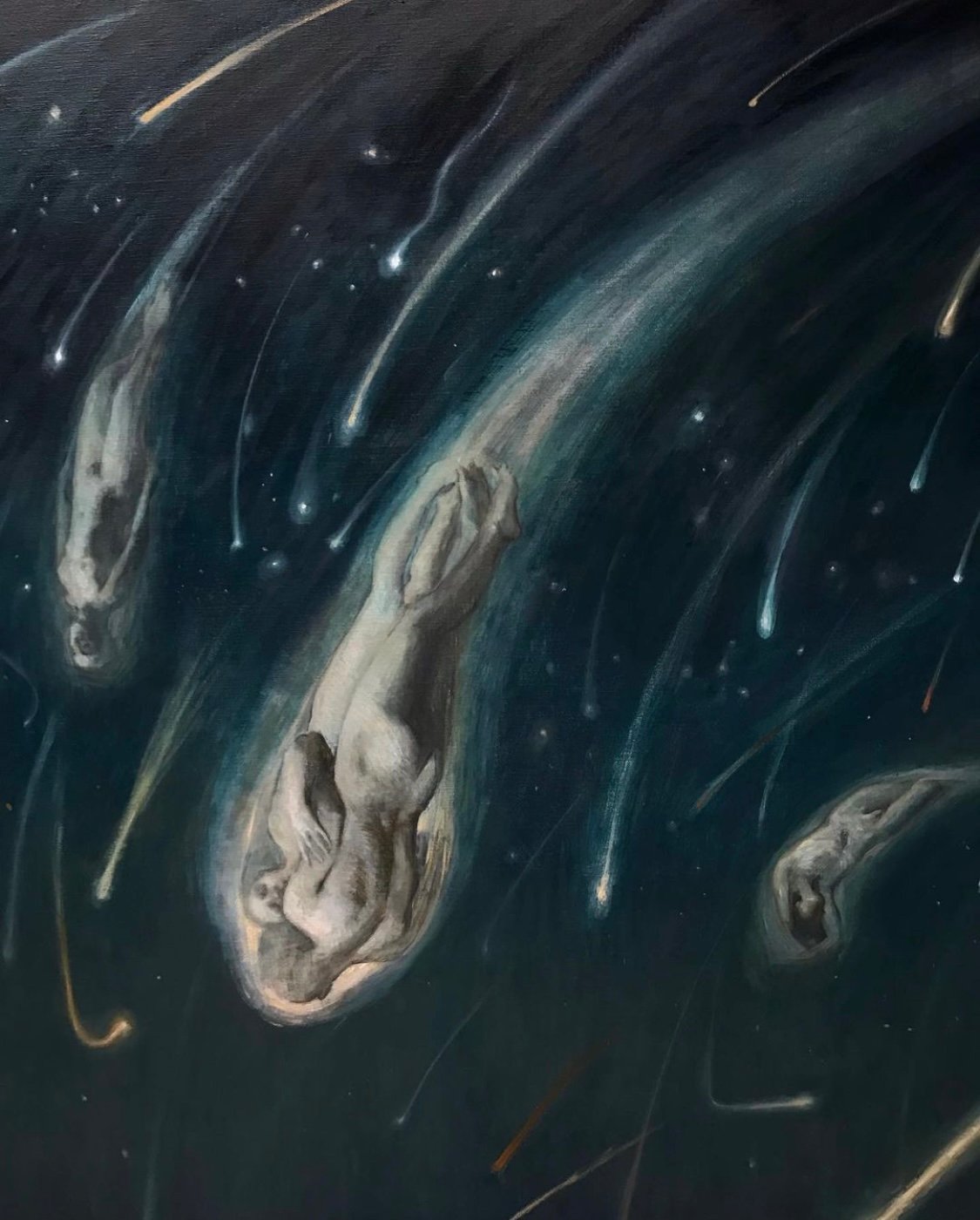
自由写第二日 | 魔法是幻灭的
去沙池吧!碗筷一撂,饭还没落喉咙,念想已飞去沙池。提溜上小桶小铲,有时三五成群,有时只有自己,小学的我,在尚不用应对升学考试的晚间大多是在沙池度过的。沙池的神秘首先在于它的深不可测,年幼的手无论如何也够不到它的尽头,沙子的百变又是种种妙想的土壤,除了垒城堡、挖地道,还有什么可能性?

自由写第一日 | 却忘记了姓名
忘记姓名是不可容忍的,我常常这样规训自己,也许这能解释为何我过于不擅长自我介绍,不给出自己的名字,或给出打了折扣的名字,便能有效避免可能的被忘记。同样,开始回忆这个一直在心底的地方时,我试图从它的名字开始,毕竟至少得言说它叫什么,位于哪里,才显得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