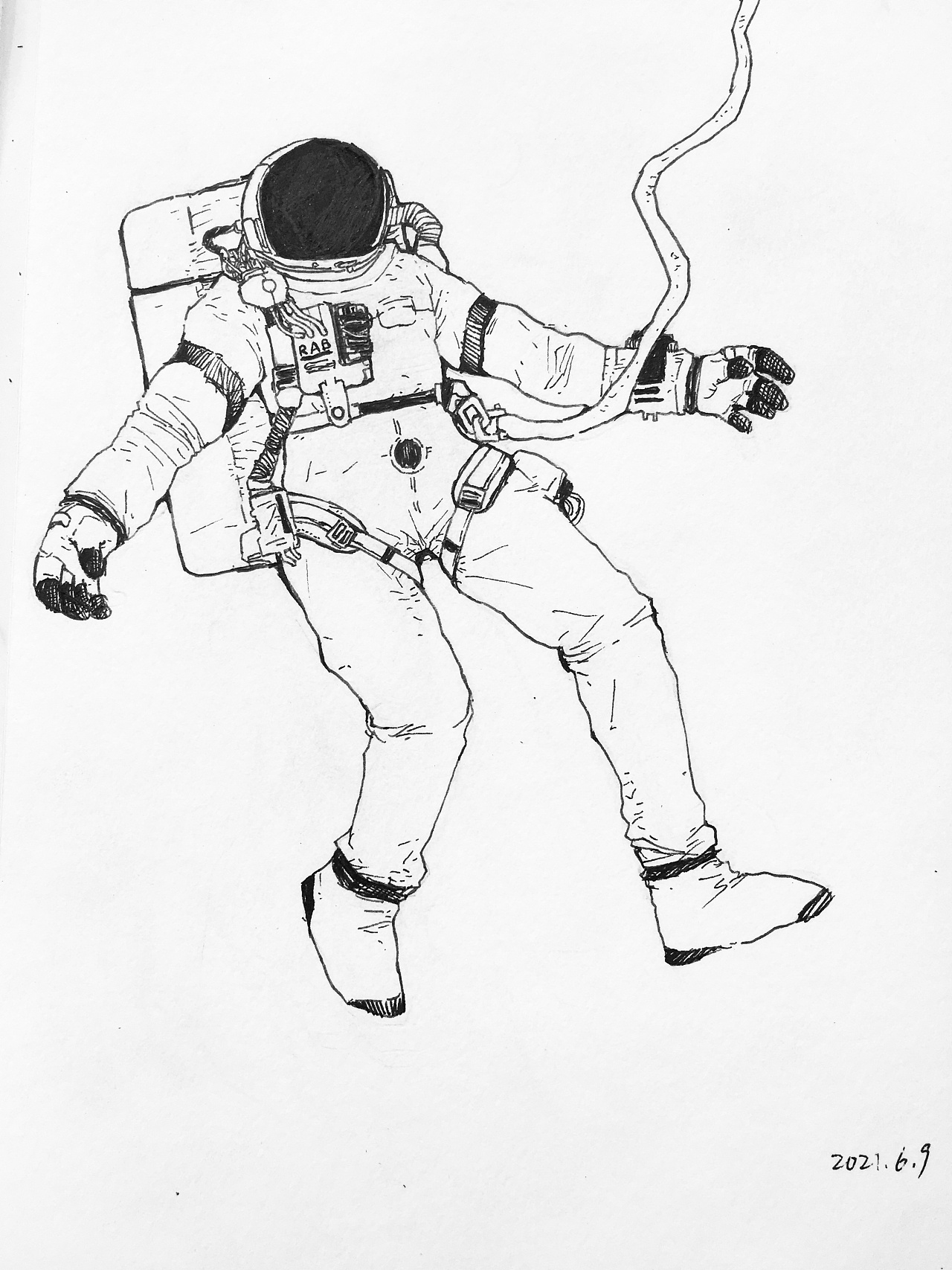阅读|余光中的左手散文
(本文写于202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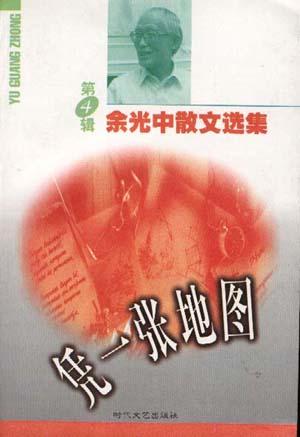
一九九七年出版的《余光中散文选集》,走过二十一年的岁月来到我的桌上与枕边。书页已酵黄而发脆,开卷如同轻抚古物。书古得可爱,但里面的文章仍新得眩人眼目,就是刊载在现代的文学杂志里也毫不过时,甚而还要胜过许多现代的“散文”。我又想起《三体》里丁仪的无奈:“孩子们啊,我这两个世纪前的人了,现在居然还能在大学里教物理。”
我毕竟没有发言权可以老生常谈,而宁愿相信是余光中文字自身的力量超越了时代。一方面,余光中自小接受完整的国学教育,打下深厚的古诗文功底。后来又广读外国诗歌、推广现代诗,留学美国后浪子归来,在中国诗歌散文传统之上,合理吸纳西方文学的思想、意象与表达,意欲“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地说,这颗丹炼成了,而且炼得历风霜而不灭。另一方面,余光中的诗人身份让他的散文具有在抒情、炼字、观察视角方面的“先天优势”,是为“高级的诗质对散文的介入”。不得不提的是余光中的写作背景:六七十年代的台湾。在那个时代,台湾虽有白色恐怖的政治打压,但文学却前所未有地繁盛自由生长,几有“人人读书”的盛况。而因战争来岛避难的许多学者,如梁实秋、胡适等,也培育了许多后来的大家。后来大陆掀起文革,台湾更是凭一湾海峡得以避过那场戕害一代文人的疯狂运动。如今回望当年,不免有“时势造英雄”之感。虽然那片空前绝后的“时势”,也是许许多多“英雄”一张稿纸一张稿纸地耕耘出来的。
而散文,虽然只是余光中的“副产”,却也在他笔下盛放出汉语无穷的生命力。在《余光中散文选集》卷首自序中,余光中提出:“……好像认定散文的正统就是晚明小品,却忘了中国散文至境还有韩潮澎湃、苏海浩茫,忘了更早,还有庄子的超逸、孟子的担当、司马迁的跌宕恣肆。”余光中的散文观源于传统古典文言,成于现代白话文。他的作品不仅扬弃了五四早期稚嫩的语言、抒情方式与眼界,更大胆地破除中文语法、句法甚至标点的规范,以拥抱横有千古、纵有八荒的浩大境界,与至真至善之文意。与此同时他强调“明朗”、反对“虚无”和“无谓的晦涩”,这使他的散文即使用典频繁、炼字稠密,却依然可读而且耐读。文章结构上,余光中也尝试跳出传统中以时间、空间为线索的排篇布局,借鉴意识流的手法,穿梭于古今,往返于此地与彼方。
一
对于五四以来的散文传统,余光中曾撰《下五四的半旗》疾呼“伟大的五四已经死了”,写《论朱自清的散文》,认为他“历史价值已经重于艺术价值。他的神龛,无论多高多低,都应该设在二三十年代,且留在那里”,并多次叩问“我们的散文家有没有自《背影》和《荷塘月色》的小天地里破茧而出,且展现更新更高的风格”。虽然他承认一些指责“失之太苛”,但余光中希望扬弃五四稚嫩的白话文并打磨出一种成熟的、适于现代的中文语言的急迫心情,是极真诚的。
当我们现在重读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时,常常会觉得生涩且陌生。其原因在于,那时白话文尚处于牙牙学语的时期,稚嫩不可避免。且当时改革者拒绝回看中国古典传统,多提倡全面西化。如此背景下,许多语法、用字的规范皆无定数。胡适曾为了写日记,自创了一套标点系统,足见当时中文所处境地之尴尬。我们不能否认五四为中国白话文文学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它的局限:五四的语言已经死亡。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等,可以作为散文的“基础范式”,但决不能成为现代散文发展的方向。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余光中开始了对中文语言可能性的探索:“以诗笔写散文”。
余光中散文里最易于辨识的诗笔,是各种修辞手法的灵活运用,以及极富想象力的动词。在余光中的第一篇散文《猛虎与蔷薇》中曾如此评论:“只有原诗才恰到好处,因为猛虎象征人性的一方面,蔷薇象征人性的另一面,而‘细嗅’刚刚象征着两者的关系、两者的调和与统一。”余光中一直及重视动词的使用,并多次在诗论中提及“动词才是有用的,形容词、副词都没有力量”。这样的理念贯穿在他的散文中。动词的妙处在调和关系,也在化静为动。经动词的点睛,前后的意象便陡然活了过来,且相互紧密联系、交错成意象之网。
归途中,我们把落日抛向右手,向南疾驰。(《石城之行》)
青春不是长春藤,让你戴指环一样戴在手上。等你们老些,也许你们会握得紧些,但那时你们只抓到一些痛风症和糖尿病,一些变酸了的记忆。(《鬼雨》)
因为现代的大城市里,电话机之多,分布之广,就像工业文明派到家家户户去卧底的奸细。(《催魂铃》)
第一句中,将返程中太阳西斜到右手的车窗的情形,写成是“我们”主动“把落日抛向右手”,顿时使无甚趣味的小事翻出诗意,且用“抛”字,更生出一股“天地为我所有”的豪气;第二句中,“青春是长春藤”的比喻其实平平无奇,奇在余光中更进一步把长春藤变作指环,而且以准确的动词“握”与“抓”,联系起青春与衰老的意象,揭示青春之易逝与将老之悔恨;最后一句把电话比作奸细,极尽厌恶之余,更化静为动,使我们仿佛看见一台台电话机偷偷溜进各家各户的荒诞又恼人的场景。
另一处诗笔,是对中文语法、句法、标点规范的大胆创新——现代诗一直是这方面的先锋部队。其实玩语法句法,倒有点回归中国古典传统的意味。我们不是早有杜甫“香稻啄余鹦鹉粒,碧吾栖老凤凰枝”的句子吗?更不用说文言文里俯拾皆是的各种主谓倒装、宾语前置、状语前置了。至于标点,古文中本无所谓标点,而且我们确实有回文诗的传统。当然,余光中的创新受中国古典影响,更受外语语序的影响。“翻译体”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未将外语的语序和句法(如从句)消化而直接翻译。余光中说:“至于欧化的句法,颇有助于含蓄与曲折之趣,有时也是必要的。”某种程度上,外语的句法正为中文语言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但余光中散文的成就不止停留在对中文语言的创新,而在“追求成品而不是原料的和谐”,“让中国的文字……交响成一个大乐队”。
雕落下。萧萧的红叶红叶啊落下,自枫林。(《逍遥游》)
魑魅呼喊着魍魉回答着魑魅。(《鬼雨》)
如此单句摘抄实在不公平。不论是第一句的调换“落下”与“自枫林”的语序,还是第二句取消逗号,以前半句宾语为后半句主语的语法变幻,其意都指向段落与篇章的整体节奏:或突缓停歇,或连绵稠密。余光中绝非为求新而求新,每处语序、标点的处理定是如写诗一样细心推敲而为之。《逍遥游》一辑后记中的一段话,我以为最能概括余光中散文的语言成就:
“在《逍遥游》《鬼雨》一类的作品里,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在这一类作品里,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与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
二
“明朗”一概念,本是余光中在《论明朗》中针对现代诗“虚无”与“晦涩”提出的诗的美德。他写道:
“可是明朗不是一览无余张口见喉式的浅显,含蓄也不是晦涩的代名词。明朗指‘深入浅出’,是指王国维所说的‘不隔’,是指美感经验表现后的透明状态,它使读者的直觉有贯穿的可能。它是秩序化了的纯粹世界,读者可以按图索骥,顺着诗人笔尖所指的方向,去看他安排给你看的风景。然而这风景并非一目了然的。浅显的诗不耐看,明朗的诗则虽透明犹耐百读。这是因为浅显的后面是贫乏,明朗的后面是丰富。所谓明朗,实在是洞察下的深邃,纯朴了的丰富。”
此段论述放之散文亦然。“明朗”在散文中的敌人,更多是“浅显”而不是“晦涩”,是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辫子》中提及的“花花公子的散文”、“浣衣妇的散文”。有太多的散文把无病呻吟当作深刻,把干干净净当作正确,读之无味(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净爽成汪曾祺那样的文字)。某些张晓风和蒋勋的作品皆有此病。而汪曾祺的文字虽然简单到无一字有炼造痕迹,却字字不可少,立得起意境。
余光中前期的散文可以说是汪曾祺的反面了:质感强、密度大、用典频繁、炼字稠密。即使如此,“明朗”二字始终贯穿他的写作。虽然余光中的散文意象繁密,大片大片地抒情,但读起来并不晦涩。究其原因,其一在于意象的具体、生动可感。唐诺在《阅读的故事》中谈到:
“无限不是人的可知对象,但文学巧妙地以具象来处理它、指称它并相当程度地驯服它。文学以有限的焦点实体和我们自身有限的存在打交道,接通并唤醒我们的感受;文学并且以此具象的一点为发光星体的核心,用其光晕般漫射出去的隐喻,点燃我们的想象力,负载我们飞离自身的局限试着去窥探无穷。”
人的可感比于他的可写,是近乎无限的大于。而余光中以其丰富的想象力,用具体可感的意象弥合可感与可写之间的沟壑,再加以上文所述精妙的动词使用,使读者在阅读时最大程度地还原入他意象纷呈的可感世界。可感的通路打通,“晦涩”也不复存在。
月光的冰牛奶,滴进了几CC的醋。(《莎诞夜》)
雨地里,腐烂的熏草化成萤,死去的萤流动着神经质的碧磷。不久他便要捐给不息的大化,汇入草下的冻土,营养九茎的灵芝或是野地的荆棘。(《鬼雨》)
余光中文风“明朗”的原因之二,在于他善妙用典,近于信手拈来出神入化却无一点掉书袋之气。我常常疑惑余光中哪里是在用典,分明就是呼朋唤友、左嚷右拥、闹闹腾腾地把古今中外的文人邀来自己家一起开party嘛!试看:
王维的辋川别墅里,要是装了一架电话,他那些静绝请绝的五言绝句,只怕一句也吟不出了。(《催魂铃》)
当然也不全是太热闹的:
哭过了曼卿,滁州太守也加入白骨的行列。哭湿了青山,江州司马也变成苦竹和黄芦。即使是王子乔,也带不走李白和他的酒瓶。今夜的雨中浮多少蚯蚓。(《鬼雨》)
如此用典,古人不再是高高在上供人瞻仰的神仙,也不再是彰显自己博学多读的材料,而是与写作者、阅读者共悲喜的真实存在。
当然,余光中的“明朗”还有节奏与音韵的明朗,限于篇幅,不一一细讲。
三
紧接着上面的话头,余光中散文的用典不仅是链接情感的桥梁,也为其文增一股横有千古、纵有八荒的浩大气势。我以为余光中散文中最特别的,正是这股气势所形成的厚重感:他的情感与思想总是穿梭于古今,往返于此地与彼方,在小小的书页中拓出无穷无尽的抒情空间。
余光中说他的乡愁“不在具体的中国,而在历史的中国”。因此我们常常读到他的触景生情,思想高速疾驰在时间与空间中:
他不能对那些无忧的美国孩子说,因为他们不懂,因为中国的一年等于美国的一世纪,因为黄河饮过血扬子江饮过的泪多于他们饮过的牛奶饮过的可口可乐,因为中国的孩子被烽火烽火的烟熏成早熟的熏鱼,周幽王的烽火,卢沟桥的烽火。他只能独咽五十个世纪乘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凄凉。(《四月,在古战场》)
短短的一百二十七个字,涵盖古、今、中、外,读者随作者置身于时空变幻的蒙太奇中,惶惶然挣脱实存的当下,以超越光的速度弹射在历史之中。余光中的散文直逼中国古诗时空交错的连环妙计,陈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只怕将将要被比下去了。
四
很幸运的是,经朋友的推荐,我在今年读到了余光中的散文;很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十八年,我对余光中散文的印象只有那首《乡愁》,对“散文”的印象还没能挣脱朱自清。即使自谦,我读的书也不能说很少。你自可以说是我涉猎太窄,那我也可以问:是不是我们的教材选编出了问题?是不是我们的教材选编跟不上时代了?在年青人急切地要找到语言表达自己的时候,教材上却总还是不痛不痒的《荷塘月色》《背影》《北方的秋》,网络劣质小说的盛行果然错在我们吗?我当然懂得“教材是面向全体学生而做出的公约数”这个道理,但是许多公约数毕竟已经老去了,历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了。这时候我们还要死死抱住这个公约数不放吗?如果无法用教材的文本唤起学生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兴趣,那么语文这个学科,除了教授文字规范,除了在高考中贡献一百五十分的分值,还有什么用处?
“童年阅读的地狱,往往是善意的学校教育和教科书铺成的。”唐诺斯言凿凿矣。
教科书如此,更不必说市面上流行的“散文选集”了。当代的“散文选集”图景是:找一个有点名气的作家,找几篇含情脉脉温柔如斯大谈人生的文章,当然还要有点智慧警语,配上几幅不是远方风景就是网络素材拼贴而成的图片,加以松散的排版,就成了一本“散文选集”。不翻则已,一翻则反胃得想呕吐。张晓风、李娟就被这样糟蹋过。余光中苦诗选泛滥久矣,我也苦散文选泛滥久矣。最终的结果是,我们看完之后便想:“原来如此如此写就是‘散文’啊!”世风日下,散文选集的泛滥要承担一半的责任。
那更不用说比散文还要“阳春白雪”的诗了。家中有一本北岛选编的《给孩子的诗》。选的内容是很好的,但我只有一点奇怪:为什么要把外国诗放在前面而中国诗置于其后?“孩子”们难道要先去看二手的陌生化的译文,再来读本土的地道的中国文学吗?本末倒置也。余光中预言:“现代诗将成为中国诗歌的正统。”就现在许多人对现代诗敬而远之的态度看来,离“正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当然我不是盲目悲观的。至少在人教版新教材上,我们看到了刘慈欣的身影;至少有许许多多的图书编辑在一线奋战,尽其视力与心力做好书;至少有越来越多人开始热爱深度阅读,越来越多人参与到推广阅读的工作中;至少至少,还有许许多多的好写作者在写着,尽管他们尚未走出学校的大门,尽管他们尚未被人发掘……正如我常常抱怨学校的不重视绘画艺术一样,愈是喜爱一样事物,就势必要为之忧心忡忡、愁断心肠吧。阿城说,看过的书,总都要还些什么回去。那么,这些些浅薄的文学欣赏,以及这片不吐不快的抱怨,虽然粗糙,就算做是对《余光中散文全集》在高三赐我新鲜空气的一点点微薄回馈吧。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