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致力于介绍人类学观点、方法与行动的平台。 我们欢迎人类学学科相关的研究、翻译、书评、访谈、应机田野调查、多媒体创作等,期待共同思考、探讨我们的现实与当下。 Email: tyingknots2020@gmail.com 微信公众号:tying_knots
240|农耕国家是作茧自缚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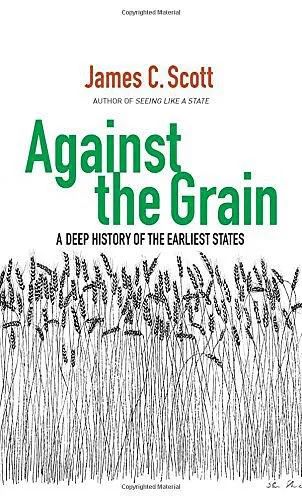
随着俄乌战争,还有此前的全球变暖和新冠疫情,国际上的粮食价格近期大幅上升。伴随而来的粮食安全讨论逐步升温,恰好明示着粮食的不安全感逐渐弥漫,也提醒着我们农粮问题从未随着所谓的人类进步和产业升级而远去。承接此前关注农粮问题的人类学视角,这篇文章借着《作茧自缚》和《万物的黎明》两书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学议程,质询这一不安全感背后的一系列逻辑链条:农业、国家、集权、不平等,这些要素是否在人类历史里一个推着一个地排山倒海而来?作茧自缚是否是人类的必然命运?农业是自发的劳动还是自上而下的规划和统治?
–
有意思的是,常被同归为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的两书作者实有不同的知识生产和行动路径。斯科特与CIA之间的勾连所引发的热议尚未得到他的回应。我们不应简单以人废言,而应历史化地看到斯科特被CIA选派到东南亚的机遇背后是全球冷战下强权对东南亚“世界粮仓”的开发及对东南亚农民的利用与诠释。格雷伯和温格罗所提出的“玩乐农业”概念背后则是近年来国际层面上力图重述工作本质的种种社会运动。与之相对的是,在晚近的粮食危机下,“如何让农民重新去种地”成为理所当然的治理动机。而正如本文的思路所示,这种“理所当然”应当在重新纳入农民工作和政治主体性的基础上被反思。
作者 / Argo
编辑 / YC
对中国读者来说,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并非是陌生人物。这位著名人类学家、政治学家的主要著作,近几年在中国已经陆续出版,从《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到《六论自发性》,斯科特广泛涉猎东南亚山区社会、阶级统治、国家规划、定量研究等诸多议题,以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旨趣(斯科特并不认为自己是严格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思考既定社会的另一种可能——在一个愈发缺少批判和反思的年代,我们相信这种主张是值得追求的。有意思的是,人类学与无政府主义似乎有某种“亲缘性”,这部分地来自于人类学的研究内容:这一学科总是对非国家社会的组织形式抱有好奇和兴趣。正因如此,当大多数学科毫不怀疑地接受诸如民族国家、资本市场这些预设时,诸多无政府主义者和人类学家提出疑问:我们赖以生存的现代制度是否理所应当,有没有另一种发展路径呢?
在斯科特的最新作品《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有关早期社会的“常识”的反驳,在这里,历史并不是从狩猎-采集时代到农耕文明的线性发展;国家也不再具备毋庸置疑的中心地位——在它诞生后的数千年中,它仅仅作为一个变量而存在;更重要地是,蛮族-文明的二元划分,至少在早期社会并不完全成立,农耕国家与文字文明的产生,不只是证明了人类改造地景(landscape)乃至驯化自然的伟业,它同时也意味着,人类的自我驯化——时至今日,我们仍未知道这是否是一种作茧自缚。
01. 谷物造就国家
教科书式的进步史观认为,人类对农作物的栽培是永久定居生活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城市和国家自然产生,文明曙光由此普照蛮荒大陆。但值得注意的是,当第一批有阶级划分、围墙铸就、征税的小型城邦在新月沃地出现时(约公元前3100年),人类在培育谷物、过定居生活方面已经有超过四千多年的经验,定居生活甚至比种植作物和驯化牲畜更早,这种生活方式此后还广泛存在于完全没有种植习惯或条件的人类环境中。
以上考古证据表明,我们的先祖并没有如同我们想象的那样,在掌握培育作物的技艺和习惯定居生活后,十分欣喜地投入到国家的怀抱。这种表述的错误来源于其立论前提对现实的简化:原始社会资源匮乏,依靠采集-狩猎的手段难以为生。相反,早期大型定居点往往出现在各种物资相当丰富的地方,例如,湿地。

斯科特指出,实际上,六、七千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是由数百条支流纵横交错形成的湿地三角洲。当地居民就生活在地势稍高的土丘上,周围的湿地资源触手可及:充当建材的芦苇莎草、可食用的各种动植物,人类自如地充当猎人、采集者、牧民等多种身份。我们很难想象在这种地方具有诞生早期国家的土壤,因为丰富的“共同财产资源”让自上而下的集中化管理毫无必要,而多样化的维生资源(植物生长期和动物迁徙期的不同),更使得中央简单的核算办法不可能,这也意味着,征税——国家的基本支柱难以保障。
但毕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早期国家的摇篮,而农耕文明又确实是其基本形式,这意味着该地的人类社会一定发生了重要变化。在斯科特看来,这与谷物种植有重要联系,最开始,它只是早期人类众多活动的一部分,人们会根据天时和具体环境,在种植者、收集者、猎人等角色中转换,但谷物种植以及动物驯养的开展,带来了一种深刻的历史变化,这使得农业乃至国家占据人类生活的支配性地位。
一方面,谷物耕种与狩猎以及采集在性质上有重要区别,狩猎采集工作遵循着多种多样的自然“节奏”,往往具备随机性和多元化;而农耕则专注于单一的食物资源网,使人们陷入年复一年的常规当中。事实上,所谓“文明化的进程”,也暗示着一套严格安排、步骤精细、互相关联、强制性的日常工作。斯科特不由打趣道,当智人走上务农的道路时,我们这一物种就好像进入了一座恪守教条的中世纪修道院。即便在早期社会中农业生产只是族群活动的一部分,但一旦它出现,则意味着人类族群必须更加紧密地生活在一起,以便完成一系列繁杂的时间表和例行程序。
更重要的变革在于谷物本身。事实上,可以满足人类需要的作物当然不只谷物一类,但为什么我们未能发现有关诸如“大豆立国”“马铃薯立国”的踪迹呢?尤其是在谷物之外,同样也有很多作物,可以支撑大量人口的食物需要并富含营养价值。斯科特认为,谷物对国家形成的影响在于,只有谷物可以作为有效的征税基础,因为它看得见(相较于埋在地下的马铃薯);可同步成熟(相较于不断产生豆荚的豆类),再加上其可分割、可估算、易于储存和运输,这使得谷物成为最有利于征税效率和方便的物种。
正因如此,早期国家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对谷物和人力组合的控制与利用。现在我们能简单复原这一过程:农耕劳作将人类限制在标准化的程序当中,职责分工、农业相关的祭祀以及奴隶的利用扩大了阶级分化。雏形期的等级国家依靠谷物获得税收,这进一步增强国家的强制力。而为了使得收税、资源分配、农地管理等活动更加高效,必要的书面文字随之诞生——早期文字记录常常是收据、库存清单等。当然,为保护既有财富(同样,防止生产者逃跑),国家也应该筑造围墙。所谓“文明”的诸多要素由此齐全。
02. 崩溃,抑或是新机会
围墙的出现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现象,尤其当早期国家并没有我们惯常想象的那样文明和美好时。拉铁摩尔考察中国长城时发现,这道宏伟的围墙不只是将蛮族阻隔在“文明世界”之外(正如统治者常常标榜的那样),它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是,阻隔不满于苛捐杂税的农民们出逃。围墙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象征着国家的脆弱性,它并非完全符合教科书中的暗示,较非国家社会来说有不可置疑的优越性。例如在前文提到过的美索不达米亚湿地,资源丰富随处可见,采集、狩猎毫不费力,农耕生活也只是满足资源多样性的一种方式,对当地的居民来说,等级统治、生活受限、甚至还要缴纳物资充当税收的国家,有什么吸引力呢?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因素导致国家生活不受欢迎。首先是人畜大量混居产生的大量流行病,农庄综合体——人、猪、牛、鸭和各种野生动物集中在一个固定区域——是天然的禽流感和猪流感病毒培养皿,更别说大量物种聚居产生的废弃物(粪便、秸秆等),是蚊虫、老鼠等疾病载体理想的繁殖和觅食场所。不光是人,农作物也是大量新兴疾病和食草动物的受害者,同时它们还要与顽强的杂草竞争。但我们都知道,农作物的单一化人工栽培,相较于多变的大自然而言无比脆弱,早期人类对地景的有限改造,需要时刻防范四周自然环境的强烈反扑。
史无前例的新疾病,无论是霍乱、天花,还是腮腺炎、麻疹和流感,似乎都是“文明效应”的表现。人类历史上广泛传播和具有严重致死率的疾病,大多与城市化和农业发展密切相关,这也能解释,为何在新石器时代带来革命性的文明成就时,世界人口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流行病学的意义上,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一段时期,初步聚集的人类社群饱受各种疾病的蹂躏。
人口集中定居更意味着对自然环境的深刻改造,或者不妨说,破坏。早期人类社群往往出现在河流下游冲积平原和入海口。侵蚀作用将上游的土壤、木材冲刷下来,满足聚落的基本需要。但木材的用途是如此广泛(取暖、建筑房屋、冶金、烹饪等等),以至于它总会成为稀缺资源,国家不得不将砍伐木材的范围从河流下游往上扩展。短期内这当然不会造成问题,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木材的日益消耗,上游的水土流失足以达到引发灾难的地步。洪水、淤泥阻塞水渠、淤积带来的疟疾传播,都能对人类带来毁灭性影响。除此之外,过度灌溉造成的土壤盐碱化,也使得经过一段时间后,人类不得不放弃一片土地并迁居别处,而这很容易导致原有社群的消亡。
疾病肆虐、生态破坏、战争、暴政引发的集体出逃,乃至贸易节点的转移,都能轻易地导致一个国家的毁灭。我们常在历史书上看到各种文明在短暂出现后就归于沉寂——崩溃,对于人类社群来说,这似乎是一个相当伤感的命运。但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国民而言,这只是为适应多变而残酷的社会环境的一种审慎策略罢了。对文明本身来说,崩溃指的是从庞大(但也脆弱)的政治实体分解为多个较小而稳定的组织的过程,与其说这意味着悲剧性的解体,不妨说是一种常见的对文化的重新建构和去中心化,小而密集的人类定居点可能比璀璨的帝国更长久,而倘若环境需要,它们同样也能重新转变为集中化的国家结构。
事实上,诸如“文明崩溃”和“黑暗时代”的说法,本身就是国家中心主义和精英史观的体现。毕竟,国家崩溃最大的受害者应当是不事农耕、剥削其他阶级的“肉食者”们,对他们而言,无人使唤、无法统治确实是一种灾难和黑暗。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阶级国家的崩溃也可以象征着争取自由行动的胜利,甚至意味着人类福祉的集体改善。埃及的第一中间期并没有导致人口的急剧减少,地方统治者对中央的名义效忠可能带来了税收的降低,这意味着中央控制的减少和小规模的民主化;《荷马史诗》可以追溯到多利亚人入侵的黑暗时代,这不仅能说明文明并未随国家崩溃而消失,口头史诗的流行还代表着文化并不为少数识字精英所垄断。
03. “高贵的野蛮人”
奴隶制并非国家的发明,但我们确实可以说,国家发明了系统性、大规模的强制劳动,这些苦力和奴隶多为战俘和被虏掠的外国人。奴隶往往从事繁重而危险的工作,例如挖矿、采石和伐木,稍微幸运的奴隶,则成为权贵阶级的奴仆,以此彰显等级社会的威严和不容反抗。在这种情况下,底层生产者以及被完全物化的奴隶,有足够的理由逃离国家的控制。更具挑战性的观点可能是,国家外社群当中的人们,也在自觉地进行抵抗,以免被纳入到国家体系当中。事实上,就算到公元1600年左右,绝大多数人口都不归属于国家体系。他们是猎人、采集者、山民、刀耕火种者、牧民,非国家社会仍然具有难以想象的吸引力。

正如斯科特在他另一本书《逃避统治的艺术》中描述的那样,居住在东南亚山区的人们利用地形崎岖这一自然优势,成功地阻止了国家力量的介入,栽种“国家避免”的作物(如荞麦、芋头)也使得经济控制难以进行。由此,山区居民较大程度上规避了徭役、征税、战争、劫掠等国家现象的影响。这种现实揭示了“蛮族”一词长期受到的污名化过程,他们并非完全是茹毛饮血的原始人或者未开化者,而是不属于国家体系的人,出于经济和政治因素逃出国家的居民在其中占据了不少比重。只是因为对国家的拒斥,他们长期被国家中心叙事认为是“没有历史的人”。
随着民族国家的诞生,全民动员和意识形态宣传逐步走向日常化,对于现代人来说,效忠于某一国家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但对于古代乃至更久远的社会而言,国家并不那么具有优越性。可以说,帝国的繁盛与否,同一位奴隶或农民有什么关系呢?正因如此,在早期国家中,“自我原始化”即便不是常见现象,也绝对称不上值得惊奇的事情。这种逃离国家的行为不会被普通人视为悲惨和愚蠢,相反,它可能带来生活环境和营养状况的改善。讽刺的是,重新变成“野蛮人”,对很多人来说是改变命运的良机。
更进一步说,农耕国家倘若能被称为更加文明的话,这根本上源自于国家体系更高效的剥削方式(或许,只有在国家当中才有体系化的剥削可言),这使得国家更加强大,进而推动国家这一实体在人类政治建构中最终“胜出”。今天的历史策略类游戏精准地还原了这个逻辑:居民只是作为与矿产、水源、木材等类似的资源而出现的,它在不同的环境下由人口数量、人力储备、劳动力等指标表示,一切目标都是为了使玩家控制的对象(通常来说是特定的文明或者国家)能够成为支配区域乃至整个世界的霸权。在这种情况下,谁能说集中控制、等级制的农耕国家不是最合适的制度呢?
《作茧自缚》暗含着斯科特对启蒙主义式进步史观的挑战。现代国家并非我们唯一、更非最优的制度选择,“现代性”本身也并不理所当然地象征着人类历史的新高峰。类似的表述我们同样能从其他人类学家那发现。大卫·格雷伯指出,17世纪来到新大陆传教的法国神父沮丧地写道,当地的原住民社会比法国更加自由、和谐、容易满足。萨林斯也描述过澳大利亚的“原初丰裕社会”,在这里每个人都称得上“有闲阶级”,平均每日四小时不到的劳作,就可以满足生活需求,剩下有大量可支配时间用来闲扯、吃饭和睡觉。反观大部分现代人,深受“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折磨,从业者都不知道自己的职业对社会有何益处,还要每天重复着例行公事,那么尊严感也无从谈起了。
必须指出的是,斯科特的目的并不在于将早期社会浪漫化,也并非要求现代人重返蛮夷。正如伏尔泰所讥讽地那样,即便人们萌生用四条腿爬行的欲望,但毕竟我们已经丧失了这种习惯。斯科特力图说明,启蒙视角下的现代性思潮,让国家与市场的中心叙事垄断了一切解释权。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国家与市场之外还有人类文明可言——这不仅仅是一种自负,同时也是无知和缺乏思考力的体现。斯科特在质疑“黑暗时代”的表述时写道,“黑暗”究竟是对谁而言,而又指的是哪些方面?同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启蒙和现代究竟表现在哪呢?与其对不合理的制度缝缝补补,是否存在替代性的选择?——或许这才是人类悠久历史带来的最重要的经验。
04. 作茧自缚?——大卫们的回答
在《万物的黎明》(The Dawn of Everything)中,大卫•格雷伯与大卫•温格罗同样拒斥了早期人类社会的主流观点。他们指出:人类并非因为人口、环境负担才开始农耕生活,而对作物的精心栽培和对动物的驯化在很长时间内都并非早期人类的主要活动。从觅食者(forager)到农民(farmer)的路径固然符合启蒙式的进化论预设,但它更多只是满足了政治建构的需要,或者是迎合了现代主义的进步狂热,而并非反映人类历史进程的真实状况。在对线性跃升史观的质疑中,斯科特和两位大卫达成了共识。因此,我们不妨简要介绍《万物的黎明》中的相关论点,以此与斯科特的理论形成对照与补充。
上世纪80年代的一项实验表明,只需运用简单的农业技术(镰刀收割或单纯用手连根拔起)就能在二三十年内改变野生小麦的基因,使其能够适应对作物的驯化,这一过程至多也只需要两百年。但在今天北叙利亚的部分地区,早在公元前10000年就已经开始谷物栽培,但对其的驯化直到公元前7000年前后才完成。再结合上文中斯科特提到的新月沃地农耕生活与城邦诞生之间长达四千年的时间差,不难发现类似“农业革命”的说法更像是伪命题,因为这种“转变”实在是太过漫长,以至于我们无法找到任何明显的标志性事件来说明革命确实发生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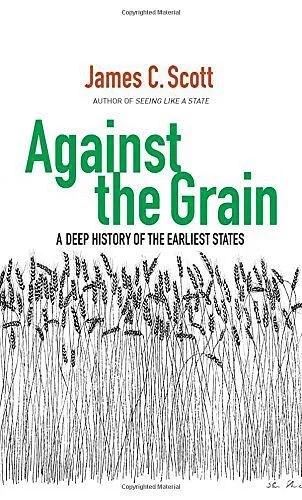
叙利亚地区谷物培育到驯化的漫长时光同样证明,对于先民而言农业远非必不可少。查塔霍裕克(Çatalhöyük)位于土耳其中部的科尼亚平原(Konya Plain),是已知最早的大规模人类居住地。在上世纪的人类学研究中,查塔霍裕克被看做是“农业发明”“农业革命”的里程碑,但随着发掘的愈发深入,新的证据表明原先的诠释更像是现代人的牵强附会和一厢情愿(一个重要例子是,该聚集地的艺术与仪式活动都几乎与农业无关)。而当我们考察查塔霍裕克的周边环境时,或许可以对此做出解释。
查塔霍裕克坐落在一片湿地当中,附近的河流定期泛滥,河道纵横交错于科尼亚平原上。大大小小的沼泽环绕在四周,其间点缀着一些地势较高的干燥地块。读者可能会发现,查塔霍裕克的周边环境与斯科特所考察的美索不达米亚早期人类定居点几乎没有差别,这也确证了人类早期社会的湿地假说。正因如此,查塔霍裕克居民对农业的“冷漠”也就不难理解:大量动物伴随着河道变化在湿地四周迁徙,洪泛平原带来肥沃的土壤,居民只需等待洪水退去即可。无论是狩猎、采集还是种植,都不被视为需要历经磨难才能得到的施舍。在此时,严肃的农耕活动只能是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对土壤的维护、幼苗的照顾,以及丰收后必不可少的脱粒簸谷,不仅会占用其他获取食物活动的时间,更别说工具制作、生育和游戏玩乐了。
斯科特将农耕种植看做早期人类多样活动中的一种,而格雷伯与温格罗将这一定位更加具体化。与其说新石器时代人类对动植物的影响方式是栽培与驯化,将其视为园艺(gardening)或许更符合实际情况。对此,我们可以以亚马逊(Amazonia)为例进行考察。雨林居民在捕杀猴子、鹦鹉和野猪等动物作为食物后,会将它们未成熟的后代养育起来。但关键在于,这些动物并不被视为可持续的狩猎对象,也即意味着它们不会在成年后被吃掉;同时,居民也不会在它们成年后继续喂养,而是让其自如地生活在人类社群当中,作为情感寄托和玩乐的对象。
在这个意义上,早期人类对动物的“驯化”,与我们今天对动物园的管理并没有明显区别。就算这不足以概括各地的情况,但至少为我们理解人类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那就是:“农业”(让我们暂且保留这一称谓)并非诞生于资源不足、人口压力大的困窘境况,而是相当休闲、娱乐化的产物。这也意味着,对早期社会来说,我们今天认为是农业劳作的行为并非出于营生的需要,而是人类探索生活多样性和可能性的一种形式,倘若它真能被定义为农业,那么玩乐式农业(playing farming)的称呼或许更加恰当。先民们并非是在与自然环境的搏斗中将其降服、驯化(domesticating),而是说服乃至劝诱自然使之为人类代劳——我们在洪退耕种、动物培育中都能看到这一点。
在前文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斯科特实际上暗示了农耕与早期国家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即农耕与不平等的必然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表达了“作茧自缚”的忧虑。但格雷伯和温格罗认为这并非不可避免。事实上,在新月沃地这种农业与早期国家的重要发源地当中,社会阶级分化与不平等现象的出现,也是在开始农业栽培与驯化活动千年之后的事情。而倘若我们采用“玩乐式农业”这一概念,那么这种将农业从各种早期人类实践(或者不妨说,实验)中剥离出来,将其视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理论,无疑更加站不住脚。
在各地的实际情况中,农业更不代表私有产权、财产分化和地位不平等。大量考古证据都表明,共同所有权(communal tenure)、对土地的定期再分配、共同管理等行为并不特殊和少见。查塔霍裕克的例子同样指出,尽管存在社会威望上的个体差距,但更具社会地位的个体在居住分布上与其他人没有区别,更没有形成精英聚集的社群。在性别关系上,同样也不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异。
尽管存在一定的分歧,斯科特与两位大卫都指出平现代惯常认知的漏洞。正如格雷伯和温格罗所总结的那样:尽管从现代社会出发的各种假设看上去顺理成章,但“你不能简单地从故事开头跳到结尾,然后假设你知道在中间发生了什么”。人类学所具备的开放性、不确定性,使其拒绝任何基于现代思维范式的应然推断,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必然是充满争议和质疑的,也因此具有颠覆性和创造力。
作者简介
Argo:硕士不知道读什么的社科学生
最新文章(持续更新)
农耕国家是作茧自缚吗?
欢迎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
独立网站:tyingknots.net
微信公众号 ID:tying_knots
成为小结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