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不公不义,如何在深渊中存活
重谈政治抑郁在今天的文章之前,想先谈一下去年成为小群体内现象级词语的“政治抑郁”。实际上那几篇文章的撰写初衷,是笔者的个人纾解需要。在这个词语被广泛传播和使用后,我想需要做一个补充说明。之所以使用政治抑郁这个词,一方面是希望更加明确地点明造成今日痛苦的一种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在更清晰和聚焦的语境…

我的霓裳中国 | 汉人之外:在寻找民族服饰的过程里感受中国
在喀什的假发我在古城大门斜对面的美食城里用餐,戴了一顶蓝色的假发,几个带着花帽的维族服务员看了我很久,忍不住走过来夸我的发色好看。一个五官立体的男孩走过来,问我头发是真的还是假的。冬天的喀什,河边的芦苇在日光下摇摇晃晃,空掉的古城躺着残垣断壁,路上行走的人们穿着朴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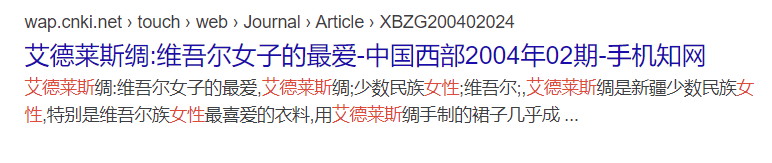
2020,交换生请回答
前两天收拾东西,翻出了以前在台湾交换时拍的照片,拍摄者是我当时的台湾男友。物是人非,多年后的今天就看到了《教育部:暂停今年大陆各地各学历层级毕业生赴台升读工作》。念社会学的网友食菠萝发表感慨:“同学说,我们这几届陆生搞不好是两岸交流历史的短暂插曲……” 关于交换生和交换生活,我曾经写过一些不痛不痒的文章。

南下省親記 | 尋找散落的人類學家
4月23日—29日,从东南到西南,拜访人类学系毕业的三个朋友。三月过得颓唐,日日失眠,在某个难熬的夜晚鬼使神差买了张去广西的机票。待春意将歇,恢复了气力,便决定把这次南下旅行的主题定为“省亲”——我要去看看曾经的人类学伙伴。人类学没有本科,本科低年级时我只是通过理论课了解过一些。

在泰国边境喝醉后,难民朋友说他想做社工
十月初去了泰国边境一个叫美索Maesot的地方。亚洲最大的难民营在这里。泰国与缅甸边界逾 1,800 公里。缅甸数十年军事统治及族群冲突,造成十万余难民避居泰国境内的难民营;同时,过百万缅甸人被迫成为移工,在泰国谋生。我在这里认识了从缅甸来此地的阿伟和阿豪——最近看港片多,所以给他们俩起了这样的化名。

遇见大灰狼罗克
翻出了我的“参考文献” 在郑渊洁的童话里面,有一个经典形象叫“大灰狼罗克”。在郑渊洁起笔写童话的年代里,大灰狼还是儿童文学里面的典型坏形象。哦,想起了灰太狼,看来到今天大灰狼也不是什么好角色。罗克的诞生起源于《大灰狼画报》,这是一本低幼童话刊物。

3月11日我在北京
本文寫作于2018年3月11日。我從一家大企業辭職,去了一趟新疆,剛回到北京。寫完這篇文章的不久後,我離開了北京,結束了北漂生活。墻內寫作,多用曲筆以抒胸臆,當日絕非偶然寫作這篇文章,文中寫到的那條新聞到底是什麼?我想了很久很久。早上起來,打開英語聽力,聽力講得是關於芭蕾舞的事兒。

寫給女孩的話
儘管新年即將到來,女性境遇卻遠沒到辭舊迎新的時候。最近的新聞,每一條看了都生理不適。牟林翰,馮世祥,錢逢勝,老中青齊活了。而受害者都是年輕女性。今天不想用什麼曲筆,寫什麼隱喻,只想告訴你:這些人,有毒。考慮到這些事情都是發生在人際關係建立以後的,或是戀人,或是夫妻,或是師生。
朋友感染了HIV,我才发现自己对艾滋病了解得太少
其实我面对面和感染者接触只有两次。一次是大四研一那会儿做毒品使用者的社工干预课题,和项目负责老师去了昆明的戒毒所。当时比现在还要学生气很多,带着访谈提纲和问卷,跟人家聊天。在女子戒毒所那边,学员一个个的轮流和我聊天。遇到一个年级蛮大的学员,说着说着就哭了,提到自己得病了,我说什么病,她说艾滋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