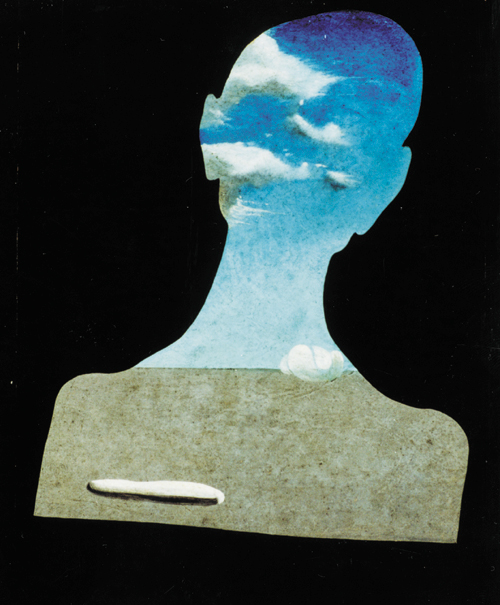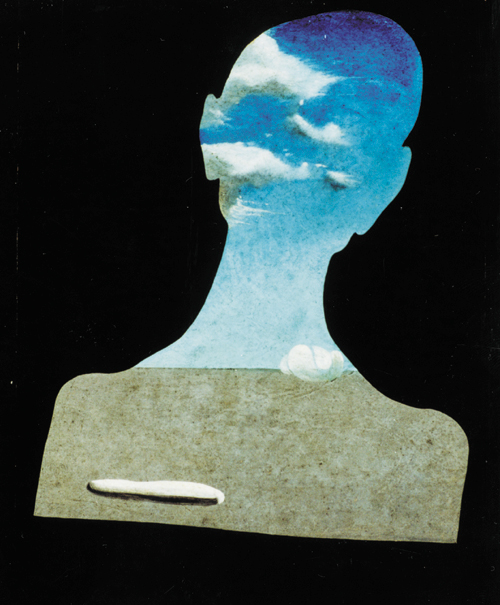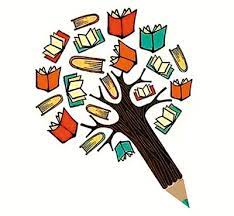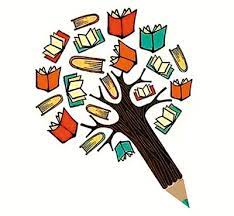哈尔滨,道外的旧故事
当我走出中央大街地铁口,走入通辽街时,这样的感觉更强了。路上很多人,人们围在大连铁板烧、冰糖葫芦的推车摊位边,公交车从我们身旁穿过,通辽街开着一个又一个餐厅,本地菜、烧烤店、俄式餐厅。在向松花江方向的步行中,在某些街口,还能一瞥与通辽街平行的步行街,那里挤满了人吵,他们在冰雕、商店、旧日殖民地建筑中漫步。
这让我想到了上海九江路,尽管,四周的建筑物明显指向了另一种维度和气候,但都有一种旧日大都会的气息,一种丰富的街区混杂的感觉。尤其是当我,经过通辽街132号,发现这是一栋规模巨大的犹太活动旧址,此时变成了咖啡店、书店、音乐会堂时,在走上几步,一支交响乐团成员,正在犹太中学旧址的教室里,进行着排练,他们由不同年龄组成,很多是业余爱好者,每周末会在刚刚经过的老会堂举办古典音乐演出。
那一晚,我去看了他们的演出,指挥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中年人,他们表演了一些民族、红色的古典乐曲。表演结束时,乐团成员在掌声中,在这间老教堂里,鞠躬、致意时,我感觉到老建筑物活了起来,这片街区也活了起来,哈尔滨也正在向我敞开。
人们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哈尔滨,对于漫长的中国历史来说,也可以说是一天。这是哈尔滨的简短城市史:1895年,沙俄迫使清朝,签订了《中俄密约》,获得了中东铁路修筑权。 1898年6月9日,沙俄决定将铁路工程局设在哈尔滨,以此成为铁路的中心。从哈尔滨出发,往西到达满洲里,往东到达边境口岸绥芬河,此后又修建了向南到大连的支线。
1920年代,哈尔滨成为了国际大都市,大量俄国移民及其他欧洲移民来到这里,也留下了丰富的外国建筑群。第一天,我们在哈尔滨的旅行,围绕新艺术建筑。出发前,王可达参考了常怀生在1990年编著的《哈尔滨建筑艺术》。三十年过去了,我们很难确定书上现存的建筑物,面貌在今天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去了红霞街的老公寓、科学宫、秋林公司旧址、马戈尔宾馆、米尼阿久尔餐厅的旧址.......整个中央大街,周围都是老建筑物。我很好奇,这些漂亮建筑物的背面有什么。当走去时,尤其是住宅区,更多是一副破败的面貌。从外观看,公共区域堆满了杂物,有些房间的门都是破碎的,居住面积很小。这里和上海、武汉、广州一样,房管所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很多人只拥有一栋房子的某处居住权。
在铁路的另一头,就是道外,这里有着庞大的中华巴洛克街区。我们站在靖宇街,纯化医院所在的十字路口。王可达向我们讲解四周的建筑,他觉得这些建筑,像是一本本细节很多的书,也是一座座记忆的宫殿。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柱子,很多房子会为了伪装成一种大理石建筑,而刷上了白色的漆。但岁月却暴露了秘密,颜色脱落了,人们很容易看出这是砖块建成的房子。
“这是为了装点门面。这栋房子看起来,在圣彼得堡、莫斯科也成立,但细看的话,更像是进入了《盗梦空间》的世界,在里面,你无法醒来。” 王可达比喻道,这些建筑就像是一栋栋记忆宫殿,暗含着当时的中国工匠们,所处的丰富时代,具有的一种混杂的知识。王可达继续带着我们,观察这些建筑的细节:“你们看方形的浮雕,画着梅花和鹿,还有一块像是中式园林的匾额。这底下,有当地人熟悉的梅花、菊花,但还有一个菠萝,这并不是黑龙江的水果。也许,工匠也没有琢磨那么多,但他们吸收了不止是俄国的新事物,也有来自南方的新事物..........”
漫步在哈尔滨道外,总会让我想到汉口、上海华界的故事,小学老师常会提起,跑马场的告示牌上,会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晚清的上海,华界与两租借在外事活动上,会展开凸显谁是上海主人的竞争。上海道台会在豫园,备八人大轿,用中国传统菜肴来款待美国来宾。汉口的首富刘歆生买下了租界外的大片土地,成为地产巨头,建成了对所有人开发的“华商跑马场“。
这里有着类似的故事。 1898年,中东铁路修建时,数万名中国人来到哈尔滨,他们选择住在了道外。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铁路、海运通路被日军封锁,哈尔滨的民族资本业迅速发展,随着工业发展,他们开始模仿起道里、南岗的外国建筑,同时又在窗式、花纹、女儿墙等细部,加入了蝙蝠、牡丹的中国传统元素,形成了一大片今天被称为“中华巴洛克”的街区。
1920年,道外焕然一新,但始终不如道里那般现代、繁华,缺少公园、医院这样的公共设施,但不失为一个独特、热闹的中国城。在靖宇街,商铺林立,开设有同记商城、大罗新环球货店,人们可以去陈氏接骨、世一堂看病,还有亨达利、典当行、三友照相馆、温泉浴池等各种生活服务。绍兴人来此开了饮食店老鼎丰,还有不少河北人开的张包铺、老仁义、宝盛东等餐厅。街上也总有演二人转、耍猴的、耍大刀的、演皮影戏的贫苦民间艺人。




1990年,道外的生活一样是混杂的、热闹的,它地处市中心,但房价较低,吸引了很多外地人来这落脚。如同潮湿会吸引蘑菇一般,城市的老街区,也总会生长出棚户区。另一些居民,则住在1930年代的商业、工业建筑里,它们的进深较长,采光很差。大多数人的住处很逼仄,没有卫生间,在冬天需要烧煤来取暖。
迟子建在中篇小说《起舞》,描写了如此景况:“如果说道里是一个衣着华丽的贵妇人的话,道外就是一个穿着朴素的农夫了。道外原来叫傅家甸,从一开始,这里就是小手工业者聚集之地,虽没有大气象,但最具人间烟火的气息。直到如今,哈尔滨的道外区,仍是大店小店,遍地开花;三教九流,无所不有。”
今天,我们失去了道外的生活,也许只留下了一些碎片。在北头道街,我很喜欢北三沙家烧麦,这里有十五块一碗的羊肉汤,里面好多羊肉。当你喝完了汤,伙计会爽朗笑一笑,问你要不要再加一些,是免费的,汤很浓郁。他笑着说,我坐着近,很方便就给我加汤。汤都在一个滚动的大锅里,里面正煮着一整根羊排骨,浮动着让人有食欲的油荤。那是我最喜欢的一顿饭,如果我会再一次去哈尔滨旅行,很可能只是因为这家小店。
坐在我隔壁的,是两个中年大哥,他们也快要老年人。两个人是做装修的本地人。其中一个告诉我,装修队里,也很多来自湖北孝感,这些工右来了几年后,就不愿意回老家了,因为受不了南方的阴冷。两个大哥点了水爆肚、韭菜杏鲍菇、两碗羊杂汤,98元,正喝着啤酒。桌子上有不少空啤酒瓶,一个人对着另一个人说道,干一杯吧。
“对我爸,对我妈,我都不亏心。但我妈说八句话,有八句话都不对,我就顶回去。” 说话的人,更消瘦一些,面色红润。他总共只喝了一瓶啤酒。他说,和自己表哥很久没联系了,就不细说了。我预感到,当一个人说不想细说时,往往代表了要开始讲故事了。
“以前,有一个老房子,等着拆迁。他不愿意,想着卖了买新的,卖了11万5。再等几年,等拆了,可以分几十万。但卖了就是他自己的,等拆了后,就是四个人(二姐、大姐、小表姐,我哥)分。其实,我大姐、二姐有钱,就算等拆迁了,她们也不会要。”
“新房子,最开始也是我帮着装修和水电的。到死了,表哥也没让他爸妈去住。他老爹死的时候,眼睛都没闭上,你说能闭上吗? ”
这也是老故事了,道外的动迁工作早就结束了。所有的居民都搬走了,现在这里到处都是围挡和脚手架。仅在南十四道街,就有十多家劳保店。但有一些工人,会专门来到纯化医院的十字路口在王阿姨的摊位上,购买更便宜手套、鞋子。
这一片,有很多人在摆地摊,有些是职业的,有些是批发生意失败后,需要清理挤压库存。城管不会驱赶他们。两年前,王阿姨来到这里,她告诉我,冬天是生意最好的时候,很多游客会来哈尔滨玩雪,逛完中华巴洛克风情街后,顺带来买些厚袜子、手套。
十八岁,王阿姨进入哈尔滨一家皮革厂工作,但她没有想到四十四岁,工厂改制了。此后,她领到了一笔赔偿金,要给自己交养老保险,靠自己养活。很快,王阿姨找到了私人鞋厂合作,在家里帮忙加工鞋面。这几年,合作鞋厂也不景气了,她决定来到头道街摆地摊。一双十五块的手套,很多来自亲戚、朋友们不要的旧衣服。
这样摆摊生活,还能持续多久,王阿姨也说不清楚。来摊位买劳保的工人们越来越多事,也意味着她离开的时间快到了。按照规划,我们所在的北头道街,位于中华巴洛克三期,这里会成为一处全新的文旅消费聚集区。
那天下午,我们在道外历史街区漫步,只能通过遗留的店招、木头楼梯、丢满垃圾的胡同,来想象过去热闹的生活秀。不远的未来,这些建筑被修缮好了,但街区也消失了,只留下了一个诺大的影视城般的观光地。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