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書> 第四日|流連粵語歌中,懷念
嚴格意義上說,我不是道地的廣東人。我的父母一個來自北方,一個來自南方,相遇在北京,然後南下了深圳。我一歲起就在深圳長大,卻很清楚深圳並不被廣東人看做道地的廣東。我也學會了本分,很少在外說自己是廣東人,在廣東人面前更是如此。
我的父母都不說粵語,但小時候去香港,聽到店員們口頭確認“大陸人”,或者地鐵上有人念叨“北姑”,我媽會白上一眼。上學的時候,跟廣東孩子耳濡目染,我也開始張口說,卻總是鬧笑話。例如,“下雪“我會說成“下血”,“興趣”會說成“性趣”。後來我再也不用國語的同音詞套在粵語上了。
我的粵語突飛猛進是在英國。那年我十七歲,跟大多數內地去的孩子們找不到共同語言,於是混在了香港學生堆裡。我參加他們的社團,跟他們去唱卡拉OK,一起刷TVB劇,讓我找到一些歸屬感。有好幾個新年和聖誕,為了不跟一堆不認識的大陸學生喝酒吹牛,我也是跟他們一起度過的。就這樣,我的粵語進步很快,至少到了去香港購物,不會被店員白眼的程度。
粵語對我的複雜意義是在我離開學校後才開始顯現的。父母是90年代初到的深圳。當時香港還沒回歸,大陸沿海和香港的收入水準還有相當距離,香港也還沒有爆發革命。那個年代去深圳的人看上的無非是改革紅利,收入和機會都比內地好,唯獨去了香港會感受到階級差距和赤裸裸的瞧不上。母親在深圳生活了快40年,至今還會說起回歸前,她在公立單位工資只有幾百一千,難得去到香港買衣服,卻被Marks & Spencer的店員當面嘲笑:「這件毛衣680塊,你買得起嗎?感的孜孜念念,以至於總用「彈丸之地」這種貶抑的語言談論香港。
但反觀我,從小就受香港文化影響,看TVB,聽粵語歌。後來,自由行去香港方便了,我會說些粵語,有文化親近性,又喜歡這座城市的法治和效率,很自然就愛上它,關心它的命運。大學時代,我有內地朋友去了香港讀書,正值香港經歷爭取真普選的雨傘運動。作為一個不會粵語的大陸生,他們經歷的內在矛盾、衝擊、甚至創傷,是我難以感同身受的。那時我意識到粵語對我的意義更像一張通行證,一張可以走近這層文化內外,和有關它身分記憶的通行證。
後來的將近十年,我對粵語和粵語文化的親近讓我更願意走近香港的文化和電影,理解香港的政治和運動。和粵語相關的記憶還有愛情,有我在異國他鄉的失戀夜晚無數次循環的「Lonely Christmas」。我因為粵語愛上了王家衛、杜琪峰,也愛上了在無聊的工作日夜晚反覆狂刷無間道,思索那個總在鏡子裡審視自己的劉建明,是否就是另一個時空中正在掙扎的自己。
如今我身在美國,我的身體和語言都脫離了最舒適的土壤,對生活的歸屬感和掌控感消失殆盡,我常常靈魂出竅,不知道哪裡可以回去。失去語言的我,彷彿站在一條湍急的河流中間,一邊是失去自由的陷阱,另一邊則是無法附著的孤獨,我終於接受無論是母國還是異國,在此刻都已無關痛癢。我為了被理解、被愛而不斷解釋、嘶吼,直到最後精疲力竭,發不出任何聲響。
在最被抽空的日子裡,車裡的粵語歌單竟成了我最安靜的歸處。當手放在方向盤上,對速度和方向的掌控歸於本位,思緒卻被兒時就會哼唱的粵語歌帶到了安靜的地方。我們之間沒有審查的張力,它也不要求我自證清白。我們像兩個走得很近的過客,享受著彼此的陪伴,但不羈絆於情感的包袱和對錯的重量。這是最沒有期待的關係,也是最讓人平靜的關係。
也許,迷失在粵語旋律裡,就是迷失在我兒時對那個小小城市單純的喜歡和對公平、自主的執著裡。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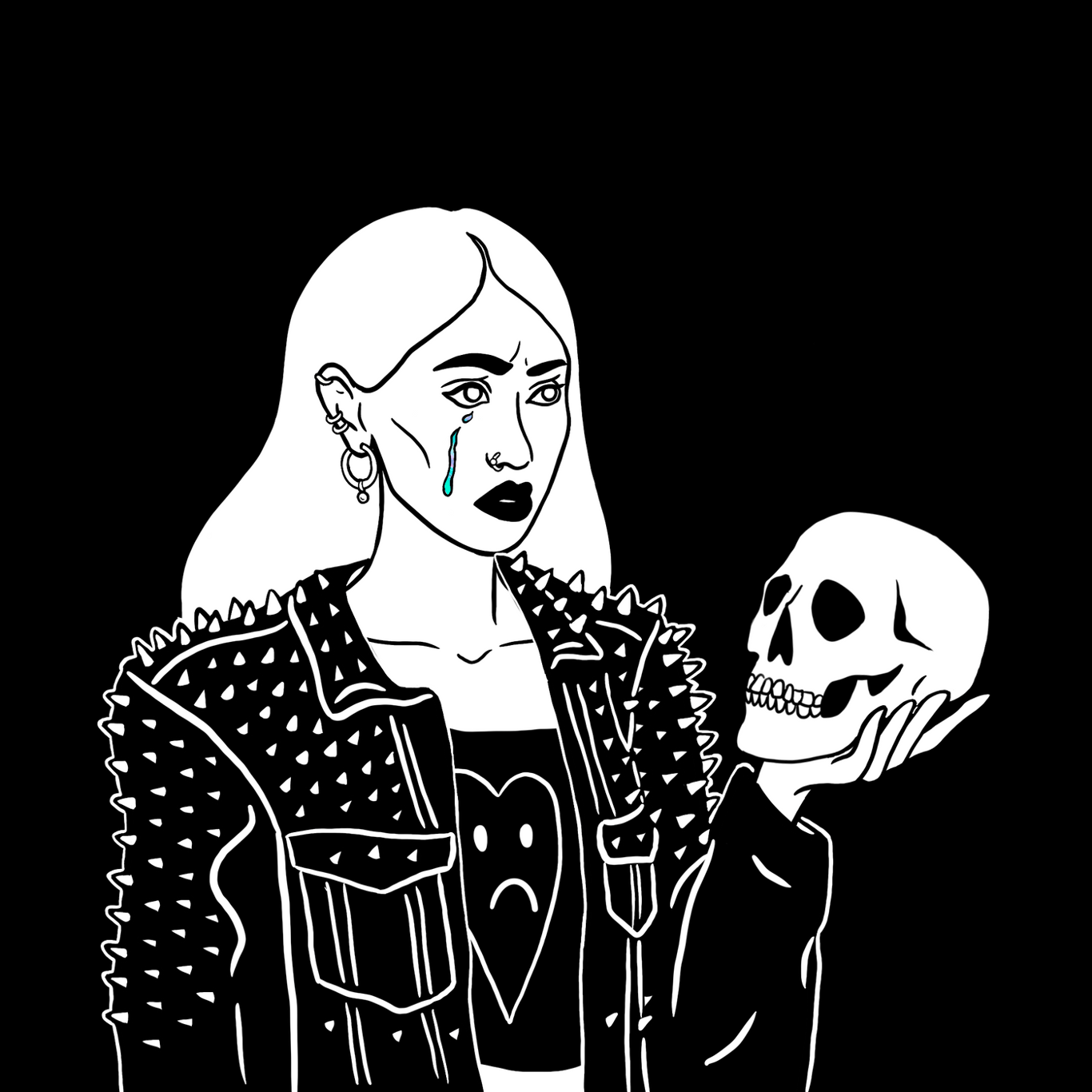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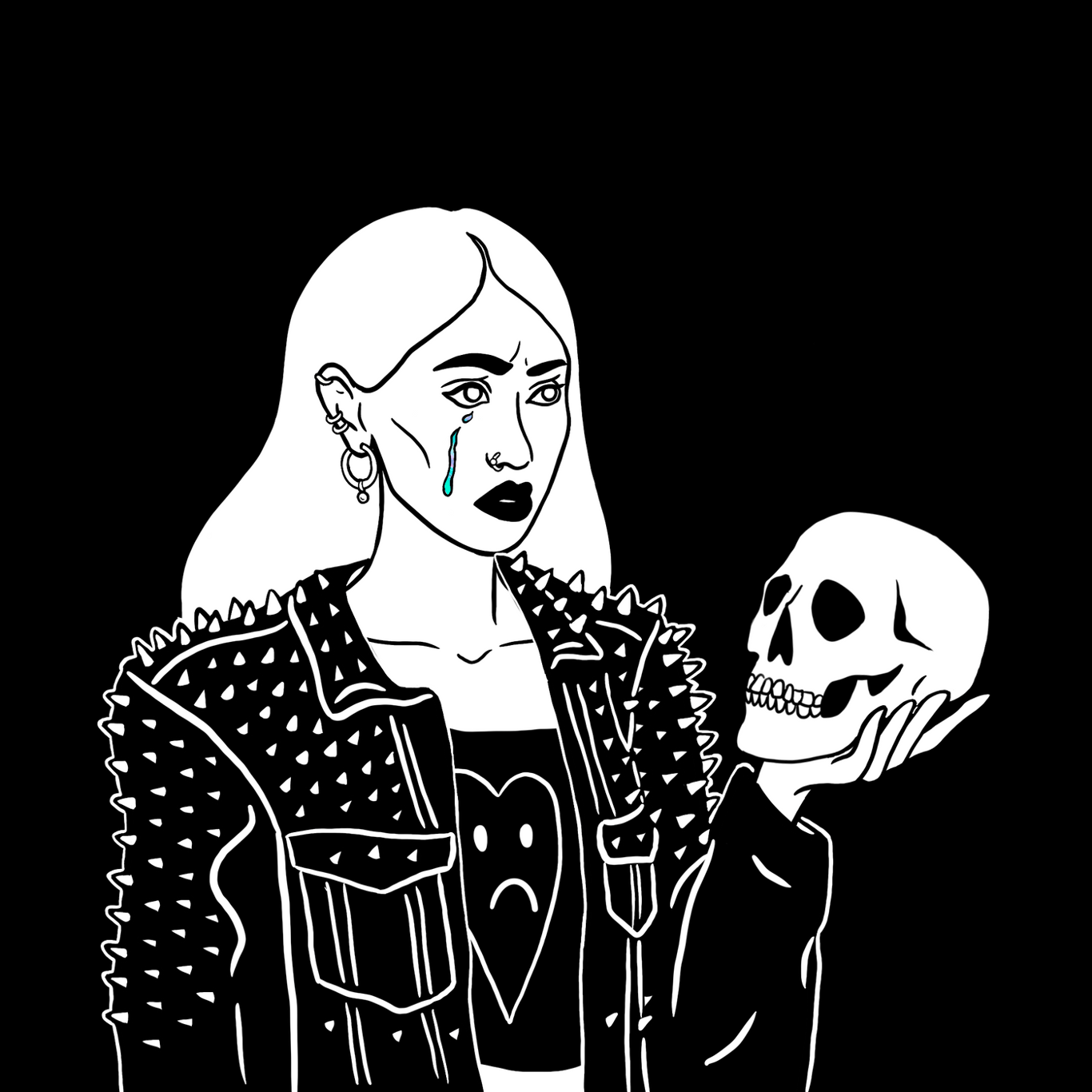

- 來自作者
- 相關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