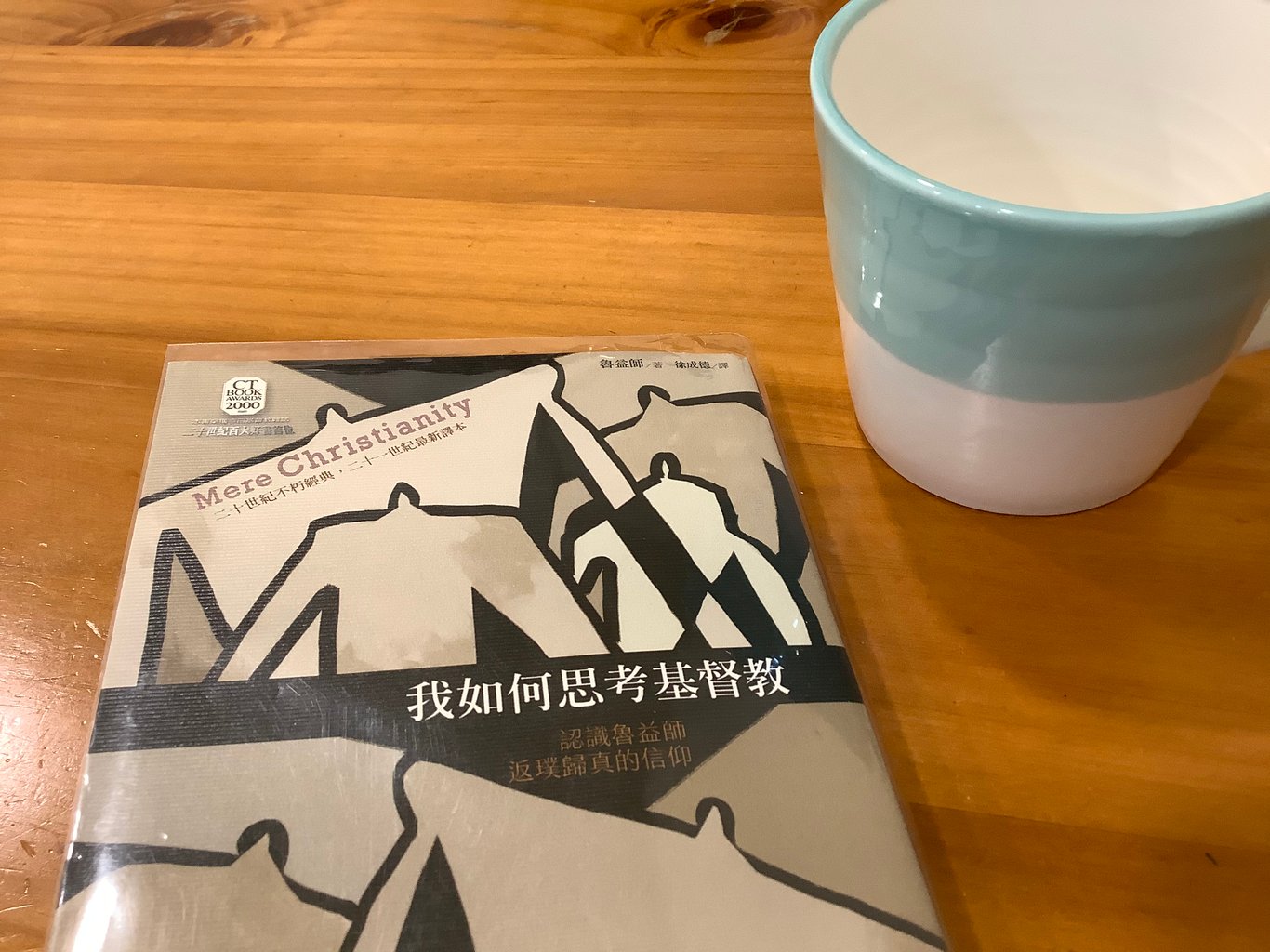來自雪國的遺書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所謂的文學,不過是怡情養性的奢侈品。
意味著,即使我們的生活中,即使絲毫沒有「文學」的成分,並不會使我們有所欠缺。
有些人喜歡文學,那很不錯,但沒有文學的人生也不見得錯過了什麼。
現在的人要“說服”自己去閱讀文字,需要越來越多理由,畢竟有其他更快的理解方式:有podcast、有YouTube影片。
但是有時我忍不住想,我們其實不知道自己在遠離文字的時候,究竟失去了什麼。
「來自雪國的遺書」這個故事讓我深受震動,因為它清楚揭露了「文字」對於我們真正的意義,和它無法取代的力量。這些需要被「寫」出來。
事實是,那些「不喜歡文學的人」,只是還沒有發現文字的魅力,還不知道它的力量而已。他們還沒有機會讓它在心裡爆炸,在內在創造出一個更大的空間,容納他所還未能體驗的豐富感性與思想。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戰爭終於結束了,但是對於在滿洲被蘇聯俘虜的日本軍人來說,是另外12年痛苦的開始。他們被帶到蘇聯的國境內,從俘虜變成戰犯,關押在天寒地凍的西伯利亞收容所裡,在營養不良及嚴苛的勞動條件下掙扎求生。
在零下幾十度的極寒中從事重度勞動,一天只配給三百五十克的黑麵包、飄著兩三片剩餘蔬菜的鹹湯⋯,身體衰弱的人因為營養不良,一個一個死去,其他人瘦成皮包骨,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跟著倒下。
在這樣的環境裡,有一個人忽然說:「我們來辦個讀書會吧!」
「讀書會」根本是一個搞錯場合的詞彙,在生存條件嚴酷到快活不下去的狀況下,「讀書」應該是他們最不需要的一件事。
但是這個帶著眼鏡,看起來斯文瘦弱的男人,像是理所當然地這樣說:「沒錯,如果放棄活著回去的希望,我們很快就會沒命了。不稍微動動腦袋的話,將來就算回到日本,也會因為變成俘虜笨蛋而派不上用場。」
「那也要回得去再說吧!」這是大多數人沒有說出口的話。一開始還懷抱著歸國的盼望,但當希望一次又一次落空的時候,放棄還比較輕鬆一點。
死去的同伴就在白樺樹下挖洞掩埋,將來自己也會力竭倒下被埋在白樺樹下,那就是自己的命運,默默地忍受勞役,直到有一天倒下死去。
只有山本不一樣,他所擁有的不只是「樂觀」而已,他彷彿已經“看見”將來歸國的一天,只是把這個消息傳達給看似毫無盼望的現在。
「冬天,會有寒流來襲,即使穿著防寒棉外套也覺得冷,連聲音都會結凍,不管是敲石頭還是打木頭,耳邊都只會縈繞『鏗鏗鏗』的金屬聲,令人毛骨悚然,爐火也燒不起來。阿新,這些全都可以當作季語喔。」
季語是俳句裡的元素,在短短的字句中,融入對季節的感受。「時間」是俳句這個文學體裁的生命,我們都活在往而不返的時間裡,因此所有的此刻都獨一無二。俳句似乎比任何題裁都更適合傳遞生命轉瞬即逝與獨一無二的尊貴性。
身處於收容所中的犯人們,被剝奪了自由、尊嚴、身份、家人⋯⋯幾乎是一個人所有的一切,但是即使如此,透過被創作出來的文字,透過文學,他們保有了某個極重要,無法被奪走的珍貴事物。
即使在戰敗時拿著自決用的手榴彈,寫下給遙遠故鄉的妻子、父母遺書時,天空仍舊是藍的;在極寒之地獨自一人面對二十五年的重度勞動刑時,天空也依舊是藍的;那種藍可以用什麼字語來形容呢?山本所寫下的「西伯利亞的藍天」這首詩,讓收容所的同伴們,開始找回對生活的感受和喜悅。
他們背著監視兵用木棍在沙土上寫字,寫完就趕快擦掉;用剪下的水泥袋做成小冊子,馬尾巴的毛和解開的繩子都可以拿來做筆,以燒剩的煤炭浸泡在水中代替墨汁。
並不是為了忘記苦難而寫作,而是生命本來就充滿了值得書寫的事物。
無論現實多麼不可理喻,只要活著,生活仍然充滿了許多值得開心的事物。並不是故作堅強,山本是打從心裡這麼覺得,即使是在收容所裡,還是可以發現許多喜悅與樂趣。
被關進收容所裡的日本軍人大多是三十、四十歲的青壯年人,人生中最有可為的時期,他們有許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菁英,卻被關在這裡,像奴隸一樣做著開採煤礦和鋪設鐵軌的工作。
當1956年最後一批戰俘從收容所被釋放回到日本,已經是戰爭結束的十二年後了。戰爭結束時三十歲的青年人,回到日本已經是四十幾歲的中年。受山本委託背誦遺書的其中一人,在回到日本以後,先是找到在建設公司倉庫的工作,後來靠著苦讀考上土木技師的執照,結婚後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四十幾歲才開始的人生,他還是沒有虛度地盡力往前。
這或許是因為山本總是這樣鼓勵他們:「我們還年輕,人生還很長,一定會有回去的那一天。」
總是鼓勵周圍的人,帶給人盼望的山本,自己並沒有能夠活著回到日本。1954年,收容所生活的第十年,山本幡男在收容所裡因病過世。
為了將山本的遺書帶回給日本的家人,他的朋友們以背誦的方式傳遞山本的遺書,這是因為紙本的文件會引來懷疑,被抓到可能因此延長刑期。
山本過世的一年八個月以後,收容所爆發抗議事件,有許多人因為絕食抗議而身體虛弱,但對於受託遺書的人們,記下遺書交給山本家人的任務,成為支持他們生存下去的動力。
山本過世的兩年後,日蘇共同宣言簽訂,蘇聯終於決定釋放境內所有剩下的日本戰俘。帶著山本留下話語的人們,接二連三的拜訪山本的老家,將遺書傳遞給他的妻子、母親和四個孩子。
不只是山本的遺書,還有他們一起在北國所創作的和歌、俳句,已經刻印在腦海中,成為生命中不可抹滅的部分。是這些文字讓他們撐過在收容所裡艱困的生活,和回到日本之後再出發的人生。這些文字構建了他們生命裡面那個堅韌的核心。
話語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力量呢?在被表達的那一刻,有什麼被創造出來,有一個新的架構在心裡發生,有什麼感受和新的想法誕生,這些都在有意識和無意識的領域裡同時發生⋯⋯如果錯過了這些,人的生命會有多麼無趣呢?
或許正是北國那貧乏的環境促使人在內在發展出更豐富的事物;在無法滿足的渴望裡激發了創作的慾望。這樣說來,貧乏和飢渴會不會反而是一個優渥的環境,使人有機會品嚐更深刻而穩固的滿足?
在病榻上,山本依然持續創作。對來探病的朋友野本,他這樣說:「我腦袋裡出現『兀隆兀隆』這個詞,所以就想著要好好運用一下⋯兀隆兀隆,你不覺得這個詞很不錯嗎?」
山本用「兀隆兀隆」寫下「海鳴」這首詩。
在回日本的歸國的船上,「海鳴」這首詩浮現在野本的腦海,後來在他人生的許多時候,這首詩也時常浮上腦海。這或許也是山本遺書的一部分,是他所寫下,留給這個世界的文字之一。
只要這些文字仍然被閱讀,在某個人的腦海裡迴響,創作者就仍在述說。
因此文字從來不只是一個符號而已,也無法被其他任何取代。它怎麼被寫下,怎麼被記憶,怎麼被想起,這些過程都是不可思議的奇蹟。
我無法想像,生命中如果沒有這些奇蹟會是什麼樣子。我在想那一定非常非常無趣,失去大多數可以為之驚奇的事物,並且不知道要用什麼來填補。
邊見純的「來自雪國的遺書」被歸類為紀實文學。但我喜歡叫它「紀實小說」。稱之為「小說」並不代表不夠真實,而是因為它具有相對應的創造性與敘事性的架構及藝術價值。
紀實永遠比不上小說。對於紀實文學最大的讚美應該是「它讀起來就像一本創作的小說」。因為真實永遠不缺乏戲劇性,卻很少人能發現這一點,很少人知道如何呈現這一點。
作為紀實文學,「來自雪國的遺書」並不會因為它不夠真實而失去價值,但可能因為敘事不夠完整或結構鬆散,而失去成為一個好故事的機會。讀者或許會好奇,書裡所描述的是否都是「真實發生過」的情節,沒有什麼比一個真實發生過的故事更引人入勝的了。但你知道,它只是一個故事,意思是當你聽到它時,多半已經落入敘事者的圈套中。
我心甘情願落入邊見純所精心編織的圈套裡,因為她用一種詩意又明快的語調說故事。她採訪所有事件的當事者,取得她所能得到的所有第一手資料,然後她鋪陳這些一個一個目擊者的陳述,說的就好像自己所創造出的故事,如此地完整又渾然天成。
所以我不會指責在這個故事裡其實忽略了一個極為重要的「事實」,山本幡男的遺書早在他過世的那一年就透過管道被帶回日本,交在他家人的手中了。也就是當那六個受託背誦遺書的獄友,戰戰兢兢地將遺書的字句塞入頭腦的兩年間,這個任務已經不存在。
但「背誦遺書」的使命並非毫無意義,因為最後或許是這些話語帶著那些背誦者最終回到故土。他們乘載著另一個人的意志,生命的意義於是超乎自身的存亡,是這個「超然」的意義賦予他們生命原本沒有的力量。
遺書背誦的意義,並不是在被傳遞者本身,而是在那些閱讀之後的傳遞者身上。
在創作裡作者或許並不是主角,讀者才是。是那些閱讀並將所讀到的,作為自己生命養分的那些人,才是創作活動的主角。在「來自雪國的遺書」這個故事裡是如此,在所有其他的故事也是。
文字使我們所有人都成了作者,也都成了讀者。這是一個尊貴的身分,不管作為作者或讀者,都在「創作」這個活動中扮演著了不起的角色。
作為文字的愛好者,今天我也寫著自己的“遺書”,並且試著做一個盡責的讀者。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