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街头到广州乡下,我和酸面包的旅程
一、缘起
2018年,我在香港新界一个随时要被拆除的散村里,用刚从朋友那拿来的一罐发酵面糊糊,烤了我自己的第一个酸面包。现在回想起来,它其实没怎么发酵好,简直不能叫面包,可能叫“酸种大饼”更符合它的质地。我也记不清这个饼的风味和口感如何,只记得跟市面上卖的面包简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食物。
我很喜欢。
我所住的村子在新界北区,因毗邻深圳很早就被战略性划为新发展区。虽然大部分居民从祖父母辈就扎根于此了,但因为没有官方认定的土地和房屋业权,被政府视为无物,多年争取也无法撼动政府的发展计划。大学毕业后我带着单薄的同情来到这里,从斗志高昂的争取到全力打压后的低潮,在无从抵抗的大环境里,在末日随时临近的村子里,我们执着于生活里微小的事物,比如“照顾”一团面糊,它就能生长,每天贡献一点点酸种,让我们用它烤出面包来,是多么值得欣喜的事情呀。
那罐发酵面糊糊,就是“酸种”(sourdough starter)。谷物面粉加水,通过多次“投喂”,给予足够时间等待具有发酵力和不同风味的各种酵母菌和细菌落地扎根,相对稳定之后就得到了酸种。把酸种加入面团,发酵、切割整形再发酵、烘烤,就是酸面包。

我给乡村邻居送去酸面包。我们一起做了老面馒头(这在南方尤其是香港很少见),也相约在田边做了酸面包。现在想来她们未必那么喜欢酸面包,但对新鲜事物和新朋友的渴望,以及对充实健康的日常生活的向往,借由面包生发出来,让酸种和我们一样,进入了他们的生活。
酸种需要日常维持,通过按固定比例投喂面粉和水保持活性。投喂就是在给多样的菌群营造一个适切的稳定的生长环境。温度、水和面粉的比例、投喂的频率、面粉的种类……无数种排列组合,意味着无数种菌群,也带来无数种面包的风味。
香港的村落,某种程度上跟酸种菌群相似,无论香港其他产业的发展与衰落,村庄都能在都市扩张的洪流里野蛮生长,内里形成松散却仍有韧性的社群网络。零散的农地和中小型工坊是许多村民生活和生命的重要部分,老人相对能自力更生,不少壮年能在城市高压之外维持生计,无数生物有宝贵的栖息地——尽管从主流经济的计算方法来说,这些都不值一提。
这些乡郊地区有点像疏于投喂的酸种糊糊,会有风味奇怪没有发酵力的杂菌,不算生机勃勃,却也能做个面包出来,甚至偶尔意外地碰撞出特别的风味。
2019年,部分村民被迫“自愿上楼”(租住或购买有政府份额的高层公寓),数十年几代人自食其力的“野生”乡郊历史接近尾声。拆迁摧毁了营造自立式环境的可能,村民反被塑造成霸地谋赔偿的无赖。搬去高层公寓的村民成为真正意义的弱势群体,被迫依赖连锁店、社福机构、微薄的政府津贴和福利,却依然无法安居。


二、酸种小社群
介绍我认识酸种的朋友叫小兜。她早几年接触到酸种后十分着迷,狂热地喂养了许多种以不同谷物粉为食的酸种宝贝,并且积极与人分享酸种和在家轻松做酸面包的可能。在她看来,酸面包不应该只属于高档外国面包店,不是只有有海外生活经历的阶层可以接纳它,它可以是家庭主妇、繁忙打工族,或者任何愿意对自己日常生活多一些掌控的基层市民的生活的一部分。
相比即发酵母做面包,做一个酸面包很费时间。即发酵母是提纯的酵母菌,在合适的温度下,用它发酵,从和面到出炉,三四个小时足矣。如果用程序自动化的面包机,整个过程更是无需看管。
但做酸面包呢?和面之前要先准备活跃的酵头(levain),最短也要三四小时,然后和面,再经历两次发酵,到烘烤完成,大约六七小时。一个面包,花10个小时,谁有时间做呀?!
然而,当我们换一种想法,把做酸面包看做陪伴一群生命呢?在面包发酵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菌群,依环境不同或活跃或抑制,不同菌种此起彼落。如果我们营造恰当的环境(主要是温度),让菌群与我们的生活节奏相协调——比如我们没空照看就先低温抑制它们生长,把连续的10个小时按自己作息斩成几截,拉长到两天或更长时间。如此做酸面包就不是占用时间,而是与生活为伴。找到酸种跟生活切合的节奏,就可以自在享受孕育酸面包的乐趣了。
小兜的共学小组聚集了一群被酸面包吸引的朋友,大约每月聚一次,大家分享做面包和其他发酵食物的快乐,交换食材。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给身边的人做面包。尤其是2019年之后,伙伴们在荒缪和绝望中互相扶持,抓住一些生活下去的勇气。
三、商业面包店里的酸种
2020年,自己在家做了两年面包后,我决定去面包店打工,想看看更好吃的酸面包是如何做出来的,也开始考虑以做面包作为未来的生计。
我选择了我认为香港最好吃的酸面包店。跟很多以酸种、天然酵母为幌子卖高价速发面包的店不一样,这家店虽然是规模化生产,却实实在在地用酸种低温长时间发酵,从养种到出炉历时三天。
也不同于一两人的微型手工面包店,它有工场,分工序完成面包制作——这也是店主非常骄傲的一点——制作过程有许多不可控因素的酸面包,也可以规模化生产且品质稳定啊!
面包店的酸种非常健康,每日固定时间投喂,放在恒定的温度发酵,形成恰到好处的稳定风味。每天的配方和生产数量由店主修订后打印出来交给员工,员工按照固定流程操作即可。
店主尽力将一切变量考虑进去,让生产过程中的不可控因素降到最小。他要求员工在关键步骤拍照向他报告,比如和完面的温度、入炉前的面团等等。员工是面包店最不重要的元素,只要有手有脚能听懂人话就行。很难说是因为员工毫无价值,所以店主就更努力地让一切可控,还是因为店主追求一切可控,才让员工毫无价值。


在那里工作了五个月,我精疲力尽。体力上的重负是次要的,主要是我无法吃那的面包了。闻到烘烤的香气让我紧张作呕,好像回到了那个满是责备和抱怨氛围的工场。我仍然觉得那店里的面包十分出色,只是没法再吃一口了。
做面包的人不快乐,但吃面包的消费者完全不知情,也可能不在乎,因为面包店撇开工场的工人,重新塑造了面向客人的气氛和价值。我不能否定面包店作为推广好的酸面包给公众的价值,但很显然,我没办法继续参与制作这样的面包了。
更糟糕的是,之前做面包跟人分享的快乐找不到了,总觉得自己面包做得不好。这段时间一起住的狗狗们帮着吃了很多面包,以至于她们看见面包就扭头了。太沮丧了。
四、走上街头的酸种
2019年之后,加上疫情,许多人不再相信建制了,但行动自由度缩窄。“不如去地铁站外面卖早餐面包吧!”因局势被迫中断稳定工作的朋友这么提议。
位于乡郊的地铁站外有一块空旷的场地,一部分是政府规划的货柜屋组合成的假日小贩市场,毗邻的空地经常有阿姨阿婆摆卖自家农产甚至宵夜小吃。尽管自发摆卖是不合法的,疫情限聚令和强制口罩令之下,规管也更严苛,但碍于生计铤而走险的人们更多了。
出于“反正自己要练习做面包的,能有人吃甚至出钱买当然更好”的心态,我们就揣着面包走出去了。疫情之下,对健康和食物的关注让更多人知道酸面包,也借着人们对年轻人的同情和支持,我们一开始就有一个非常宽松友善的售卖环境。
面对面售卖,信任很容易就产生了。除了酸面包和甜点蛋糕,也有喜欢手冲咖啡的朋友来客串。我们也会把酸种带出来分给有需要的人。
疫情期间,戴着口罩的人们竟然也接受我们完全不用预包装,现场把面包装进纸袋,人们甚至不顾法令,摘下口罩,一边吃面包喝咖啡,一边聊天说笑。
除了卖面包,混迹于阿姨阿婆档是更令我们兴奋的事情:互相帮忙销售,或者叫对方帮忙品尝新产品,或协作跟来”扫荡”的政府部门捉迷藏。

五、迁移的酸种,向往的社群
我在疫情解封前从香港回到内地,带着酸种经历了一周的隔离。秋天的岭南,气温也超过25摄氏度,酸种在这个温度至少得一天喂一次。出发前我把酸种放进塞了冰袋的保温盒里,带上足够投喂份量的面粉。每天投喂不成问题,怎么处理每天多出来的酸种比较麻烦。也就是在隔离期间,我竟然有了突破,用酸种蒸出不酸的馒头来代替要命的隔离餐。
那是解封前最紧张的时期。隔离一结束,我带着狗狗投奔广州乡下,去探访从化银林村的酸面包工坊。在这之前,我对做面包要用怎样的食材有很多想象却没有充分的实践经历。既然在用对待一群生命一般的态度来对待酸种和面团,自然要用无添加或有机的面粉。但当看到银林的“吃土工坊”全部用国内生态小农面粉的时候,还是挺吃惊的。进口的有机面粉并不比国内生态小农面粉贵,而后者状态更不稳定且跟欧洲面粉有很大差异,要做出品质相对稳定、跟得上传统欧包标准的面包就更难了。


工坊的面包风味并不特别,但透着平和、日常的力量,不知不觉就会成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成为会不时想念的食物。在生态良好的乡村,做面包也是用山泉水,这都是以前未能体验过的。
更幸运的是,工坊就设在银林生态农场里,把农场的出产恰到好处地融进面包里也是稀松平常,比如糙米、荔枝干、番薯、柠檬等等。我感觉到,小农的生态面粉、生态蔬果等等都不是单纯地拿来替换普通食材,而是面包的主体。做出来的绝对不是只换了食材的市售面包的翻版,而是焕发着工坊所在土地的生命力的独具神韵的面包。
村里就有酸面包的日常消费者,大家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以面包交换自家食材、手作,工坊协同孕育着酸种,酸种孕育着包含人与其他生物的社群。
在这里,我用完了之前用惯的德国面粉,也开始用国内小农生态面粉投喂酸种了。之后,我带着承载着力量的酸种,回到陌生的出生地,希望能发酵出新的社群和关系,一起造出彼此共生的自在生境。

食通社是一个可持续食物与农业的知识、信息和写作社区,由一群长期从事农业和食物实践及研究的伙伴们共同发起和管理。我们相信,让消费者了解食物的来源,为生态农业从业者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和社会环境,我们的食物体系才能做到健康、美味、可持续。
微博/豆瓣/知乎:食通社
微信公众号:foodthinkchina微信小号:foodthinkcn
官方网站:www.foodthink.cn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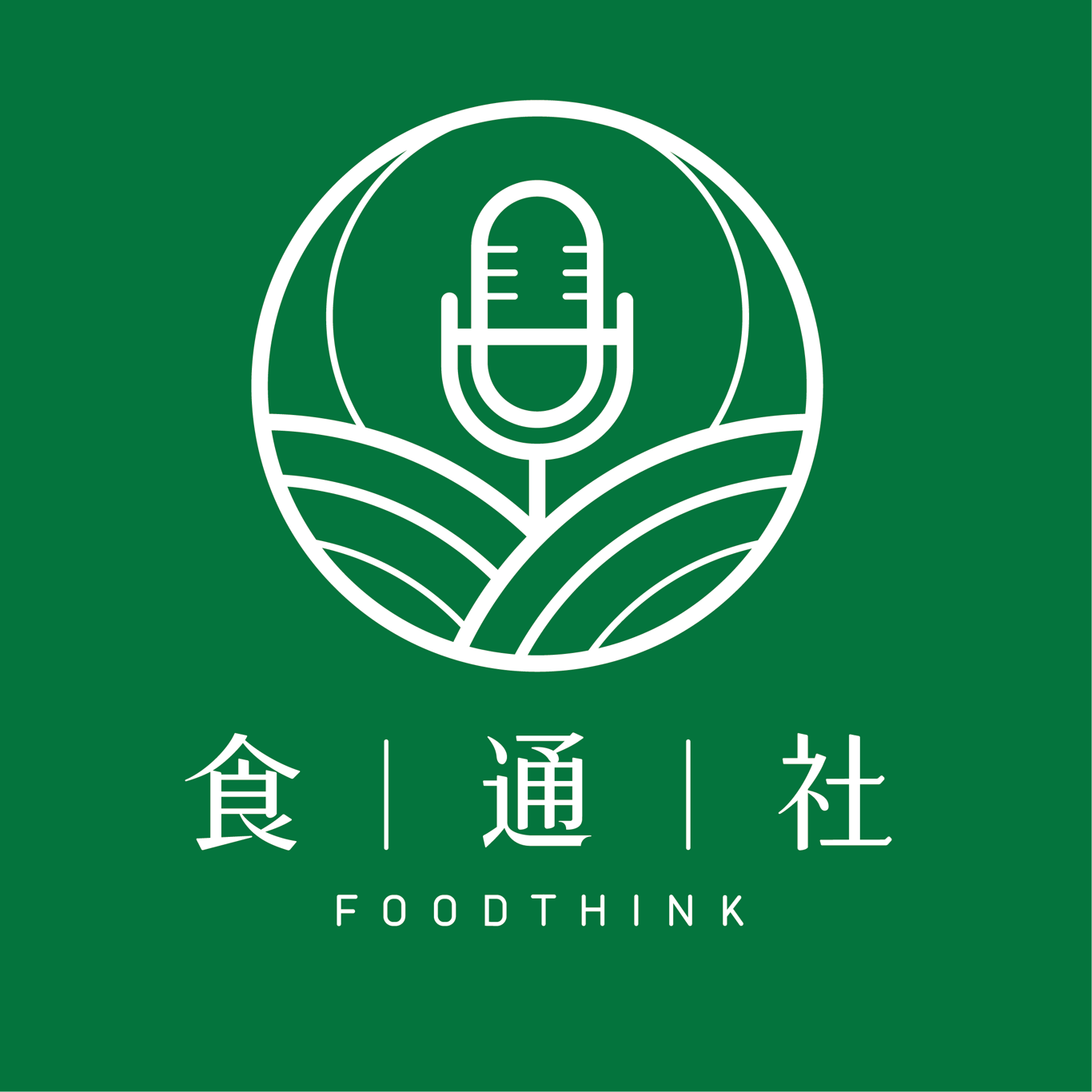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