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隐居南亚深山的前驻阿富汗教育学家的两次对话
第一次见到 Michael 时,我以为他又是一个在西方社会混不下去,跑到亚洲娶年轻老婆的白人鲁蛇。
2019 年夏天的斯里兰卡,刚经历了震惊全球的 “4·21 恐怖袭击”(2019 年 4 月 21 日,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等多地先后发生 8 次连环炸弹袭击,造成至少 253 人死亡,500 人受伤。事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对事件表示负责),国家经济和旅游业进入了萧条状态。时隔五年,我第二次来到这个国家,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原因一是游客少,原因二是经验告诉我,在特殊时期,必定会遇到很多计划之外的人和事。

在南部的海边城市待腻了,一天我在翻 Airbnb,突然看到中部山区有一个点:方圆 20 公里内没有任何市镇,没有一条住客评论,一座带花园的别墅,只要 80 人民币一晚。如果你是穷游背包客,在东南亚住过 5 美金一晚的混间床位,就一定能想象,当我看到 80 人民币能住一个别墅时有多激动。
第二天我离开南部,火车转巴士,来到中部。还没到住的地方,一股鸟不拉屎的气息迎面扑来。Tuk Tuk 司机一脸茫然、半信半疑地把我放在半山腰的一个分岔口,虽然我们无法用语言顺利沟通,但他的眼神告诉我:我是第一个来这里的游客。

顺着入住提示,跟几个刚好路过的村民鸡同鸭讲、比手划脚一轮后,终于见到我的房东:一对皮肤白暂、英文流利、脚穿运动鞋的斯里兰卡老夫妻。从肤色和穿着不难看出,他们来自斯里兰卡的最高种姓。果不其然,他们世世代代都是贵族,千金结婚时还请了前总统,合照被挂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

接近傍晚,房东太太说:“你是我们村子第一个游客,来!我带你去串串门。”于是她带着我,绕着山道,挨家挨户喝红茶,吃水果。走了一圈,准备回家吃晚饭,房东太太突然说,啊,Michael 他们应该回来了。
房东的大房子旁边,有另一个大房子。我们按了门铃,一个 7 岁左右的小男孩出来开门,房东太太用力地亲了下他的脸颊。门后站着一个目测 60 岁左右的白人男性,我马上意识到他就是房东太太口中的 Michael。他看到我,像我看到他一样,显然,我们都没有想过在这里还能见到第二张外国面孔。一番闲聊后,我们终于要回家吃饭。席间,我跟房东夫妇提到我在国内有做一些跟性别权益有关的项目。
晚上我在房间,准备睡觉,房东太太来敲我的门,递给我一本书说:“Miki,我觉得你会对这个感兴趣,这是 Michael 的书,里面讲的是很多年前,他在阿富汗帮助女性和小孩的经历。”

当时我就愣住了,后脑勺发麻:住进贵族的祖屋,还有一个去过阿富汗援助的邻居。毫无疑问,这是我花过最值的 80 块!
第二天,还是接近傍晚,我拿着书,再次来到 Michael 家,向他郑重其事地介绍了自己,表示想知道更多关于阿富汗的事。眼前这位满头银发的男人笑了笑,说,让我想想要从哪里开始说起。
听说我来了,Michael 的太太搬了两张椅子到花园里,孩子们也跑出来,递上红茶和饼干。
作为交换,我也请对方郑重其事介绍下自己。
“我叫 Michael Hirth,来自德国,是一名教育学家。像你看到的那样,我结了婚,有三个很可爱的孩子。”
“1993年,我第一次被派到阿富汗,那个时候我刚加入BEFARe(Basic Education for Afghan Refugees,1989年由巴基斯坦和德国共同达成关于基础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双边合作项目。其服务范围主要包括教育、卫生、生育、妇女赋权、民主、能源等)。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救助机构,BEFARe 的救助对象,光是难民儿童,就超过了 10 万名。当时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为难民儿童提供基础教育,比如识字和算数。除此之外,由于大多数难民来自普什图语地区,BEFARe 还有普什图语扫盲项目。在接受了两年的课程后,我们的学生基本可以达到阿富汗国内的平均文化水平,参加扫盲课程的人可以进行基本的读写,满足他们在现代社会的生存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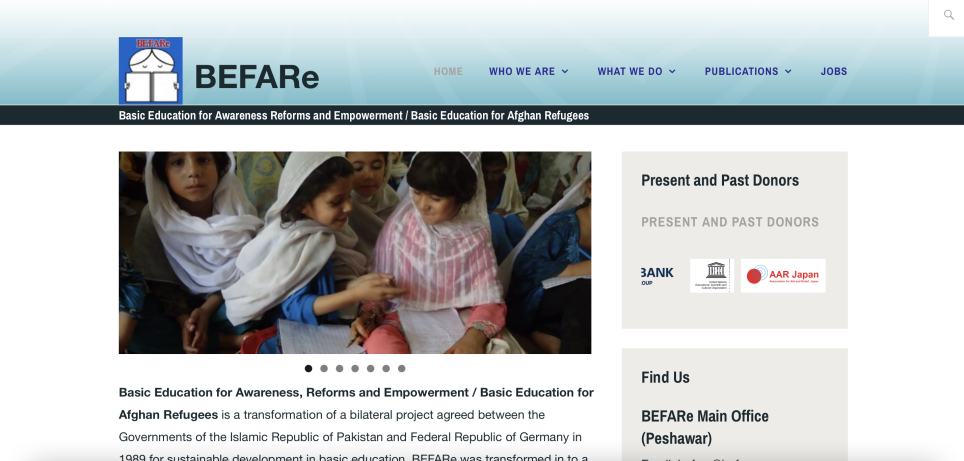
“我在 1995 年成为 BEFARe 的首席。2005 年,以 GTZ 教育项目的首席身份,第二次到阿富汗,一待就是 6 年。”
“GTZ(German Technical Cooperation,已于 2011 年正式改名为 GIZ,Germ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主要提供教育/职业培训、农业、法律、警察培训等援助。现在的 GIZ 是一个在全球 130 多个国家拥有约 18000 名员工的政府机构。因为联合国难民署和 GTZ 资助过很多 BEFARe 的项目,尤其是非正规教育援助项目(NFE,Non-Formal Education,指正规环境之外进行的任何形式的系统学习),所以 BEFARe 跟联合国关系一向非常紧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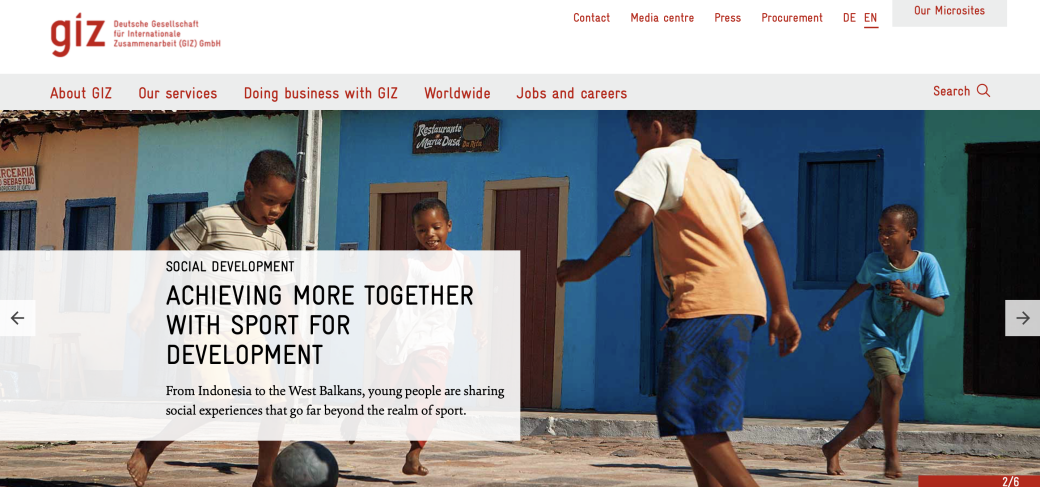
“阿富汗内战(1992年-1996年)期间,首都喀布尔在内的好几个主要大城市,包括附近的偏远地区,都被战火严重摧毁。将近 300 万阿富汗人逃到巴基斯坦。出于安全考虑,BEFARe 最大的办公室设在巴基斯坦北部的白沙瓦,只留了一些小的分部在阿富汗(主要在喀布尔)境内。”
Michael 喝了一口茶,接着说:
“我第一次到阿富汗,战火纷飞,加上管理不善,整个国家非常混乱。还记得有几次在喀布尔的夜里,圣战组织相互炮击,那个场景太可怕了。难民们的命运注定是一场悲剧。有一次在冬天,大概有 5 万名难民在一夜之间涌入巴基斯坦,他们需要足够的食物、温暖的衣服,和一个避难所去抵御寒冬。5 万人!当时现场让人非常绝望,每个人都紧紧地抓住家人的两只手,防止在混乱中跟对方走失。”
这里,Michael 用了一个词:hell。“当时的阿富汗,跟地狱没什么两样。”
“永无休止的内战使塔利班有机可乘。90 年代中期,塔利班进入国际舞台,并且以极快的速度,迅速占领了阿富汗。事实上,在塔利班入侵期间,一些情况曾出现过好转:进入巴基斯坦的难民数量不再上升,一些难民家庭甚至决定返回阿富汗,因为他们觉得,塔利班能够在几周内停止内战。”
听到这里,我皱了皱眉头,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塔利班组织的正面言论。我问Michael:“你的意思是,事实上塔利班的占领,在当时,某种程度上是对阿富汗有利的?”
“是的。”
“我第一次遇到塔利班是在 1996 年,那个时候 GTZ 在霍斯特(位于阿富汗东南部,邻近巴基斯坦边境)开展了一些职业技术培训项目。由于塔利班不反对技术类的培训,并且比较看重旧阿富汗政府从 60 年代就建立起来的与德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所以负责管辖霍斯特的塔利班分子对我们的工作比较配合,没有干涉任何德国主导的项目,甚至对我们在霍斯特市内和周边的项目场地,进行维修和保护。”
那你个人有与塔利班正面交锋过吗?我是指那些危险的情况,还是想听一些符合我印象中塔利班邪恶形象的真实故事。
“当然有。”
“我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任职期间,曾经跟塔利班成员多次面对面交涉。那个时候人们只能经喀布尔进入霍斯特,所以我都是前一晚在喀布尔的一些挪威人开的宾馆里过夜,等白天再前往霍斯特。”
“有一个晚上,外面正下着大雪,屋里头非常冷,我正围着火炉取暖。突然听到有人非常用力地拍打我的门。几个塔利班的头目打听到我在喀布尔,于是连夜找到了我。他们表示,想要跟我 “商议”(discussion)一些事,但我知道这话中有话。出于好奇心,并且考虑到如果表示拒绝,很可能会激怒他们,因此只能跟他们走。”
“他们开车把我载到总统府外面,对我进行全身搜查,并把我带到一个更大的房间。房间里挤满了留长胡须的男人,他们披着传统长袍,戴着头巾,穿着马甲和四分裤,每人手持一把 AK-47 自动步枪,就像你平时在新闻里面看到的塔利班分子一样。”
“他们的首领用流利的英语向我介绍了自己,他曾经是塔利班的 ‘独眼领袖’——穆拉·奥玛尔(Mullah Omar,塔利班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几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在 911 事件之前多次为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提供庇护)的顾问。他问了我很多关于 GTZ、联合国、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问题。他们对 GTZ 是一个政府机构,而不是 NGO 这点表示很惊讶。途中,他们给我递了一杯茶和一些饼干。然后又问我,能不能帮他们开发天然资源,像黄金、宝石,或者锂这类原材料。我向他解释,我是一个教育学家,不是地理学家,可以向 GTZ 总部发一个需求,派遣一位地理学家过来协助他们。”
“我们喝了很多茶,有说有笑,但同时我也感受到,他们全程用诡秘、怀疑的眼神打量着我。到了晚上 10 点,我提醒他们宵禁时间到了,我该如何回去宾馆。这一问,引起一些小混乱。我猜他们一开始就并没有打算放我走。但最后他们还是给我安排了一辆雷诺。礼节性地握手拥抱后,在几个成员的陪同下,我被带离了那个房间。他们把塔利班的旗子挂在车窗,一路上反复交接暗号,通过了所有的检查站。”
“那个夜晚,一切看似非常顺利,但这不意味着我可以轻视塔利班这个对手,因为他们多数成员是宗教强硬派,冷酷无情,极端地信奉和执行着伊斯兰教法。”
Michael 跟我说起这些细节时,语速很慢,没有中断,有时陷入短暂回忆。眼看天快要黑,山里厚重的雾气慢慢升起,想着还要准时回去跟房东一家吃晚饭,我问出了这次拜访最想问的那个问题:塔利班是怎么迫害女性的?
“在霍斯特,妇女和女孩被严厉禁止去上课。塔利班会在主麻日(Jumu’ah,也叫Friday Prayer,穆斯林于每星期五举行的聚礼)向信徒发出这种严厉的警告。如果有女教师进行公开授课,或者女性去公立学校上课,一旦被塔利班发现,最恶劣的情况,老师和学生都会被处以石刑。”
“当时有一些勇敢的女教师会进行秘密授课(secret lessons)。为了躲避塔利班,他们用碗橱把‘教室’的入口封起来。入口不大,每次只能让一个人通过,要进入教室,必须把碗橱移开,爬进一条地下通道,从教室的后方进去。当时大概有 10 个这种教室分散在镇的各个角落,整个上课过程不能发出任何响声。这种秘密教室搭建的结构非常脆弱,我每次都会犹豫到底要不要进去,因为看起来随时会坍塌。有时候过来上课的人会多一点,有时候会少一点,这个取决于当时接管这个辖区的塔利班的强硬程度。我的同行人告诉我,有一个担任要职的塔利班成员的女儿也是这种 secret lessons 的学生。”
“塔利班组织相对比较尊重这种专门针对女性开设的非正规教育课程,我甚至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去参观女性上课,因为这种形式有点像伊斯兰学校(Madrassa,指伊斯兰世界所有类型的学校,包括世俗和宗教学校):在树荫下上课、没有固定的年龄分组(通常是孩子和成年人一起学习)、没有固定的课程时间,学习的内容依据当地习俗制定。联合国和 GTZ 是项目主要的资助者。如果没有资金,这些项目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
“2005 年我第二次到阿富汗,看到整个教育体系有了非常大的改善,一些女子学校重开,这点让我非常欣慰。尽管农村地区的教学质量仍然不尽人意,教室通常只给男孩用,女孩只能坐在外面的树荫下听课。”
多年后,斯里兰卡内战(1983年7月23日-2009年5月18日)后期,Michael 被 GTZ 派往北部的贾夫纳,为女性和儿童提供非正规教育援助项目。故事的最后,他留在了这个印度洋的小岛,并组建了家庭。

我在山里住了一周,临走前,问 Michael 要了他的邮箱,而房东太太则送了我一条她娘家传下来的项链,“拿着它,你会再回来的。”

回国后,我跟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8 月中,塔利班接管阿富汗的新闻铺天盖地而来,历史再次重演,令我又想起了 Michael。于是我给他发了邮件,只问了一个问题:
今天的塔利班,对阿富汗来说,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
Michael 站在一个教育学家的角度,给出了他的答案:
“在这一点上,我是持有质疑的,因为我看到,今天的塔利班和昨天的塔利班,本质上是一样的:认为妇女不应该拥有权利、殴打妇女、不让女孩接受教育、根据伊斯兰教法惩罚人民、对他们执行石刑。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是吃素的。塔利班非常聪明,深知如果不运用点国际外交手段,就不可能长期统治。2001 年美军进入阿富汗后,很多教师重返阿富汗,把现代教育思想传入阿富汗。从那时候开始,阿富汗人民的思想发生了巨变,人们开始学习和寻找民主价值观,这使得新的一代人开始涌现,正是这些青年,上周在贾拉拉巴德(Jalalabad,又称 “光辉城”,于 8 月中先于喀布尔被塔利班接管,后发生了多个有人员伤亡的反塔利班游行)和全国各地示威反对塔利班。塔利班很清楚,他们不能忽视 911 后的这 20 年,否则必须得消除掉整整一代人,这对他们来说代价太大。”
“有一点是很肯定的,阿富汗战争这 20 年间,西方国家的 ‘洗脑’ 只成功了一部分。如果不是得到了大多数阿富汗人的支持,塔利班是不可能在仅仅几个星期,甚至几天内再次占领阿富汗,这个速度是我不敢想象的。在新闻报导上,也能看到塔利班在一些村庄和城镇是如何受到民众欢迎的。这是为什么?”
“众所周知,阿富汗是宗教国家,阿富汗人都是信徒,他们极度笃信宗教,这一点一直被西方社会无视,甚至践踏。2005 年我第二次来到阿富汗时,三分之一的电视频道都在播放色情片,这让我感到十分震惊。很多民众对这种来自现代社会的新的生活方式是不接受的。”
“对于一个 70% 人口都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国家来说,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塔利班的统治是依据当地的习惯和规章的。如果阿富汗人在法律上想要按照西方的方式解决一个案件,必须等个好几年,他们的案件才会被处理。塔利班不一样,他们遵循普什图瓦里(Paschtunwali,普什图人的传统民族价值观,由族人祖传的生活规范演变而成的道德、社会及法律制度,在偏远山区部落被广泛奉行),跟可兰经一样,能让他们高效管理一个辖区。”
“西方军事力量对信仰的忽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错误,也是不可原谅的。”
“所以,让我们静观其变吧,塔利班会否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这个问题谁也没法给出答案。现在塔利班重新掌管阿富汗,必将是国际局势上又一次激进的历程。”
“无论如何,让我们齐心面对他们吧,We are strong enough。”
(笔者声明: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受访者本人观点。)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