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的注释学与现在
江户的注释学与现在 江戸の注釈学と現在
柄谷行人
「江戸の注釈学と現在」是柄谷行人在1985年11月1日于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会发表的演讲,演讲词后收入『言葉と悲劇』一书中。
1
最近,大家总说掀起了一股“江户热潮(プーム)”。诚然,我是写过关于江户思想家的文章,但我的研究与这种“热潮”关系不大。不过,我大致能理解为什么现在会出现“江户热潮”,甚至也能预见这种趋势的走向。其实在战前,也就是昭和十年代,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江户热潮。当时,不仅本居宣长和国学的研究被重新关注,还有“时代小说”非常流行,甚至“时代电影”也广受欢迎。这里所谓“时代”,显然指的是江户时代。但有趣的是,这些作品并不是因为人们对历史有多大的兴趣,反而是因为对历史的关注减少,甚至对社会的闭塞感,才催生了这些“时代小说”的出现。换句话说,这些作品更多是在江户的影像中投射出现代的情绪,而不是单纯为了追溯过去。
这种风潮与“近代的超克”的口号所代表的思想倾向并非毫无关系。例如,九鬼周造的《“いき”的构造》(『いきの構造』)[通行中译いき=粹是有误的,见下文]可能是第一次尝试给江户后期日本人感性和生命形式赋予哲学意义的作品。但这也是在“近代西洋的超克”的课题中所找到的“江户”。简单来说,江户潮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历史意识的封闭。这可以换成“历史已经结束”的意识。人们不再拥有什么必须要达成的目标。在战前,这种状态是马克思主义受压制和崩溃后的状态。第二,与此相连的是,在封闭的空间中试图自给自足的倾向。这种自足感并不是排外的民族主义,而是认为西方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学习的东西。
当前的江户热潮基本上与此相似。也就是说,它与所谓的后现代主义(ポストモダニズム)的倾向有着紧密的联系。虽然没有遭遇过某种压制(弹圧),但人们已经不再为“历史到达某个目标或拥有必须实现的目标”而动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已经结束”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浸透人心。此外,这还与“消费社会”密切相关。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并非在生产一些实质性的东西,而是似乎仅仅在创造差异=信息。而且,日本人现在开始感觉,西方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再学习的东西,甚至开始觉得自己走在了前沿。
我之所以决定研究江户的思想家,是因为这种倾向变得越来越明显。当我在思考昭和十年代的“近代的超克”时,我觉得我必须追溯到江户时代。因为像小林秀雄、保田与重郎、西田几多郎、九鬼周造等人所依赖的,归根结底就是江户的思想。如果不检讨这些思想,我们也注定会重蹈覆辙。换句话说,江户思想中是否有某种形式,尽管我们自认为在追求新颖,最终却不得不回归到这些形式?我想思考的正是这一点,江户思想中的某种形式是否以彻底的方式显现出来,且它是如何形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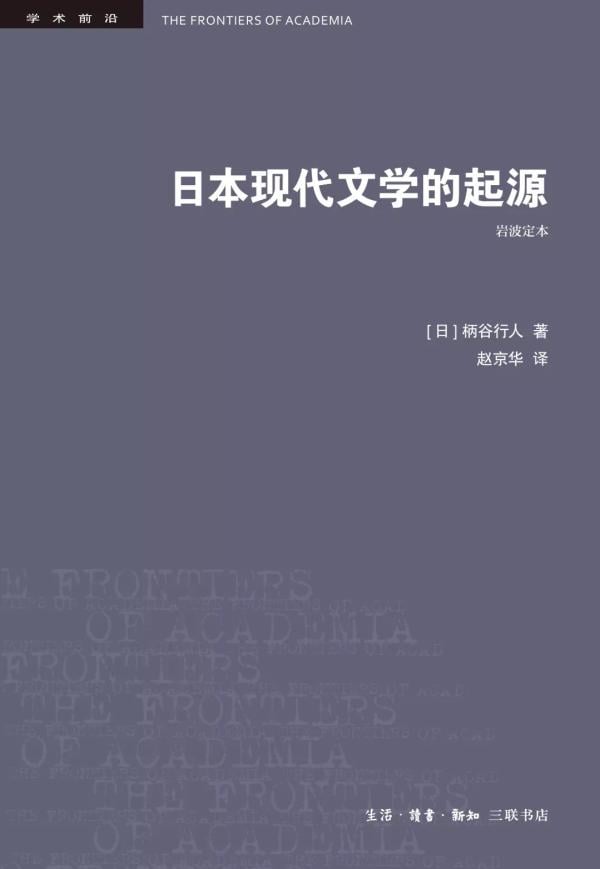
我之前写过一本《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在书中,我讲述了“现代文学”(近代文学)在明治二十年代的某种“颠倒”(転倒)中诞生,但明治二十年代按西历来说就是19世纪末。因此,日本的现代文学,基本上是属于20世纪的文学。
换句话说,我们仍然身处于不到一百年的现代文学之中。如果抛开政治体制和经济关系不谈,在感性和生活方式等领域,19世纪对日本来说几乎等同于江户时代。而且,这个时期并非某种需要被现代化的、未发展的落后状态,实际上,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完全被精炼的,达到了一个无法再进化的高度。日本现代文学,或者说现代意识的形成基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封建社会或滞后的阶段,而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彻底的存在,具有无法超越的某种特性,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所做的,是指出我们所认为理所当然的“文学”和“内面”这样的概念,实际上仅仅是在19世纪末才形成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要否定“现代文学”或“现代”本身。我想表达的只是,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一状态,并非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观念而已。
进入1980年代后,我开始觉得自己过去一直在与之搏斗的东西似乎发生了反转。因为“现代文学”一直以来所珍视的东西,比如“内面”和“深度”(深さ),开始遭到人们的嘲笑。我在那里看不出任何意识形态。现在存在的,恰恰是日本现代文学从中诞生出来的19世纪的江户。这并不是回归日本的传统,而是当下的状态,仅仅揭示了过去80多年的现代意识或制度的地基。
我提到“19世纪”,但通常我们会把它称作江户时代、元禄、文化文政时期等。然而,我想特意用西历来称呼。理由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使用西历可以让我们摆脱像明治或大正这些时代标签所附带的含义,能够以一种不受这些定义束缚的视角来看待事物。顺便提一下,西方哲学的讨论通常会涵盖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到康德和黑格尔等17、18世纪的哲学家,今天依然常常被作为同时代人物讨论。这不仅仅是历史研究,而是把莱布尼茨、斯宾诺莎作为与我们同一时代的思想来阅读。尽管他们是西方人,但我们并不觉得他们与我们有太大的距离。可是当我们提到江户时代时,日本18世纪的思想家们,却被视为与我们毫无关系的远古人物。像伊藤仁斋、荻生徂徠、本居宣长这些思想家,完全变成了陈旧的存在。这是非常奇怪的,也是不公正的事情,不是吗?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江户时代”这样的划分固定化,暂时把“文化文政”这一称呼抛开,干脆称其为“19世纪”可能更好。
在日本,近代化始于明治维新,但文学的进展大约在三十年后。因此,在日本,19世纪几乎等同于江户时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19世纪,那正是九鬼周造所说的“いき的构造”。根据九鬼周造的定义,“いき”是“使可能性之为可能性的将可能性绝对化之状态”。换句话说,它是指在某个阶段停下,不去追求超越。蓮實重彥曾说过,“在深度的诱惑中,停留在浅薄的地方”,我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粹”的结构。
在近代文学中,“いき”——北村透谷将其称为“粹”(粋),但实际上,对“粹”的批判正是由北村透谷首先提出的。比如在《论粹与“伽罗枕”》(『粋を論じて「伽羅枕」に及ぶ』)或《厌世诗人与女性》(『厭世詩家と女性』)这类评论中,透谷主张“いき”的时候,他强调的是“恋爱”,即司汤达(スタンダール)所说的那种激情之爱(情熱的恋愛)。透谷虽然是基督徒,但“恋爱”这一观念在明治时期(恰恰)是围绕教会传播开来的。基督教会,尤其是新教教会,是男女可以平等相处的地方。因此,教会实际上是与明治社会的现实情况有所脱节的一个特殊场所。以这个场所为中心,恋爱这一概念得以扩展,透谷等人也是其中的代表。恋爱成了一个新兴的观念。
顺便提一下,虽然我说以基督教会为中心,但实际上“恋爱”这一概念与基督教本身是对立的。鲁热蒙(ルージュモン)甚至认为,“恋爱”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的异端(如清洁尔派[カタリ派])。透谷很快放弃了基督教,他转而依赖于美国的超验主义思想,特别是爱默生的思想。爱默生认为神并不是一个人格化的他者,而是内在于每个人的超越性。既然它是内在的,那么每个人都能到达它。透谷认为,“恋爱”是一种与异性之间的爱的合一。
从“いき”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完全是“庸俗”(野暮)的。因为“いき”就是比如说,是要求某个姿态,比如如果是媚态,就要停留在媚态本身上,而不应去实现它。而且,不应当因为未能实现而感到慌乱,也不能绝望。这些都是“庸俗”的表现。如果“いき”是让他者保持在无法到达的超越性状态的话,那么透谷的超验主义中所展现出的“庸俗”或“野蛮”正是显而易见的。
近代文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从“恋爱”开始的。例如,在夏目漱石的作品中,无论是三角关系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都变成了“庸俗”的极致文学。可能与此潮流有所偏离的,是永井荷风的《濹东绮谭》(『東綺譚』)或川端康成的《雪国》之类的作品。这些作品大约出现在昭和十年左右的所谓“文艺复兴期”。也就是说,这些作品与前述的昭和十年代的江户潮流紧密相连。总的来说,江户文学或19世纪文学最终到达的是什么状态呢?可以说,那就是永远不会达到超越的境地,而是在这个边缘停下来。这种状态可以理解为“意气”十足的放弃。如果与此相比,近代文学则完全是庸俗且野蛮的。因为它总是在试图达到某种状态,拥有目标和终极,必须不断朝着那个方向前进。
然而,17世纪到18世纪的“江户”与19世纪的江户有所不同。它反而表现出“庸俗”的特点。思想家们也是如此。然而,“江户”被讨论时,通常指的是19世纪的江户。在西方,尤其是在法国,所谓“日本性”的概念,实际上完全是指“19世纪的江户”。
这在印象派画作中尤为典型。如果你读梵高的信件,他多次提到自己希望像日本人一样看待事物。他虽然说自己是日本人,但实际上他只了解绘画。并且,他所了解的绘画显然是“いき”阶段的画作,而不是元禄时期的画作。也就是说,他所理解的“日本绘画”其实是19世纪的绘画。梵高所说的“想像日本人一样看世界”,实际上指的是19世纪前,西方人通过某种洗练的阶段达到了极致。他们通过“19世纪的日本”来发现了西方“19世纪”的某些表现。
而印象派和梵高把这种画作当作“日本”的表现,而非江户时代的表现,他们对此的激动可想而知。对于他们来说,“西方现代的否定”的一个重要契机正是来源于日本。而一百年后,当前的后现代状态与我们重新发现江户,重新发现“19世纪的江户”是紧密相连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重新理解“江户趣味”,无论是永井荷风还是九鬼周造,实际上都是“西方的日本趣味”的媒介。
罗兰·巴特曾为日本写过一本书《符号帝国》(『表徴の帝国』)。在书中,他所提到的“日本”的实例,完全是19世纪的日本哦。因此,对于巴特来说,“日本”基本上也就是19世纪的日本。西方人感兴趣的是后期的江户,实际上,他们把它称作“日本”也是可以的。就像科耶夫等人一样。我们可以将其批评为“东方主义”。因为它不过是将西方本身所面临的问题投射到“日本”这一镜像上而已。然而,当我们看待现在的日本时,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这种观点。
过去,我们或许可以说,西方人只是随意地说出这些看法罢了。但现在,我们不能这么处理。因为在今天的日本文学和思想领域,简单地用“后现代”来形容是完全可以的,尽管这看起来像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或者像是处于高度资本主义的阶段,然而与此同时,它也展现出了一个只不过在过去大约八十年的时间里才出现的现象,那就是江户文学的暴露——即表层的皮被剥开,江户文学的本质露了出来。
文化文政时代的文学,语言游戏和文字的嬉戏占据了主导地位,通常被称作讽刺(パロディ)或俳谐/插科打诨(駄洒落)。并不是“深度”(深さ),而是“浅薄”(浅さ)如轻浮、简短小巧的风格占据了主导地位。比如,广告文案作家糸井重里创作的“万流”,其实是对川柳的模仿,而川柳本身也是19世纪的产物。可以说,在整个19世纪,人们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田中康夫做的事也差不多。像是妓院的目录一样,关于如何打扮、如何举止、什么品牌更好之类的书籍已经大量存在。曾经,正宗白鸟曾称这一时代为“白痴的天国”,但无论如何,简短且轻薄的事物,在19世纪的日本达到了顶点。今天,我们所做的最前沿的事,在一个世纪前其实就是司空见惯的东西。
如果说“轻盈”(軽い),那么,在当代文学中,语言确实变得轻盈了。这种轻盈,可以说是从“意义”这一枷锁中解脱出来的轻盈。例如,今天几乎没有作家再提到“自我表达”了。大约二十年前的文学中,仍然存在可以称之为“自我表达”的东西。我认为,自北村透谷以来,虽然存在可以与“自我表达”相混淆的东西,但如今的作家已经没有这样的东西,想要去阅读这种东西的读者也没有了。
说到“轻盈”,顺便提一下,它也表现为相对于现实的“轻”。现实主义,也就是作为现实再现的语言,已经不存在了。对于承载“意义”或“现实性”的语言,现今文学的发展似乎在不断地否定它,或是嘲笑它,甚至反过来将其一一无效化。简而言之,语言变得极端轻盈,变得更浅薄,开始摆脱意义的沉重负担。从消费社会的角度来看,比如“群众形象”是什么样的等等,当前有些书籍讨论这一点。即便称之为消费社会或信息社会,但像今天的日本那样极端推进的地区是少数的。西方绝不会发展成这种程度。
这意味着,在日本,语言开始承载意义、真理或对象的沉重负担的时间,其实距离现在不过八十年左右。前面提到的透谷就是一个例子,近代文学中,语言第一次开始承担重负。而在日本的19世纪文学中,语言根本没有这种负担,它是空洞的。直到18世纪末,虽然在被称为“戏作”(戯作)的文学中,某些作家还比较自觉地做到了这一点。戏作作家几乎都是团体的人,一方面他们具有知识分子的意识,另一方面又通过将这一意识作为笑柄来否定它,可以说这种批评的意识依然存在。
然而,一旦进入文化文政时期,即19世纪,这种批评的意识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简单的轻松。仅仅成为了戏作。结果,真正的文学——即不是戯作的文学——也消失了。至于现在的日本社会是否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不太确定,但我感觉,现代文学的紧张感已经不复存在。大约到1970年代,戏作的意识曾经带有很强的破坏性,但到了1980年代,这一意识彻底变成了单纯的戏作。
2
那么,现在的日本,后结构主义和解构(ディコンストラクション[脱構築])已经成为了一种知识时尚。当然,我自己也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自己的理解,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然而,近年来,在这些潮流中,我不得不开始思考一些不同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我在《批评与后现代》(批評とボスト·モダン)中有一定的写作。我所讨论的是,当前思想的前沿问题,按照德里达的语言来说,后结构主义表现为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但这种西方思想的批判在日本已经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反而被作为一种熟悉的东西接受了。西方最前卫的思想回过头来看,对我们日本人来说,反而显得自然,似乎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我认为,刚才提到的知识风潮便显示了这一点。
战前被称为“近代的超克”的各种意识形态中,反思西方的西方思想被吸收并消化了。这个过程进行得太过轻松了。今天日本的后现代主义,也有着这样的趋势。而从世界的全球化趋势来看,日本的后现代主义最终可能会回归到“近代的超克”的各个派别的再版。然而,“近代的超克”的那些人依赖的,实际上是江户的思想家。例如,小林秀雄的毕生工作,大家都知道是《本居宣长》这本书。
而西田几多郎,则试图将禅在西方的逻辑(論理)中进行阐述,有人认为这是日本唯一的原创且系统性的哲学。但是,若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朱子学反而更具有原创性和系统性。事实上,西田哲学与朱子学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都起始于禅,并且都试图涵盖一切事物。江户时期的哲学家们,曾试图批判朱子学。而他们的批判采取了注释学(注釈学)的形式,因此它是无法成为一个系统的哲学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不是哲学,也并不意味着它不包含思想。说到这一点,如果在西方,像维科、尼采、卢梭和基尔克果等人都没有哲学体系,那么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他们不是哲学家。马克思也没有留下体系,他也就不再是哲学家了。没有人会认为只有托马斯·阿奎那或黑格尔才是哲学家。
朱子学并不是日本的东西。然而,朱子学离不开印度的佛教哲学,也离不开亚洲的思想交流。如果换句话说,就像托马斯·阿奎那的体系无法脱离希腊、罗马以及阿拉伯的影响一样,朱子学也是如此。所谓的“原创性”——也就是源头性,并没有那么大的价值。没有“原创”的哲学。哲学总是从外部来的。希腊哲学的起源,正是通过外来文化,或者通过整个地中海地区的交流而产生的。反而,正是柏拉图将这些外部因素隐蔽起来,确立了起源-原理,这就是形而上学。无论是在希腊,印度,还是中国,情况都是一样的。而且,这些思想相互影响。
印度的佛教逻辑学(因明)中,包含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伊藤仁斋曾说,“道”是人们往来着的地方。这看似理所当然,却是非常深刻的认识。换句话说,他对“道理”或者“起源”(根基)有着“交流”的理解。而他正是从《论语》中获得了这种认识。总而言之,认为日本有独特的哲学这种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江户的思想家们当时并没有那样的思考。朱子学是“世界性”的思想,他们正面面对这一思想。原创性,只能从那里产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江户的思想史,其实就是对朱子学这一理性主义体系的批判。至于“理”是否等同于“逻各斯”(logos),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然而至少在这里,“理”的批判是以一种彻底的方式进行的,而这种批判最终在本居宣长那里达到了顶点。如果说国学,那就提到平田篤胤这个人,他在宣长到达的思想高度上,重新回到“理”的方向,开始逆行。因此,我认为可以说,以本居宣长为代表,已经达到了朱子学思维的终点。
当然啦,宣长那样的批判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朱子学的批判早在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徠等人之间就开始了,并且契冲和贺茂真淵等人也参与其中。宣长本人主张,他的思想并非基于儒学的谱系,而是建立在契冲和真淵以来的国学传统上。然而,真淵实际上更受仁斋和荻生徂徠的影响,因此,单纯从国学谱系来思考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宣长也存在于朱子学批判的谱系之中。
我之所以一直觉得江户思想有趣,是因为它像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不需要过多考虑外部,它呈现的是通过自己的方式不断变形的语言体系和术语,这一点非常清晰。相对而言,明治以后,当人们想要重新审视先前的思想时,并不是从内部出发,而是从外部迅速借用新的概念。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局势使得这种做法成为了必然。因此,之前的思想问题并没有被彻底深入,反而在新的词汇中突然发生了飞跃。
现在,当你们阅读西田哲学时,可能会觉得其语言完全不同,非常难以接近。实际上,西田哲学在梯明秀、梅本克己等马克思主义者,或木村敏这样的精神病理学家中,以一种更为亲切的方式继续存在着,但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并不了解这种连续性。因此,明治以后的百年思想显得非常不清晰。然而,江户思想史中却有某种纯粹化的趋势,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围绕着某一个词汇展开的彻底斗争与颠覆的痕迹。但即便如此,并不能说当时的日本思想家是在孤立中进行思考的,相反,在某种意义上,江户的思想家们是“国际化”(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的。他们自己阅读和写作汉文。事实上,荻生徂徠的书后来流传到中国,且被评价为非常新颖的作品。
在东亚的世界中,正如在欧洲拉丁语那样,汉文是共通语言。因此,不能说江户的知识分子是封闭的。并且到了18世纪后期,兰学(蘭学)也已经完全传入,即使无法直接阅读西方书籍,他们也能通过中文翻译进行阅读。再者,朱子学中的“理”被认为是世界性的、普遍性的。无论是日本、中国,还是印度,都是如此。出发点的世界性假设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宣长的批判绝不是一种民族主义式的封闭,它是在关注到这一“世界性”的前提下进行的。
我们已经拥有了对江户时代的社会、经济的视点,并且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似乎能够轻松地批判江户思想史。然而,我们在思考时,必定是在某种语言体系中进行思考的,即便我们说“现实”,这个现实也是以某种理论体系为前提的。因此,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仅仅说“看清现实”,如果不能批判这种理论体系本身,最终什么都做不到。江户的学问可以简单地说是从朱子学开始的,但即使我们持有现实社会、经济的视点去批判朱子学的语言体系,仍然是行不通的。必须在那个理论体系或语言体系内,通过颠覆或批判的过程来实现这一点,这个过程是不可或缺的,也可以说,它就是一切。当然,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意味着现实的东西,但它并不是直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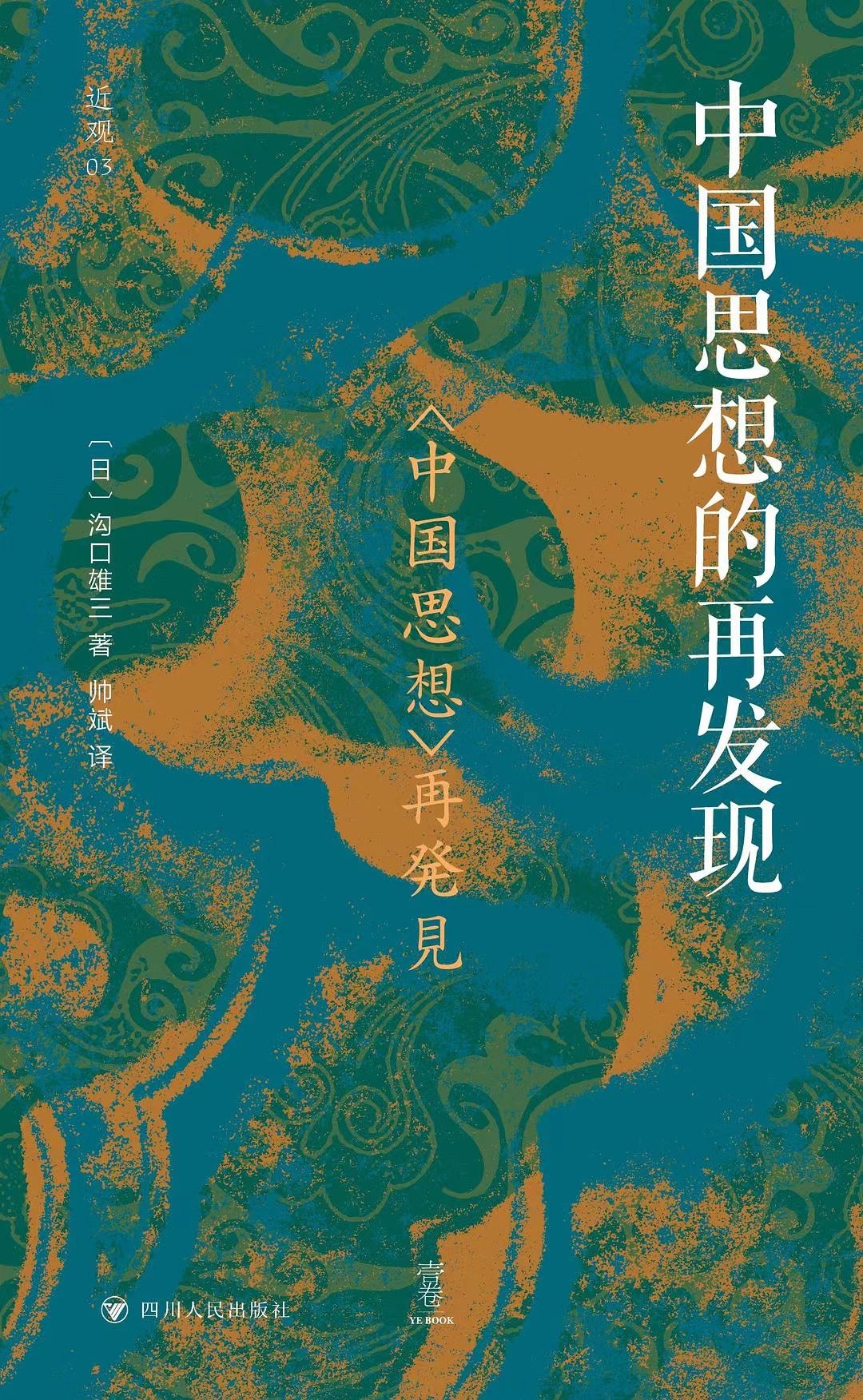
在中国,儒教看似一直延续着,然而直到大约十世纪之前,佛教和道教才是占主导地位的。相对而言,儒教试图恢复儒教性格的运动的顶点,就是朱子学。朱子学,或者说儒教的一个特征,就是认为我们处于这个世界之中。像佛教和道教,它们是超越世俗的,可以通过隐遁或出家来解决问题,但儒教不承认除在世的存在方式之外的其他任何方式。因此,政治就成了非常重要的问题,人际关系也变成了焦点。儒教,也就是如此这般的一种思维方式。然而,与其说朱子学继承了儒教的这种性格,不如说它更多地受到了佛教的影响,成为了一种极为理论化的学问,这就是朱子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在朱子学中,“理”和“气”是被分开的,为了便于理解,可以将“理”理解为原理,“气”理解为物质。也就是说,物质世界和自然界是存在的,同时自然法则也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比如牛顿的定律或者重力定律,其问题就在于它们到底存在在哪里,是存在于自然界之中,还是存在于自然界之外。这是一个看似平凡,但却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将这些法则看作“理”,那么问题就变成了,“理”是先于“气”存在,还是后于“气”存在。朱子学认为,“理先气后”,也就是说,“理”在“气”之前。然而,“理”并不是孤立地先行存在的,“理”是某种超越性的、理念性的东西,并且它并不是内在于自然界的。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气”是存在的,在“气”中才包含了“理”的整合。朱子学的特征就在于这种内在的=超越的。这就像天、地等事物,它们是超越的,但同时也内在于人类之中。无论是禅宗、佛教的思维方式,还是西方的如艾克哈特这样的神秘主义者,亦或是心理学中的荣格学派,都是类似的思考方式。荣格学派认为,在自我之下存在着更大的“自我”,通过不断自我反省,最终可以与更大的“自我”连接。这意味着,自己认识到的过程是,走向更大的自我,实际上就是世界本身,而这一切的根基在于,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朱子学看似只是理论化的,但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具备了类似禅宗的修行方法。
进一步来说,在朱子学中还有“存在”即“当为”的观点。这意味着,一个人存在的方式和一个人应该存在的方式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这个人能够达到他应有的存在方式。简而言之,意味着任何人通过修行都可以成为圣人。这一点在朱子学中有明确的表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修养自己的品德就是治理天下的基础。这种思想在江户时代得到了彻底的批判。荻生徂徠嘲笑了这一点,尽管他批评得非常尖锐,但这种批判正是对这种观点的深刻反思。即使是今天的政治家,往往也会从“修身”开始,提到自己从身边做起,先修正自己的行为。然而,这种想法在江户时代也是类似的。当经济出现问题时,大名们往往从简朴做起,但即使这样做,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徂徠完全明白这一点。虽然藩主通过简朴节约来树立榜样,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财政困难,但这种“节俭”却往往只是对下层民众施加更大的压力,从而引发更加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压迫。
接下来,关于物理和道理的问题,“物理”是指物质的理,而“道理”则是指道德的理。道理可以分为天道、地道、人道,这三者是同心圆式的相连的。这就像西方中世纪的“存在巨链”(存在の鎖),微观和宏观的世界彼此关联,因此,如果一个人通过净化自己,那么整个世界也会得到净化。相反,如果世界混乱了,那么人类也会陷入混乱。要解决这一点,只需修身齐家,这样就可以治国平天下。这种观点体现了一种宇宙观,而在江户时代,基本上是以朱子学的宇宙观为主导的。这种宇宙观与江户时代的等级社会相结合,社会中的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世界呀、宇宙呀,都在同心圆式地相互联系着。
在这里,为了说明,我想稍微补充一下,不能把中国的朱子学和日本的朱子学混为一谈。以中国为例,比如朱子等人,他们是通过科举制度入世的。科举制度就像是中国的高级文官考试,从唐代开始,到20世纪基本上都在继续。科举考试中,只要有能力,无论来自哪个阶级的人都能成为高级官员。像士大夫这样的人,基本上是读书人、文人,同时也是政治家,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这些人基本上超越了阶级,因此他们认为每个人内在都有神性,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另外,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彻底的儒教理性主义(合理主義)。所以,对于鬼神、来世等土俗宗教的思考,他们非常之批判。他们因此是非常理性和进步的人,“子不语怪力乱神”。再者,他们也相信自然界中有“理”的存在,并且致力于追求这一“理”。虽然之前我提到的是内在修行的内容,但朱子学也是一种探求自然界“理”的思想。
现在,在日语中,含有“理”字的词语比如有“逻辑”(論理)、“原理”、“真理”、“理性”,以及“理屈”(理窟)[注意理屈意味缘由]或“道理”等。我们使用“理”这个字的词语很多,但如果将这些词翻译成英语或西方语言,它们就会变成完全不同的词语。反过来,看到这些词语的翻译采用了“理”字,可以看出朱子学的影响力有多大,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在朱子学的理论体系中进行思考的。因此,关于对“理”的批判,也必须作为这一系列思想的总体来批判,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批判。
3
在谈到对“理”的批判之前,我简单地解释一下中国的朱子学与日本朱子学之间的联系。
在日本,并不是像中国那样,由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的读书人阶级来进行朱子学的研究。日本的朱子学研究是在通过武力获得政权的大德川幕府中进行的,其目的是为了确立政权的正统性和强化体制,因此必须建立一套原理。这种研究形式与中国不同。在江户之前,朱子学已经进入日本。当时后醍醐天皇实施的建武中兴,背后就有朱子学的影响。那时,由北畠亲房编写的《神皇正统记》(「神皇正統記」)等著作也正是如此。他们接触到朱子学后感到非常热衷,开始主张天皇亲政。以北畠亲房为首,他们试图以一种统一的正统性来解释日本史,因此结果必然走向天皇亲政。
然而,这并不是从日本本土产生的思想(就像读完马克思主义后突然的狂热一样),可以说,这种建武中兴的思想是突如其来的。南北朝大约持续了八十年,从现实的基础上来解释这一时期非常困难。我认为,可能每个人都在阅读朱子学之后激动不已。当然,昭和初期,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时,虽然当时确实存在劳工运动和资本主义矛盾,建武中兴同样也有其现实基础。然而,主导力量还是理念。我认为,在政权更替中,是否能给出合理的依据,是权力中心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在日本,为了有效地解释这一点,天皇总是被作为支撑点。然而,能够进行系统性理论化的,恰恰是在建武中兴时期,并且这一理论正是朱子学提供的。
另外,通常人们认为天皇主权思想来自于国学,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例如,幕末时期的“尊皇攘夷”思想本来是从水户学中产生的,而水户学派本身也是朱子学的思想体系。朱子学将将军视作“天皇的将军”,也就是说,幕府的正统性理论乃基于天皇的存在,因此对他们来说,尊皇主义只是形式上的问题。倒幕派只是将这一点反过来加以利用。如果没有朱子学,皇位继承制下的天皇主权是不可能出现的。荻生徂徠和宣长正是这些朱子学的批判者,因此,即使是宣长,也与这种尊皇思想或尊皇攘夷无关。实际上,“尊皇攘夷”是典型的朱子学思维。
即使朱子学作为德川体制的哲学被引入,日本的现实依然是封建社会,因此理论上的话语和活生生的现实世界是不可能完全契合的。人类本来就与宇宙相连接,或者超越的东西内在于人类,这样的想法是中国式的,只有通过能力来平等选拔的人们才能持有的观念,而在像德川时代这样的阶级社会中,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仁斋和徂徠等人看到朱子学的每一部分,都会觉得它虚伪。武士和朱子学本身就不契合,因为武士是通过武力获得权力的,特别是仁斋等人从町人阶层的生活出发,所看到的朱子学对他来说显得空洞,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他们对此语言和生活方式之间的错位有着深刻的意识。然而,正因为这种错位,要从现实角度解释思想的现实性,显然是不可能的。
伊藤仁斋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有特别的生活哲学,而在于他在朱子学的体系内部对其进行了批判。确实,朱子学在日本的某些部分确实行得通,但它也有很多地方与现实完全不符,这种局限性从一开始就存在。然而,对朱子学“理”的批判,恰恰是在它的内部进行的,而这一批判的火花由仁斋点燃。
到目前为止,在我阅读过的范围内,江户思想史的研究有两种主要的方向。最具代表性的是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在这本书中,他非常重视荻生徂徠,认为徂徠的非理性姿态为日本现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是在批判朱子学的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现实中,似乎正朝着与此完全相反的思路发展。
这种观点的代表是源了圓。这位学者主张,现代正是从朱子学的理性主义中诞生的。丸山真男认为,朱子学首先存在了,随后反朱子学才出现,这是一个典型的黑格尔式的逻辑展开。然而,丸山真男本人也在后来的著作中提到,实际上,朱子学自仁斋时期就已经开始广泛传播。因此,并不是朱子学先行,然后反朱子学才出现,恰恰相反,朱子学者实际上以某种方式吸收了仁斋和徂徠的思想。朱子学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灵活的变化。同样,学习兰学的人们,几乎都是朱子学者。例如,新井白石就是一个典型。他的理性主义,即便放到今天来看,也是令人赞叹的。新井白石是与徂徠同时代的学者,二人在政治上也有竞争关系。
到了幕末时期,继新井白石之后,佐久间象山等人开始出现,他们试图在朱子学的框架下理解西方科学。例如,“物理”这一词汇便是如此。他给“physics”(フィジクス)一词翻译为“窮理学”。从这种译名的方式也可以看出,西方科学的吸收是建立在朱子学的合理性前提上的。从这里开始,佐久间象山提出的著名口号“和魂洋才”也应运而生。这种“和魂”(大和魂)和“西洋技术”(西洋の技術)的二分法,至今仍然在日本的思维方式中存在。我认为,这种思维方式使得日本人在面对科学和技术时显得非常大胆,能够毫不费力地接受并发展它们。比如在生物学或生命研究领域,日本的研究者被认为是最为激进的。原本,“才”的部分与“魂”的部分之间应该是交错和令人困惑的,但日本人却不感到困扰。我认为,这可能正是日本式朱子学思维的延续。
当然啦,理性主义使得自然科学的发展成为可能,这一点在西方的情况中也同样适用。就像笛卡尔和培根一样。培根一般被认为是归纳主义和经验主义者,但严格来说,培根也暗中假设着这样一种观点:自然界中存在真理,而且这些真理是会显现出来的。西方理性主义的根本信念就是,世界中存在着真理,而我们看不见这些真理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的无知。这一信念推动了西方科学的发展,并且延续到革命理论中。通俗的马克思主义思维也是如此:有某个不纯粹的人在通过某种方式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要去除这个障碍,夺回真理。这种思维方式认为,世界的根底处是存在真理的,而这些真理是我们可以考察并实现的,这本质上应被视为一种信仰。
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等人认为,信仰-理性是统一的。理性与信仰之间并没有分裂。而与此相对的是新教,它主张信仰是理性无法达到的东西,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将神的超越性进一步强化。同样地,在对朱子学的批判中,仁斋等人切断了内在与超越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朱子学主张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修行成为圣人,而仁斋则认为圣人是超越人类的存在。也就是说,仁斋强调的是超越性的一方。这个观点不仅仅是东方的,也在西方中有所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仁斋的思想可以与马丁·路德的工作进行比较。
我稍后会详细阐述这个观点,但总的来说,朱子学的批判可以看作是对“理”的批判,亦即批判那些认为真理、原理和理性内在于人类的思维方式。然而,朱子学的批判绝不是从抽象的思辨中开始的。丸山真男和源了圓都是仅仅从哲学层面上进行思考。当他们发现这种思考方式行不通时,他们便试图通过接合现实来进行解释。
4
在此之前,仁斋、徂徠、宣长三人可以说是从“德行论”(デクスト論)出发,开始批判朱子学的。对于仁斋来说,朱子学的理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论语》本身。我之前提到过,仁斋与路德相似,路德也对天主教的教义体系不感兴趣,他主张“回归圣经”。
在讲解仁斋时,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来自四书五经中的《大学》,那就是“侧隐之情,仁之端也”。“侧隐之情”指的是对他人怀有怜悯、同情,或者说,感同身受他人的痛苦;而“仁”是指爱,朱子学认为“仁之端”就是“仁的显现”。也就是说,“仁”是一个本质存在,“端”则是它的表现形式。对于朱子学的这种观点,仁斋则提出,仁本身并不是原本存在于某处的东西,“仁之端”意味着“仁的开始”。在具体的生活中,比如当看到某人濒临死亡时,不自觉地伸出援手,这个行为就是“仁”的开始,即“仁之端”,而“仁”并不以某种“理”的形式存在于某处,这是他的观点呢。
对于“本质先行且后显现”的这种看法,仁斋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实际的行为才是关键,而所谓的“理”只是作为行为的结果而产生的。换句话说,如果把“理先气后”颠倒过来变成“气先理后”,这并不会真正改变问题的本质,只不过是把观念论转化为唯物论而已,并不能算是真正的颠覆。像贝原益轩这样的学者就采用了“气先理后”的观点,但这种方式并不能改变“理”与“气”之间的二元对立结构本身。相比之下,仁斋认为,无论是“理先气后”或者“气先理后”,最终它们依旧属于理论层面的东西。仁斋并不把这些问题作为理论来探讨,而是提出了实践的领域(実践の領域)。在他的思想中,“天道”与“地道”等领域被放在了括号里搁置,他认为所有的道理最终都归结于“人道”。换句话说,仁斋将焦点集中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上,而非超越的天道或地道,这与康德的辩证法有些相似。仁斋认为,关于世界是否有一个开端,两种答案都可以成立,或者说,对于这类问题,我们并不能从人类的角度妄下断言,而是应该放弃探讨天、地的“理”。
朱子学认为,物质世界的“理”应该存在,并且在物理学中可以找到对应的原理。而仁斋则认为,假定人类可以自作主张地设定“理”是不合理的,因此他集中在“人道”的探索上。仁斋并不简单地否定“理”,或者讨论观念与物质哪个先的问题,他认为这些都是理论性的问题,而真正重要的是实践,重要的是行为。因此,在仁斋看来,儒教是“德行”的问题,它是通过行为来体现的。而“道”并不是作为“道理”存在,而是在“往来”中,在“交通”中得以体现。
在朱子学中,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认为每个人内在都有“理”,也就是说超越的东西内在于每个人之中。换句话说,每个孤立的个体,本质上都拥有某种神圣的东西。就像佛教说的“佛性”,每个人本来都是佛一样。在基督教的“人文主义”形式下,比如黑格尔的理论,个体就等于是神。如果用中国的说法来讲,那就是每个人本质上都应该是圣人。所以只要通过修养,任何人都能成为圣人。这样一来,在佛教中,历史上的佛陀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因为每个人本来就是佛陀。当然,我个人认为并非如此。我觉得佛陀作为一个“他者”,像耶稣一样,是不能被忽略的。他们必须是真实存在的。如果说每个人本质上都是佛,都是神的话,那么历史上的耶稣或佛陀就变得不再那么必要了。
这对于朱子学而言也是一样的,朱子学本质上就是禅。即使是佛教,在中国的情况也是禅。净土宗也被包含在禅中。朱子学对儒教方面的禅进行批判,但从整体上看,朱子学这一体系本身就具备了与禅相同的结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孔子这样的历史人物就不再是必须的了。在朱子学中,历史上的孔子并不重要。因此,《论语》尽管被注释,但它也只不过是服从于朱子学这一知识体系的附属物,孔子不过是表达这一思想的人罢了。
仁斋对朱子学的批判,可以简单地说,是对超越性或外部性的发现。但这并不是说他把神或天给超越化了。如果那样的话,那就依然在朱子学的框架内了。仁斋真正发现的超越性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他者”。朱子学中的“本性”被他解读为“与生俱来”(生まれつき)。“与生俱来”意味着每个人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孟子说“性善”(性は善な),而孔子只说“性相近”(性相近し)。维特根斯坦的“家庭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也是这个意思,意思是说,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就像人类之间的相似性一样,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具备共同的特质。换句话说,人类的本性和与生俱来的特征是多种多样的。每个人身上并没有共同的“理”,没有共同的“性”,没有内在的“善”,这正是仁斋的观点。
最后,他所发现的“超越性”或“外部性”,其实就是简单地认识到“他者”的存在——这个“他者”是无法和自己完全同一起来的、与自己不同的存在。在朱子学中,“性”是本质的,而“情”是表象的。所以,“仁”是本性的一部分,而“爱”则是情感的表现。按照朱子学的理论,爱一个人如果是基于情感的话,那还是不成熟的阶段,我们应该用“仁”的方式去爱人。但仁斋的观点完全不同。他认为我们没有那种“本质的爱”,也没有那种作为“理”的爱,所谓的“理”并不是这样运作的,爱本身就是爱。他认为,朱子学所轻视的那种具体的、现实的爱,才是最根本的,才是爱的起点和终点。所以,他认为,除了这种爱之外,所谓的“仁”就没有任何意义。仁斋强调,爱作为人与他人关系的核心,是一个更本质、更根本的问题。
仁斋这个人——和中国的朱子一样——最初是修禅的,和朱子学一样,他一开始是从“心”出发的。也就是说,他关注的是每个人内心的状态,认为我们可以从这种内在的状态出发,走向觉悟,达到某种领悟的境地,这正是禅宗的核心思想。不过,仁斋不同于禅宗的是,他认为那种内在的状态并不存在。我们并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处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而且这个“他者”与自己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仁斋认为,在自己和他人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共同的“逻各斯”,我们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是无法简单同一起来的。
仁斋正是将语言置于“异质的交流”中。如果人类天生就内在“理”,那么“教诲”就不再是必要的了,因为每个人都会自觉地领悟。所以在朱子学中,“孔子的教诲”(孔子の教)是多余的。可是仁斋认为,正是“孔子的教诲”才是最重要的。在我们的交流中,确切地说,就是在完全不同的他者关系中,“孔子的教诲”作为一种可以使我们发现同一性的东西,是存在的。因此,孔子在仁斋的思想中成了圣人。这位圣人并非指每个人都能成为的圣人,而是指“绝对的他者”。如果用基督教的说法来比拟,就是类似于耶稣这样的存在。在仁斋看,在孔子以前的人并不是圣人。
这与徂徠的思想也有所联系,徂徠将孔子置于圣人(先王)的末端,而仁斋则认为只有孔子才是圣人。儒教中,孔子之前的人也被称为圣人,但仁斋主张的是,孔子的出现具有特别的意义,正是在孔子的出现中,开启了某种东西,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爱”。这是仁斋认为我们应该看到的东西。因此,孔子在仁斋的思想中,成为了那个“先验的他者”,这种对孔子的理解与朱子学的“圣人”概念不同。在朱子学的框架内,圣人是理论上的一个存在,而仁斋则认为,圣人通过“孔子的教诲”来表现,孔子的教诲才是“理”的表现。
让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像徂徠和宣长一样,仁斋的思考也有一个重要的契机,那就是他从实际阅读《论语》这一行为开始的。这是非常具体的事情。日本人在学习汉文时,即使现在也是这样,通常会通过加返り点来帮助理解汉文。但是对仁斋来说,最重要的是停止这种做法。如果我们把汉文改写成日本文,虽然看起来好像在读汉文,但那其实既不是纯粹的中文,也不是日语。那只是介于两者之间,大家用某种方式模糊地理解而已。而仁斋认为,应该直接用中文的音读,不用翻译成日本语,甚至向中国人学习中文。
他对语言的敏感度,正是仁斋思考的起点。然而,仁斋关于语言的理论一般被忽视了,主要是因为他并没有明确地把这些想法表述出来。丸山真男说仁斋偏向内在的、主观的,而徂徠则看到外部世界中作为制度和语言的“外在性”,这是对的。确实,关于徂徠,情况正是如此,他在语言方面提出了明确的方法论。例如,徂徠教学生汉文时,他一开始并不会直接给出汉文的含义,而是先让学生读出中文的音。这样,他们就能逐渐习惯中文发音,进而理解其中的意思。即便是读《论语》,他也不会像朱子学那样,先从明确的定义和词汇的含义开始。
仅仅读《论语》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阅读同一时代及其前后时期的所有文学和文献。通过这样不断熟悉语言,最终才能理解《论语》的真正意义。这里所强调的,并不是要去定义词语的意义,而是要先消除“意义”这一层面。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就是通过实践来掌握语言的用法。
然而,尽管仁斋的语言理论并没有明确地加以阐述,但他实际上已经在实践中做到了这一点。仁斋与徂徠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论语》视为一部与其他文本截然不同的文本。他认为,《论语》中的言语是古今最为重要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仔细阅读《论语》就能发现,书中的内容有许多矛盾。因为《论语》的形式是孔子对别人说的话的回应,而这些内容是根据当时的对话者和文脉来界定的。例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如果不考虑它的文脉,便无法理解其意义。仁斋认为,这句话表达的是,发现自己与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的喜悦。然而,不管如何去看字面,它的真正解读是无法简单得出的。正如我们经常体验到的那样,有时会有一个瞬间,孔子的话似乎突然在我们心中明了,这种体验也是不可言喻的。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圣经》中,耶稣的话语总是有特定的听众和文脉。它们是片段,片段之间如果不考虑文脉,甚至会自相矛盾,而无法将这些片段统一到基督教的教义体系中。这与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完全不同。
仁斋之所以关注《论语》中的语言,正是因为它的“对话性”。不过,必须说明的是,这与柏拉图的“对话”有所不同。如果从柏拉图式的“对话”角度理解,“对话”意味着与内在具有相同逻各斯的他者进行交流,因此它是同质的对话。因此,柏拉图让苏格拉底说“共同的探索”,尽管他在与他者对话,但最终这些对话还是在与自我进行对话。所以,“对话”实际上变成了“独白”。而真正的“对话”必须是在遇到与自己不同的他者时才能称之为“对话”。无论如何,《论语》就是这种“对话”的形式。相比之下,《孟子》虽然采用了对话的形式,但它依然是“独白”,更容易为学者所理解。
更重要的是,仁斋的学堂本身就是通过这种“对话”形式来进行教学的。他的学堂摒弃了传统的师生关系,采取了类似研讨会的形式。这种形式不仅在江户时代,甚至在今天都很少见。徂徠等人则是单向地进行讲解,这和朱子学者的方式类似。换句话说,仁斋的语言理论体现在他阅读《论语》的方式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教导”方法上。像丸山真男这样的政治学者,显然无法理解这一点。
因此,我们可以说,仁斋的“阅读”方式开启了新的思维方式。他明白,词语的意义并不是通过定义来决定的,而是通过具体的使用方式逐渐显现出来。仁斋确实写过一些明确解释词义的书籍,但那是他通过与门生(其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弟子)多年的对话和交流,经过三四十年的锤炼后形成的。事实上,仁斋对孔子的理解是非常文脉化的,他会根据不同的语境做出不同的解读。例如,他会说,孔子的话是针对特定对象所说的,或者说某些话语是孔子故意不想说的,或者是孔子故意不回答的。仁斋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解读的。

5
至今为止主要围绕仁斋展开了讨论,接下来我想谈一谈徂徕和宣长。仅仅是仁斋一个人就已经非常有趣。然而,当把仁斋、徂徕和宣长并列放入思想史中来看时,仁斋的那种有趣之处立刻变得淡薄了。这就像把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并列放在一起,康德就被视为只是站在前面的人,而黑格尔也被看作是马克思之前的人一样。然而,康德作为康德,黑格尔作为黑格尔,当单独阅读他们的作品时,每个人都非常有趣。起初我打算研究宣长,于是从仁斋入手,结果发现仁斋本身变得相当有趣。于是我发现徂徕也很有意思,但并不是如丸山真男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有趣。看来,将思想家以历史顺序排列来评价,总有些不妥之处。或许,通过历史方式能够讲述的内容,只不过是一些乏味的思想史罢了。与之相对,如果像仁斋那样以阅读文本的方式来看待,仁斋的文本便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有趣之处。
好吧,仁斋对“理”的否定,实际上是指他否定了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意义。最近的批评中经常提到的一些观点,其实也源自于一种文献学或注释学的传统。就像德里达,他在讨论“书写”(écriture)时提到的“文本”(texte)这一概念,本来应该是用大写字母来表示的。换句话说,德里达所说的“文本”其实就是《圣经》,特别是《旧约圣经》。常有人说要“解放文本”,但实际上,文本并不是那样简单的东西。
如果不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包含在文本当中,就不可能解放文本的意义。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种信念。也就是说,你得相信《论语》是绝对可靠的,并且《论语》里面写了所有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批判围绕《论语》所构建的朱子学理论体系。所以,文本不能随便选一个都可以,它必须是一个“大写的文本”。德里达就是在这种“大写文本”的基础上,暗示其意义并将意义赋予书写。
在这个意义上,仁斋将《论语》作为“文本”,并认为其中包含了一切,从而对“理”进行批判,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江户时代思想中最值得关注的起点,就是仁斋找到了这种意义上的“文本”,可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突破。
其实,如果不认为所有的内容都包含在文本里,就不可能解放文本的意义。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信念。也就是说,你得相信《论语》是绝对可靠的,认为《论语》里写的就是所有的东西,只有这样,你才能批判那些围绕《论语》建立起来的朱子学理论体系。因此,文本不能随便选择,而应该是一个“大写的文本”。德里达等人也正是通过“大写文本”这一概念,暗示其中所包含的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看,仁斋把《论语》作为“文本”,并认为所有的东西都蕴含在其中,从而对“理”进行批判,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江户思想中最值得关注的突破点,就是仁斋找到了这种意义上的“文本”。
对仁斋来说,像“天道”或“地道”这样物理学的问题根本不重要。简单来说,对他而言,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人道”,也就是人类的道德和行为准则。换句话说,他把“道”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对他人的爱,这并不是一种“主观性”的看法。而徂徠则把“道”看作是社会制度或者政治结构的一部分,他认为“道”是外在的、由古代先王所创立的制度。对于仁斋,徂徠批评他过于佛教式地执着于内在。但显然,情况并非如此。仁斋并没有忽视外部的现实,反而,他的思想中有着对伦理的深刻关注。与徂徠的政治学不同,仁斋的思考并不会消弭这些伦理性。事实上,仁斋的这种伦理性使《论语》具备了可能成为世界宗教的潜力,而徂徠的政治理论却在某种程度上夺走了这一点。
徂徕认为,仁或爱绝不是道德问题或内在问题,而是治国安民的问题。仁,指的是治理国家,使民众安居乐业。丸山真男从徂徕提出政治责任与政治伦理的角度,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基雅维利曾说,君主不必是道德上的完人,只需看起来道德即可。徂徕同样认为,这种类型的政治伦理至关重要,而君主个人是否是道德上的善人或恶人,并不重要。无论君主如何学习儒学,政治家唯一需要关心的是能否真正做到治国安民。
徂徕所处的时代,将军是以“犬公方”恶名昭著的德川纲吉。他是个奇特的人,甚至亲自讲解儒学。由于是将军亲自授课,家臣们都不得不聆听。虽然纲吉本人可能洋洋得意,但对于家臣来说,这无疑是一件令人苦恼的事。同样,他颁布的《爱护生类令》等政策也反映了他自身是一个极为道德化的人。然而,这些政策在现实中引发的情况却截然相反,往往是灾难性的。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徂徕的思想中包含了对纲吉这种过于道德化的领导方式的批判。因为,最令人头疼的,莫过于一位道德化的君主。正因如此,徂徕从内面性与道德性中抽离出政治性与制度性,这种思考方式的转向,正如丸山真男所评价的那样,成为了现代思想的起点。
然而,徂徕的思想与马基雅维利截然不同,也与韩非子有所区别。需要铭记的是,他的思想始终根植于儒学之中。对他而言,政治的核心在于“礼乐”。若忽视这一点,将徂徕视为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无疑是一个双重的错误。因为,在他的儒家政治学中,还包含了对人性以及人类欲望的深刻洞察——这一点是丸山真男未曾关注到的。
朱子学中常说“存天理,去人欲”(人欲を去って天理につく)。但在徂徠的观点中,“欲”这个词,我认为他更多是把它当作“欲望”来看待。也就是说,在朱子学里,人欲是指那些孤立的个体内部所存在的欲求。按他们的理解,如果通过某种认识或者修行去摒弃这些欲望,就能达到“明镜止水”的境界。
然而,欲望在徂徠的理论里并不是这么简单。就像黑格尔的看法一样,欲望不只是个人内部的东西,它其实是与他人的欲望相联系的,已经被他人所介入和中介化。所以,如果欲望仅仅是个体内心的需求,可能通过修行可以克服,但如果欲望总是和他人的关系挂钩,那就不可能通过修行去超越它了。而且,欲望的存在,也并不是单纯关乎个人自由或责任的问题。
具体来说,徂徕在《政谈》(『政談』)一文中提到,当时元禄时代的江户,无论是武士还是农民,都在模仿町人的生活方式,纷纷涌入江户,导致江户人口急剧膨胀。这不仅使得各阶层之间的身份差异变得模糊,人人还随波逐流,追逐流行,日益奢靡。这种时代中的“欲望”,已经呈现出一种朱子学无法把握的形式。
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到了文化文政时期,更加明显。无论如何,消费社会中的“欲望”在元禄时代已经清晰地显现。而身分社会对此完全无力抵抗。这种现象与货币经济的渗透密切相关,而朱子学中所设想的“人欲”与“天理”对立的二元论,根本无法应对这种情况。此时,欲望已表现为他人的欲望,或者经由他者媒介而形成的欲望,这种竞争现象超越了身分社会的限制,广泛蔓延,最终导致江户经济上的困境。
面对这一问题,徂徕是如何思考的呢?
徂徠的政治学和韩非子体系的政治学有很大不同,因为徂徠认为政治和“礼乐”是紧密相关的。简单来说,“礼乐”指的是仪式和音乐这类东西。在徂徠看来,“仁”并不是仁斋所说的“爱”的问题,而是政治技艺的问题。他认为,古代的圣人们经过多代的努力,创造了这些技艺。那么,具体的技巧是什么呢?就是“礼乐”了。它不是法律、也不是惩罚,而是更深层次的制度设计。更具体地说,“礼”指的是仪式的形式,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形式来划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在徂徠看来,元禄时代的状况正是人们的差异性逐渐丧失的体现。虽然说是“身分”,但实际上每个人都被别人的欲望驱动,每个人都在模仿彼此,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这样的同质化现象引发了严重的竞争,而封建体制在经济上也快要崩溃,却没法遏止这种趋势。对于商人来说,这种情况或许无伤大雅,但对于德川体制而言,这无疑是不可避免的崩溃危机。
那么,怎么才能控制这种局面呢?答案是“礼”的恢复。也就是说,要防止通过差异化不断加剧的同质化现象,就必须确立符合身分社会的“礼”。如果确立了“礼”,那么这种消费社会的进程可能就能得到遏制,这是徂徠的想法。当然,这种做法并没有成功,也不可能成功。
所以,徂徠认为,人的内心并没有能够自我约束的东西。必须依靠制度——即“礼乐”这种制度来约束人。你不能只是指责别人,说“你们不能有这些欲望”。如果能够消除激发欲望的差异或同一性,那么人们自然就不会产生那些欲望了。因此,政治的作用并不是诉诸个人的内心或者伦理,而是作为一种技术,通过外部的制度来实施。这种观念,与现代政治学虽然有相似之处,但在根本上是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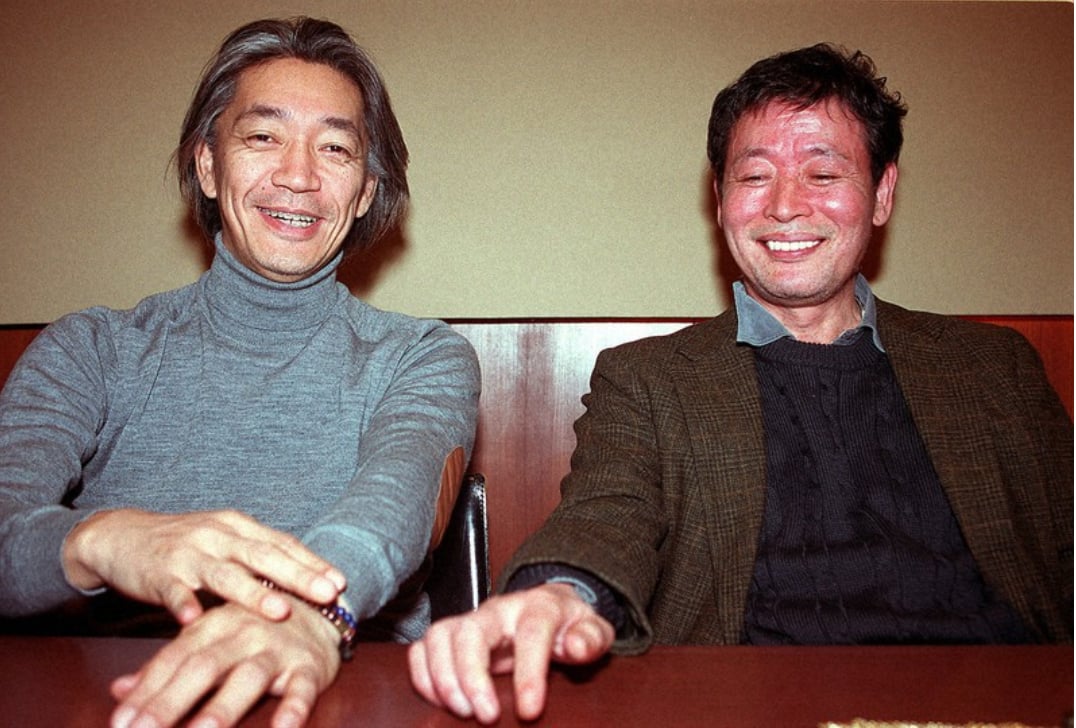
6
总结起来,从“理”的批判这一视角来看,宣长的立场可以说是将仁斋与徂徕的思想进一步推向了极致。对于仁斋与徂徕而言,他们研究的主要文本是以《论语》为首的“四书五经”。而与之相比,宣长所专注的文本则以文学为主,例如《古事记》或《源氏物语》,以及基本上以和歌为核心的作品。
按照传统的“知·情·意”分类来说,仁斋的关注点并不在于知的领域,即理论或真假问题,而是将重点放在了意的领域(当然,知·情·意的框架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知的构架,仁斋的思考可以说是试图超越这一框架)。无论如何,仁斋更倾向于在意的领域进行探讨,若以真、善、美来划分,则主要聚焦于善的层面。
然而,对于情感或美的领域,他基本上保持一种淡漠的态度。尽管仁斋也涉及文学,但当需要对美进行价值判断时,他往往会依赖某种“正确的理”的逻辑推演来给予解释。这种倾向不仅出现在仁斋身上,即使是像真淵那样的学者,也难以避免。
自古以来,诗歌为何如此重要?这是因为它被认为能够表达人的“真心”,唱诵出真诚之心,因此甚至能打动神明之心。这一观点早在《古今集》的纪贯之序文中就已被阐述。
到了江户时代,17世纪的香川景树和贺茂真淵等学者认为,诗歌之所以卓越,是因为它能够呈现出我们某种内在的真心。当然,仁斋并不认为人天生拥有“真心”,但他通过诗歌展现我们诚挚的情感,以此来为文学辩护。
这一观点依然延续至今。例如,那种认为文学能够“捕捉情境”的理解方式,即从情境的视角来解读文学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情境被视为真实的存在,而文学作为虚构,因其能够展现这种真实而被认为具有优越性。由此,文学最终成为服务于“真实”或“真理”的工具。
那些为文学或诗歌辩护的人,虽然与哲学等领域有所关联,但他们的辩护方向通常是,文学同样能够实现真理,甚至认为文学才是实现真理的最佳方式。然而,宣长对此观点完全不予认同。
那么,对宣长而言,什么是“真心”呢?显然,它并不是指那些奸邪之心或恶念。宣长并不是在某种具体的事物上贴上“真心”的标签,而是试图打破“真心”这个概念中所包含的“真”与“伪”之间的区分。这一点,与仁斋和徂徠的思路是一致的。他们同样批判了语言只是服务于真理或知识的观点。然而,在宣长这里,这种批判被带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
正如之前提到的“知·情·意”,宣长特别重视情感的领域。他使用了“知晓物哀”这一表达,这实际上是关于情感的范畴。通常来说,无论是激情还是情感,在哲学中都被视为需要被驾驭的东西。所谓的道德主义者,总是在探讨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然而,宣长却批判了将情感视为知识领域之外的东西,或者认为情感必须始终被知识所束缚的这种思维方式。正是在这种批判的背景下,诞生了他著名的“知晓物哀”这一说法。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了解事物”或者“事物具有哀情”那样的意思。当然,“知晓物哀”本身也是一种认知方式,但它并不以识别对象或区分真伪善恶为目的。相反,它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审美体验的形式。
宣长可以说在情感的领域中承认了“知”的存在,并且认为情感比真理或善更为根源。他所说的“知晓物哀”中的“哀”,自然不仅仅指悲伤,而是涵盖了各种情感。这是一种超越认知论范畴的体验,指向更为根本的存在之感。这种体验可以被视为先于认知性判断的“纯粹经验”。因此,可以理解为,宣长试图用“知晓物哀”这一句话来表达这种根源性的情感体验。
宣长所提到的“神之世”或“古之道”,在某种程度上是将徂徕的观点置于日本语境中的一种转换。然而,这其中展现了一种超越真伪与善恶的认知。他曾这样说道:人死之后,无论善人还是恶人,皆前往黄泉之国。这固然是矛盾的,但却无可奈何。然而,死亡本质上只是令人悲伤的事实,而他则反对将其按照善恶划分,用以人为地正当化或否定这一现象。
那么,人类本来的存在状态是什么样的呢?在宣长看来,人类的死亡仅仅是悲伤的事情,除此之外,其他的一切不过是逻辑推理罢了。然而,人类面对与逻辑不符的现象时,总会感到难以接受,因而试图以某种方式予以处理,例如引入“最后的审判”一类的观念。实际上,到了宣长之后的平田笃胤那里,神道几乎吸收了基督教的思想,人因此被善恶区分而分别进入天堂或地狱,结果再次陷入了二元论的窠臼之中。
宣长所说的“知晓物之哀”(もののあはれを知る)的“知晓”(知る),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知”的层次,而是一种涉及人类存在根本层面的“知晓”。这一层面超越了善恶的对立,是所谓的“神之道”,而我们必须对其有所认知。当然,宣长并未以理论的方式阐述这一点,而是通过对文本的严格注释和细致解读来展开。他的批评同样避免直接面对“理”究竟为何的问题,而是在实践中推动这一思考,并将仁斋开启的探问推向极致。
丸山真男将仁斋类比为康德,将徂徕类比为黑格尔,而在这个框架下,我认为仁斋更像是克尔凯郭尔,徂徕更像是马克思,而宣长则可以被视为尼采。尼采曾做过古希腊文献学的研究,可以说,他试图通过这种研究,探寻基督教和早期柏拉图主义之前的“古之道”(古の道)。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尼采将“悲剧”,即通过艺术方式来获得的认知,作为一种根底,由此提出了对柏拉图式知识(哲学)的批判视点。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宣长的思想与尼采有某种相似之处。
当然,我对宣长抱有批判态度,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这种批判我已在其他场合多次提及。今天我想强调的不是简单地否定或轻视他,而是要说,不应如此草率地否定掉这一思想。尽管我们当下掌握着许多新的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江户时代的日本人什么都没有思考。相反,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探究和发展以极其彻底、不可避免的方式展开,这种探索的形态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我想,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鼓励吧。
在西方,对哲学的批判,尽管往往是在哲学内部进行的,但它几乎总是从外部的领域——比如宗教和艺术——获得力量。这种批判通过引入哲学所排斥的超越性或他者性而展开。比如,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的批判便是如此。即便在无神论的框架中,这一点也同样成立。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例,他在古典经济学“同一性”的世界中,引入了货币以及货币(神)与商品(人类)之间非对称的关系。另一方面,从艺术(美)的领域展开的批判,则可由尼采作为代表。通过这样的视点来看,仁斎、徂徠和宣长对朱子学的解构,就变得更容易理解了。今天的演讲,正是希望让大家认识到这些内容,并在未来遇到类似问题时,能抱有一份兴趣与好奇去重新审视这些思想。如果能达到这一点,我将感到十分欣慰。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内容。谢谢大家。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and clap, let me know that you are with me on the road of creation. Keep this enthusiasm toge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