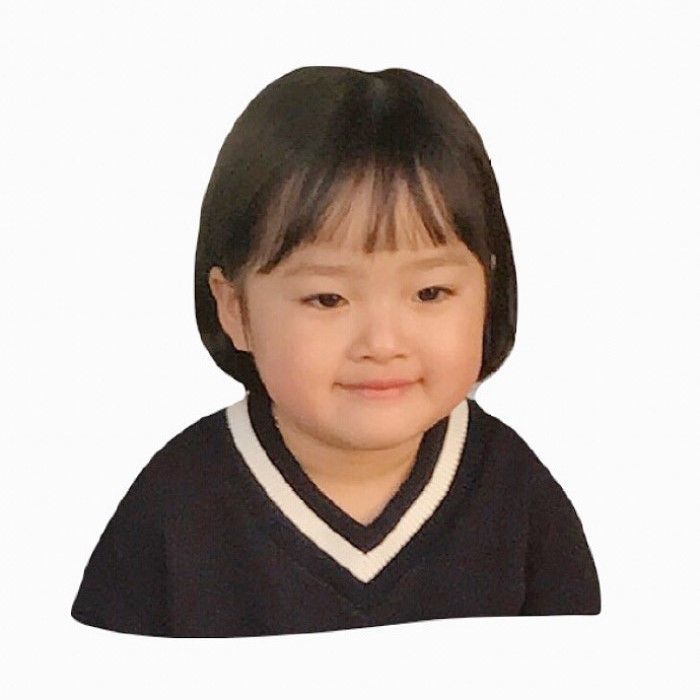七日書第二日:一年只用一次的鍋,卻讓我想起「家」
第二天( 6 月 4 日)
寫一件最能讓你想起「家」的物件。
人們會以不同的形容詞來訴說「家」,比如是溫暖、幸福、束縛、想要逃離等。有什麼物件盛載著你對家的各種情感,又能讓你想起家的?可以跟我們描述一下那件物件嗎?
家裡有一口很大很大的鍋,要兩隻手,用盡全力,才能把它抬起來,就像武俠小說裡高手們用寒鐵鑄成的某樣武器,並不是適用於所有人。鍋的顏色深黑得發紅,最近拿出來看了一眼,甚至有些發白。這麼大的鍋,跟我這個三口之家的食量並不匹配,所以它其實很少被使用,但偏偏我會因為這口鍋而想起我的「家」。
這口鍋只能用來烹飪一道菜式,那就是來自爸爸家鄉,東莞鳳崗鎮的客家碌鵝,名副其實「獨孤一味」了。烹煮這道菜的關鍵,是鵝要保有完整之身,一股勁兒地往肚子裡塞香料,大蔥、豆豉、蒜蓉、料酒。每次看到這一幕,我總是想起《憨豆先生》和《Friends》的感恩節火雞。我總是幻想家裡在做客家碌鵝時也會有這麼趣怪的一幕,然後全家人歡聲笑語地過節。
現實始終有別於戲劇化的藝術。一般來說,這道菜一年只會做一次,這口鍋一年也只會用一次。我爸挺著大大的啤酒肚,叼著煙,把佐料一點點塞進鵝的肚子裡,嚴肅、深沈,沒有搞怪,不作聲地完成全部步驟。等塞好香料,鵝身也抹滿醬油,就要放進鍋裡「碌」了。這個粵語的動詞很形象,就像你早上賴床,在床上「碌來碌去」。龐大的鵝放在這口大鍋裡,尺寸契合,再想怎麼「碌」,也只能有尺度、有邊界地「碌」。左翻翻,右拖拖,鐵鍋導熱很快,鵝迅速變得燙手,但我爸堅持徒手搗鼓。
「小時候窮,過年才能吃一次碌鵝」,我爸這麼告訴我。客家人對鵝,是滿心智慧地在烹飪:鵝肉做菜,鵝油做粄(一種咸糕點叫「鵝湯粄」)。每次吃這道菜,我都會想,現在家境也沒有很差,為什麼還是過年才能吃。後來我才知道,這道菜是爸爸跟在他的媽媽旁邊,也就是我的奶奶,觀察著學著做的。爸爸在很小的時候就離開家生活了,父母緣淺薄。他和他的父母也就是靠著每年過年的這一頓飯,裏頭客家碌鵝這道硬菜,還有那個大得快要能擋住身板瘦小的奶奶的那口鍋,去感受奶奶的愛意。
奶奶離開這個世界有十多年了,爸爸很少提起奶奶,偶爾拿出這口鍋做客家碌鵝的時候,嘮叨幾句自己小時候有多獨立多不需要父母。但我知道,他想念他的媽媽了。
深深的鍋,藏在我家廚房的角落裡,我依然很少看到它,但偏偏它讓我想到這個「家」,還有那些家庭裡零碎的個人記憶,也是深深的。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