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人是什麼:讀Adriana Petryna《暴露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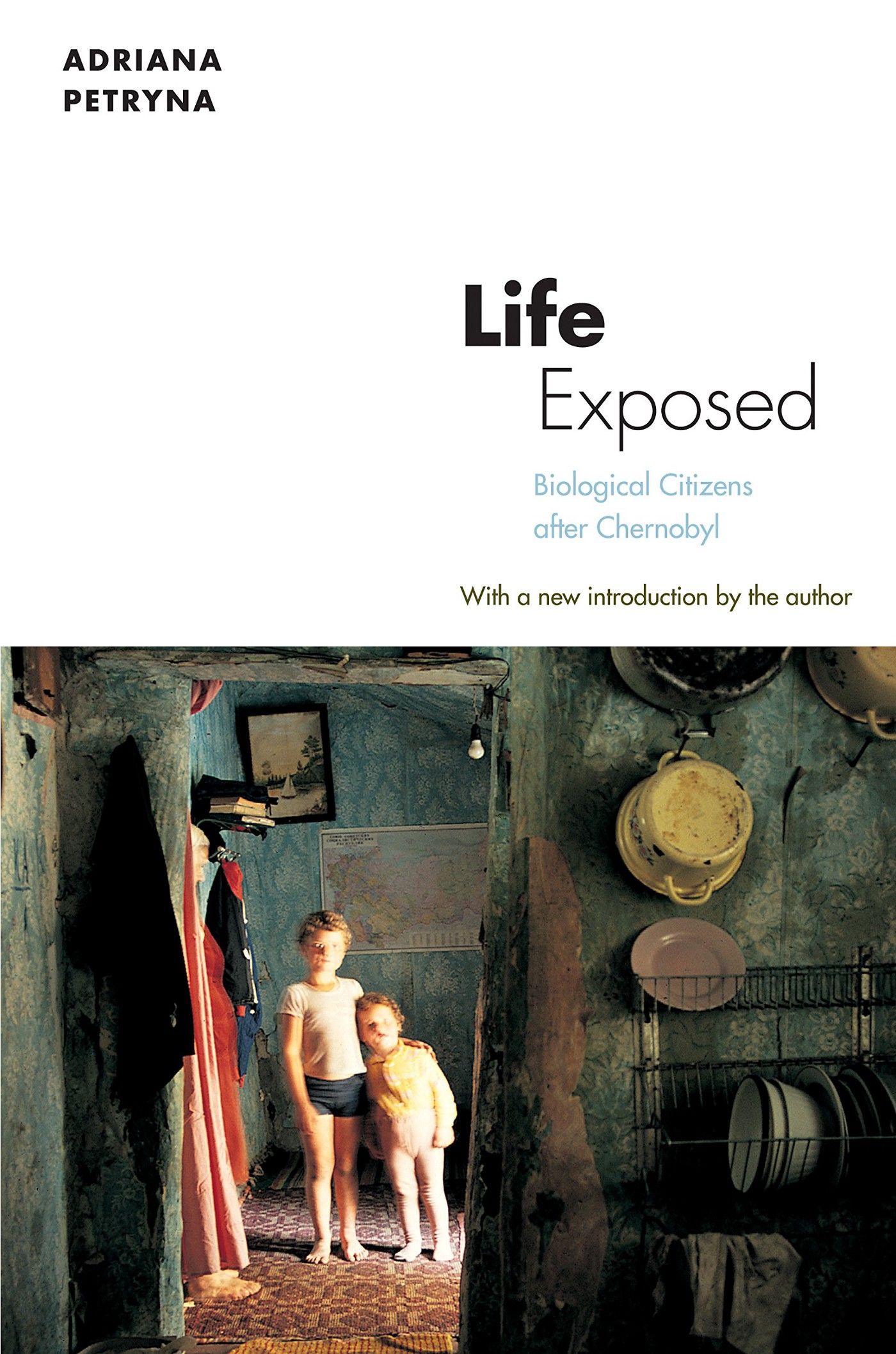
Adriana Petryna, 2013[2004], Life Exposed: Biological Citizens after Chernoby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一個波蘭人說下了一句讓我難忘的話。這是一個沒有什麼文化的波蘭農民,他把一個猶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裡,直到二戰結束,這個猶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國後,這個波蘭人被視為英雄請到耶路撒冷,人們問他,你為什麼要冒著生命危險去救一個猶太人,他說:我不知道猶太人是什麼,我只知道人是什麼。
──余華〈我只知道人是什麼〉
1「他們還活著。他們知道自己並沒有死,但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活下來的。」
這是一位生化學家告訴Petryna的話,描述的是車諾比核災後那些參與搶救跟重建的工人。2013年出版社發行了《暴露的生命》十周年紀念版,Petryna新寫了一篇前言,也選擇用這句話開場。
「不知道」有兩層意思:第一層很直覺,就是車諾比的意外發生後影響多廣,多久,多少的殘存輻射量會對人體產生影響,以及是否會有結束的一天,至今仍有各種謎團與疑義,無人真正知道。就像這群被徵召去後續整理車諾比核電廠的工人們,他們吸收了高於致死量六到八倍的輻射,生化學家與醫師都難以明白為何他們還能夠存活。但他們存活下來了,雖然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活下來的。
不過「不知道」還指向了第二層意思。那是各種政治與官僚體系共同運作造就的「不知道」。從蘇聯統治到烏克蘭獨立的複雜歷史,使得長期追蹤車諾比核災影響的研究難以可能。囿於盤根錯節的政治與經濟考量,世衛組織在2005年也建議,相關健康追蹤的研究限縮在當初攝取了大量輻射的災後清理小組,以及罹患了甲狀腺癌的兒童就好。
於是,「由於一些神祕的命運波折,應當成為提供車諾比核災影響知識的核心人群卻被邊緣化,甚至遭受排斥。」在這篇2013年的新版前言,Petryna這樣寫道:「我們至今不知道那些攝取了高輻射劑量的工作如何存活,我們也不知道那些居住在那片受污染的土地上的人們如何與長期輻射共存。」

2「爆炸事故後就沒有新的急性輻射症候群案例了,不過卻有因為社會、心理或經濟問題,刺激個人身心狀況,進而導致心血管功能調節及神經意識的輕微變化。」
蘇聯時期最權威的放射科兼神經科學權威,同時是車諾比事件後主要負責醫師Angelina Guskova在受訪時這麼說。
如果除去一切背景、脈絡和故事,《暴露的生命》主旨非常簡單,甚至在STS研究盛行的現在還有點陳舊:科學知識、醫療分類和國家政治相互緊緊糾纏。之所以如此,關鍵在於車諾比事件發生的1986年:那是蘇聯最後垮台前幾年,餘波卻延續到獨立後的烏克蘭政府時期,改朝換代的動盪與磨難在處理車諾比核災的影響與受害者一事中完全體現。
事件爆發時,一方面蘇聯體制下的生命科學與歐美不同,走的是社會環境適應的路子,而非如今我們熟悉、講求個體生命的基因概念,因此並不怎麼承認輻射能與個人身體病變之間的關聯,而傾向將受害者的問題歸於心理創傷。另一方面,蘇聯政府也透過各種行政、技術上的操作,試圖淡化車諾比事件的嚴重性。這些操作包括將判定一個病患是否為急性輻射症候群的劑量門檻提高(原本只要吸收了200 rem就算是急性輻射症候群,但後來調高到250 rem),或者要求診斷相關者時,一律開立症狀類似但病因歸咎完全不同的「自主神經血管張力障礙」(vegetovascular dystonia,相對於急性輻射症候群有明確的輻射病因,更強調環境的影響)。如此一來,官方的車諾比事件受害者,只有當初在車諾比核電廠爆炸時首當其衝的工作人員──直接受害者──從此不會再增加了。
到了烏克蘭統治時期,政府為了凝聚民眾信任,也為了突顯自身勝過蘇聯統治的優點,接手處理車諾比事件後開出了優渥的社會福利承諾:它大幅度調降了「車諾比受害者」的判定門檻,並積極推動醫學證明來認證因為車諾比輻射造成的病痛傷害,針對持續增加的受害者給出大筆的補償與津貼,宣示照顧「國民」的決心。原先「被迫」消聲匿跡的受害者們紛紛重新出現,努力透過各種管道與門路,取得身分證明──而且是嚴重程度愈高愈好的證明,以便可以獲得長期且可觀的津貼。

3「我是個『車諾比人』。」
在蘇聯垮台,烏克蘭獨立後,一位曾經被徵召參與車諾比災後搶救的卡車司機Anton開始「面對」自己作為車諾比受害者的身分。
然而《暴露的生命》要強調的從來不只是科學與政治彼此間的難分難捨。Petryna反覆提醒我們,最重要的是務必看見車諾比核災裡「人」的存在──看見一個人的生命如何在科學與政治的糾纏下,被實實在在而強烈的影響,改變,甚至破滅。
例如Anton。在過往蘇聯統治的幾十年間,儘管自己飽受頭痛折磨、時不時會記憶斷片,甚至因此賠上駕照,從此無法擔任卡車司機,但Anton從不認為也不承認自己有病。這當中原因複雜,包括蘇聯政府講求集體與連坐,治下民眾往往不願意或不敢承認自己有病──有病也就意味著失去工作,甚至面臨麻煩。同時,在這樣強調個人勤勉與集體勞動的氛圍下成長,Anton的自尊心和驕傲也讓他不願意袒露自己的虛弱。
車諾比核災的餘波裡,Anton並非個例。許多受車諾比事件波及者,在蘇聯時期被劃分在受害者之外,只能自己掙扎度日──他們既拿不到國家給予的津貼補助,卻又容易遭受他人的歧視與排擠。許多人最終選擇定居不宜人居的災區裡,做相對高薪的災區善後工作,拿近乎是賣殘存的健康而來的錢。而後到了烏克蘭統治時期,他們為了微薄的醫療補助,又被迫輾轉在各個醫療院所跟行政機關之間,為取得身分證明而努力,碰壁,又努力。在車諾比核電廠爆炸後續的數十年裡,這些被遺忘、丟棄的人們就這麼持續地徒勞地消磨著自己的生命。
《暴露的生命》裡,Petryna於是提出了影響深遠的「生物公民」概念。「傳統講的公民概念」,人類學者解釋,「將公民視為與生俱來、受保護的自然與法律權利的擁有者」。然而,對許多一出生即深受環境與健康威脅的烏克蘭人而言,公民權之上還背負著生存的掙扎。
「事實是,大批困苦的人們學會了用最基本的、非生即死的語彙來爭取經濟與社會的包容性。」
4「一個健康的小孩絕對不會來自有病的父親。」
「當我們到了農場管理人的辦公室,看到一群軍官在那裡。一名上校給了我們制服,然後隔天我們就被帶到污染區善後了。」
「為了證明我的身分,我必須取得那些小破紙(bumazhky)。他們折磨我。」
「在車諾比事件以前,Anton從不生病的。他對未來有計劃,他想做點什麼……他再也不是以前的那個Anton了。」
「我們的記憶都沒了。你持續忘掉所有事──我們就像行走的屍體。」
「為了自已兒女的健康,沒有任何內分泌專家會想在污染區生活。」
「在他十歲的時候,我知道有什麼落到他身上了……他不再能走,他的腳無法正常行動,彷彿有什麼東西不讓他的腳走。」
「我小孩跟丈夫都生病了,但我們沒錢,我們要怎麼活下去?我已經沒有未來了。我想死。」
「我當時離開醫院,不再進行療程跟病情追蹤,是因為我知道自己從此成為沒價值的工人了。我又該去哪裡?」
5「我必使他們在我殿中、在我牆內、有記念、有名號」
這句話不出自《暴露的生命》,而是聖經以賽亞書56章5節;同時「有記念、有名號」也成為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的希伯來原名──這是我讀余華的散文〈我只知道人是什麼〉知道的。
透過自己寫作與在世界各地演講的例子,余華在這篇散文裡想傳達的是,當我們一一剝開種族、國家等等的隔閡,最終我們將會「只知道人是什麼」,進而看見人們的共通與共鳴。至於《暴露的生命》則反過來告訴讀者,當我們看進車諾比受害者長期以來的困境,原先最基本、最生物性的「人」的模樣在不同政治的角力與傾軋下猶如被塞進箱籠生長的植物,扭曲,變形,甚至壞去──我們到最後,其實不知道人是什麼。
然而,無論是猶太大屠殺紀念館、余華的寫作、或者Petryna傾力完成的民族誌,它們都共同環抱著一個意念:要讓曾經被看成塵埃般的小人物「有記念、有名號」。在全書最後的最後,Petryna以美麗而沉重的這段話作結:
「在這裡,許多人正在與為了活下去所付出的代價奮鬥,同時──雖然比過去好了──在他們賴以為生的社會、經濟與政治世界中勞累。他們活在一個由科學、國家建構與市場發展共同交織而成的實驗場裡;在那裡,新的社會與制度形式持續刺探著公民身分與倫理的底線。在這樣的情況下,民族誌的作用在於捕捉那些擾亂、糾纏人們生命的元素,同時在人類存在的偶然與不可預料性之中,維持著一種對將來的敏感。」

Adriana Petryna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人類學博士,受業於Paul Rabinow與Nancy Scheper-Hughes等人,目前擔任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人類學系的Edmund J. and Louise W. Kahn教授,是當代具代表性的醫療人類學者。《暴露的生命》一書於2003年出版後便旋即獲得當年度美國民族學會的Sharon Stephens 書獎,而後更在2006年更獲得醫療人類學會的 New Millenium Award。
關鍵字:車諾比核災、醫療人類學、生物公民、烏克蘭、後蘇聯研究
這篇短文寫於2021年12月、俄烏全面戰爭之前,發表前只進行了部分微調。今天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第五天。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