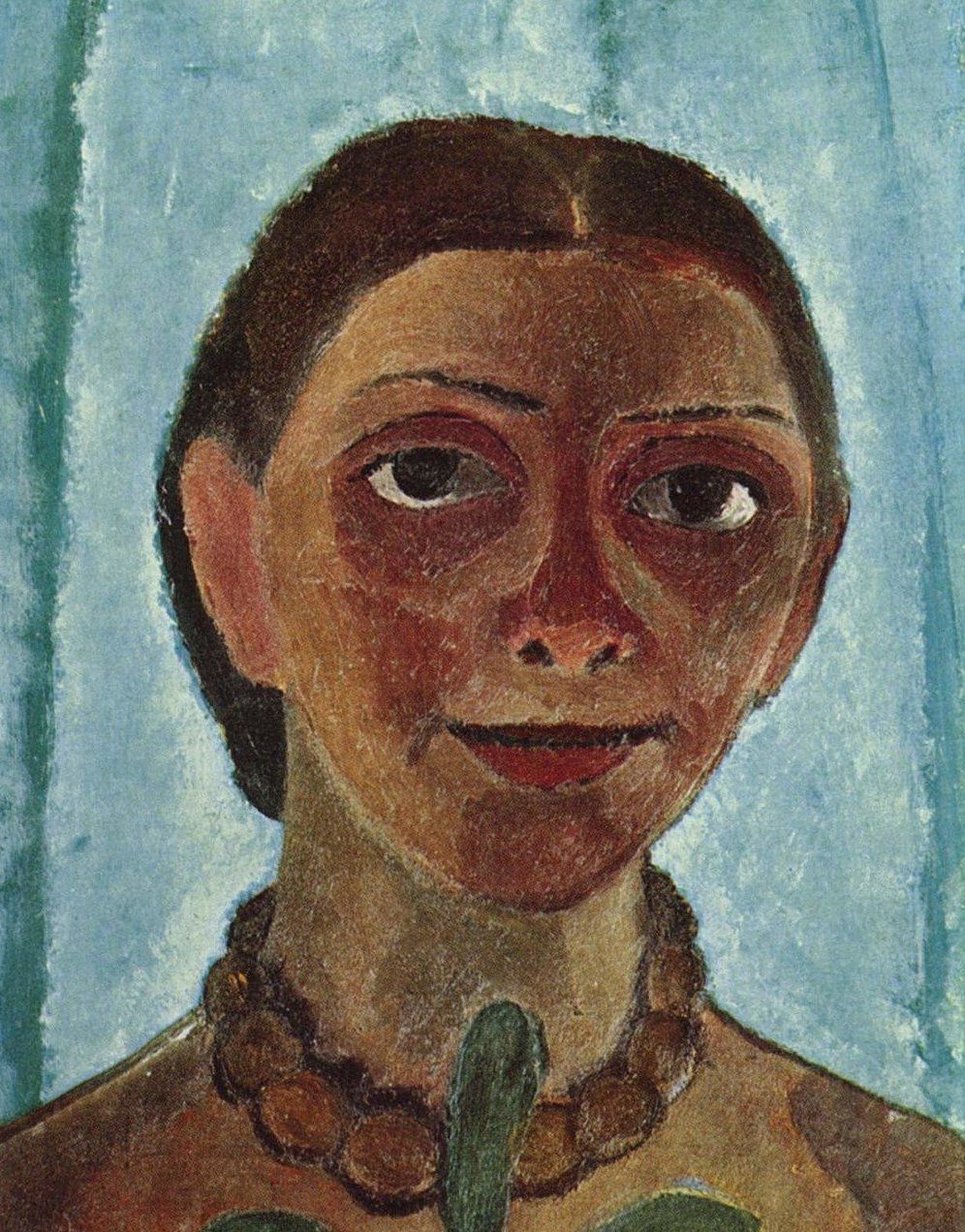流亡者的信仰
魔术师》 里阿尔玛·马勒对托马斯·曼说(大意),你不理解勋伯格,你把十二音体系写成一种技术,但是勋伯格对自己的体系有一种近乎宗教的情绪。虽然我着实不喜欢无调性音乐,但是这句话还是给我挺大震动,好像也能模模糊糊体会到一点那种宗教情绪。伯恩斯坦在哈佛六讲里提到勋伯格内心对调性的留恋,导致他在作品中不经意地流露出些许痕迹,那种蛛丝马迹中泄露的对调性的忍不住回归,但欲言又止,他终究不肯屈从内心冲动,决绝地扭头继续在音符中平等流浪。这种感情,写出来,说出来,似乎都比听到的更美。这真是件令人哀伤的事儿!
在他的十二音体系出来之前,勋伯格写过一首弦乐六重奏《升华之夜》(verklaerte Nacht),其实已在向无调性飘移,但整体仍流连在晚期浪漫派, 还带着那种belle epoque的迷人。曲子引用了Richard Dehmel的诗,诗的内容是女友向男友坦白自己怀了别人的孩子,而男友原谅了她,明月夜,爱升华。我其实不懂到底升华在哪里,但是这故事倒是让我联想到汉斯·冯·彪罗被老瓦戴了绿帽子,却仍一心一意崇拜老瓦。
我和伯恩斯坦一样热爱调性,听彻底无调性的音乐时感觉像晕船。我需要找家,我有乡愁。我不知道维也纳二小的一众才俊们都是怀着怎样的宗教情感走在他们那背离人性的的决绝之路上的。前些日Leila Josefowicz和村团演出伯格的小提琴协奏曲,上来就是四根空弦的长音,像我小时候初学琴时日复一日的枯燥练习,但这是整部作品里我唯一能记住的部分,因为接着听下去,我就晕了。现当代作品我都愿意听,但是只愿意听有调性的。伯恩斯坦说伯格比勋伯格可爱,我同意,但是好像也没可爱太多。四年前村团原定上演歌剧《露露》,我也早早订了票,本想在无调性中洗礼一下,结果被疫情冲了。据说《沃采克》是更好的作品,但如果不是现场,我终究提不起兴致自己看屏幕或听录音。表现主义绘画、无调性音乐、和魏玛共和国的混乱伦理,简直好像三位一体,但我真正喜欢的只有表现主义绘画。
维也纳二小的三杰,其中两位学生一位英年早逝(伯格),一位在门外透口气抽烟时被美国大兵一枪打死(韦伯恩),倒是流亡到美国的老师相对长寿与善终。二战结束前他们的影响巨大,美国的音乐学院作曲系被十二音体系的追随者占据,任何胆敢写调性音乐的,都得做好被嘲笑和不齿的心理准备。但二战之后,大部分作曲家也不知道怎么了,慢慢又返回调性了。而勋伯格在美国,是名声大,赚钱少。传言格什温满怀崇敬跑去找勋伯格拜师,勋伯格问他:“你一年赚多少?” “十万”。“那我应该拜你为师。”
今天一早起来,听了勋伯格为乐队所改编的勃拉姆斯g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把键盘部分都改到管乐,改编得真好啊! 尤其是铜管部分。不禁回味起伯恩斯坦说他的话,想起他早期的《升华之夜》。调性的美,其实是深刻在他心里的吧?然而音符的平等对于他,可能像正圆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科学家,是一种信仰、一种宇宙真理,所以哪怕抛弃感官愉悦与人性本能,他也必须遵从召唤走向那里。(哦,阿尔玛虽然人品堪忧,但音乐修养还真不是盖的!)从调性家园流亡,从欧洲的祖国流亡,绝对平等地流浪于十二个音符间,这简直像是圣徒宿命。
勋伯格可能是二十世纪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可能比马勒、斯特拉文斯基、拉威尔、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巴托克这些人更重要。但是他的作品很少被演出,因为,真的,大家不爱听。十二音序列更像一种纯粹的理论体系,我猜,大概它有一种数学的美,也许在谱面和在内心回味时都比听到时更美。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