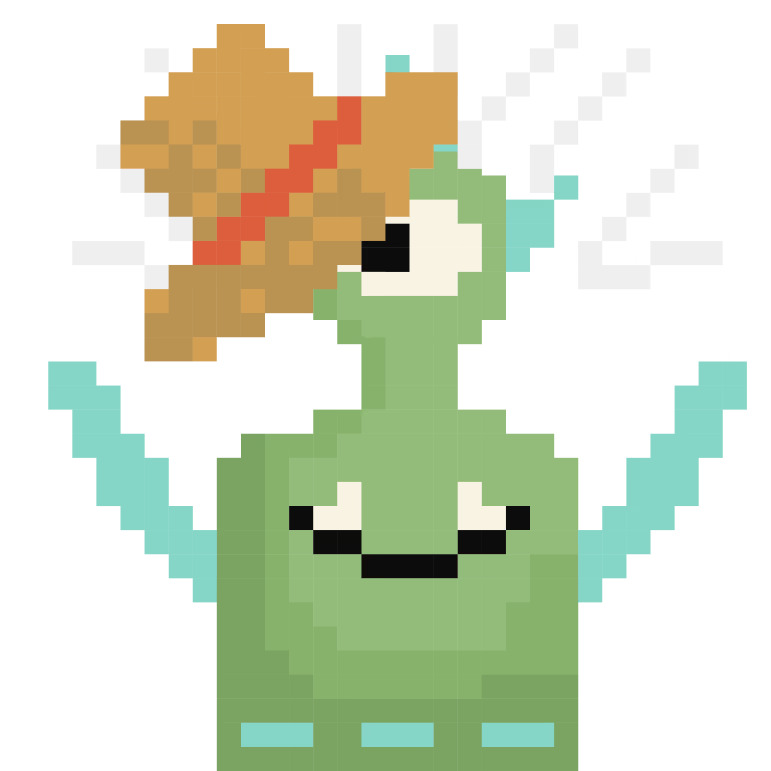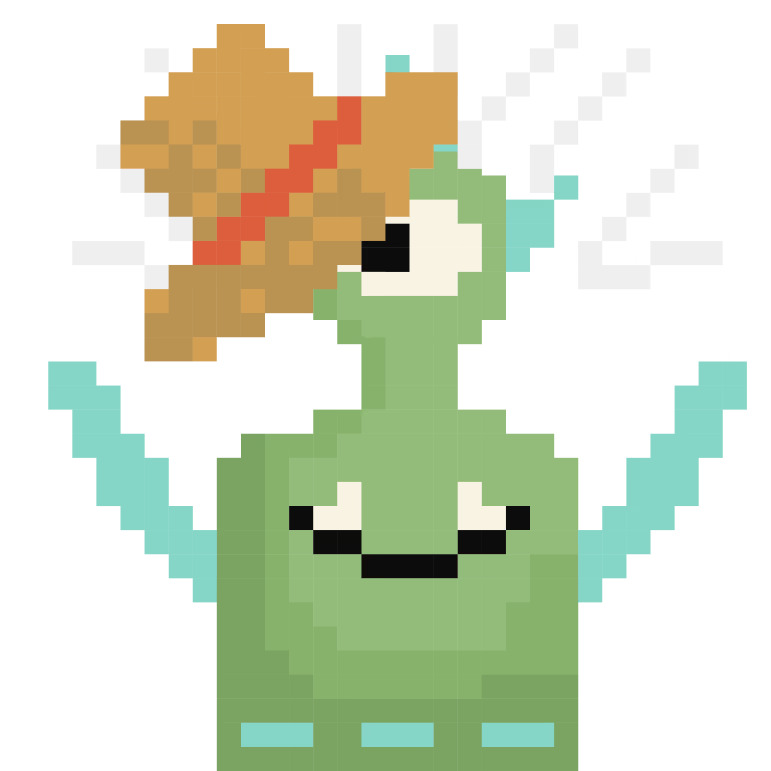2025年初雪·纳博科夫·基辛格·艾略特

都说是天有不测风云,但天气预报这次还算是十分准确。预报说星期六(1月5日)晚上要开始下雪,降雪量大约在8英寸。星期六晚上果然开始下起雪来。雪下到今天(星期日)早上,天亮一个小时之后才停止。
出门看,果然地面上真的是覆盖了大约8英寸厚的雪。
不知天气预报是怎么计算降雪厚度的。雪的紧密/密实度可以有很大的差别。有的雪花水汽十足,同样的含水量可以比空气十足的雪花要薄得多。天气预报部门又是怎么知道降雪的密实度的呢?或者,不管雪的密实度如何,只要含水量相同,雪的厚度就都大差不差嘛?
星期一要开车出门,今天必须铲雪,必须至少得把自家车道上的雪铲走,好让自家的车出入。
到车库去找雪铲。转了一圈,居然没看到。
返回家,问太太雪铲在哪里。她反问:你不是拿到工具房去了吧?
这倒是一种可能性。但到工具房去查看,就要涉过后院三四十米的积雪小路。不想去。于是就要太太去车库再找找看。她一向眼尖,这边则对自己的眼神一向没有自信,常常是东西明摆在眼前也死活看不见。
太太到车库巡视,果然在五秒钟之后找到了那把大雪铲。
不得不在内心里惊叹,我刚才怎么就看不见呐?
在写文发表出来之后,也不断有同样的、同质的惊叹——这么明显的错误,怎么校对了多少遍就是没看出来呐?
拿着雪铲从正门来到前院铲雪。
蓬松的、面粉一样的雪。应当是滑雪的好雪。先前认识的一个来自犹他州的朋友说,犹他州的滑雪场特别好,就是因为那里的雪跟面粉一样干燥。
但眼下这里气温高,贴近地面的雪在不断融化。铲起雪来扬出去,铲子上的雪会留下十分之一或八分之一。而且留下的雪是半融化的,特别有分量。不得不铲一下,再在地上磕一下雪铲。
雪虽然停了,但依然是完全的阴天。天气预报说,在星期一还会下雪。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地球北半球许多地方所谓的white Christmas(有雪景的圣诞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幅度减少,许多地区和国家的滑雪胜地也因降雪减少而不得不关闭,或惨淡经营并难以为继,或用经济/环境成本高昂的人工造雪机造雪(同样难以为继)。
去年这里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雪。现在终于下了一场规模还算可以的雪,按理说应当是喜庆的事。
隔壁邻居家的两个孩子,六岁到四岁的两个小兄妹欢乐地出来滑雪橇了。小男孩大声用中汉语冲着这边喊,“你好”。妹妹有样学样,跟着喊“你好”。
跟小兄妹俩来回寒暄,
小男孩很有趣。两岁不到就上托儿所,日常大部分时间使用的是英语,用汉语的机会不多,尽管他父母有意识地跟他讲汉语,但他能玩得转的汉语还使十分有限。他父母希望他多保留一些说汉语的能力,就鼓励他多说汉语。于是,他见到这边就叫喊“你好”。
典型的听话的好孩子,而且,也是一个大方、外向的孩子。生来比较羞涩的妹妹在他的影响下也变得越来越大方。
白雪皑皑,看上去赏心悦目。雪地上居然没有看到动物的新鲜足印,显示雪停止以来,这边还没有鹿或狐狸之类的动物出没。
三五只乌鸦在后院的树上飞起飞落,呱呱大叫,好像是对什么事情很有意见。
铲雪铲一两下或三四下还没什么。但坚持连续铲,不出三五分钟就会觉得累,很累。
二十世纪俄罗斯裔的英语世界小说好手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950年代任教于纽约州北部的康奈尔大学。那所常青藤大学位于深山老林之中的伊萨卡(一个来自古希腊的地名),一年几乎半年有雪。
据1999年出版并获得普利策传记奖的纳博科夫妻子维拉传记的作者斯泰西·希夫(Stacy Schiff)报告,每当伊萨卡下了大雪,人们多是看到维拉在他们家房子外面吭哧吭哧铲雪。
维拉之于纳博科夫可谓贤妻,之于他们的独生子(德米特里·纳博科夫,声乐表演家和翻译家)可谓良母。人们看到这位贤妻在康奈尔大学期间对丈夫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其中包括常常跟纳博科夫一起进教室旁听他授课,还认真做笔记,密切关注学生听讲状况,并直言不讳地当面告诫/责备那些不认真听讲的学生,说不认真听纳博科夫讲课是他们的大损失。
一边铲雪,一边玄想维拉和弗拉基米尔。
这边铲雪没多一会儿就觉得累了。而且,这里只是难得下一次雪,这次只是下了8英寸。伊萨卡那边动辄就是下两三英尺厚的雪,维拉不得不经常铲雪,她该是多么不容易。维拉身体显然真是好,心态好,无怪乎她比纳博科夫长寿好多年。
感觉明显累了,有意识地调整铲雪的节奏(放慢),争取达到一种平衡,不要太累,免得不可持续。
想起1971年7月,美国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来任国务卿)基辛格(台湾称基辛哲)跟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谈判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的事宜。基辛格在谈判的间隙跟周恩来闲聊,说起美国下了雪,人们铲雪是一个问题,因为总是有人不能掌握节奏,急于求成,导致心脏病发作一命呜呼。
确实,但凡不得不铲雪而且认真铲过雪的人都知道,铲雪动作本身会产生一种节奏,铲雪的人会不知不觉间被那种节奏带起,忘记或忽视了自己身体的节奏,从而导致心血管系受到过大的压力,不胜负荷。一般的人对跑步对身体的压力都有足够的认知和警惕,但对铲雪这样的上肢运动对身体的压力则缺乏足够的认知和警惕。
基辛格和周恩来谈判的文字记录当年是美国政府的绝密文件。20多年前,那些记录对外开放并且放到了网上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两人在谈判中的你来我往读起来非常有趣。
中共的宣传总是说,周恩来如何如何富有远见卓识,知识丰富,博闻强记。但这些谈判详细速记记录显示,尽管基辛格本人在他公开发表的言论中总是对周赞美有加,赞不绝口,但实际上显然他一直是以成年人陪小孩子玩的心态跟周恩来周旋,因为周恩来根本就没有什么远见卓识,知识也一点不丰富,尤其是对美国的基本知识匮乏得令人难以置信。
例如,早在1960年代初,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就变成电视了,但周恩来居然迟至1970年代还对此茫然不知;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防部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政府机构,但周恩来错以为中情局是国防部的下属机构。由此可知,当时的周恩来和中国外交部的美国知识水平有多么低下。
基辛格跟这样一个欠缺基础知识的谈判对手谈判应当是感觉轻松愉快,因为周恩来的思想/思路动向他可以一目了然,了如指掌,而周恩来对他的动向则是懵懵懂懂,云里雾里。但为了美国的和他个人的利益,基辛格在谈判期间和谈判之后的几十年里不断恭维和美化周恩来,称他为睿智的长辈。
然而,谈判详细记录显示基辛格对周恩来的夸赞完全是口是心非。在谈判的后期,毛泽东不懂装懂瞎指挥,外加毛的妻子江青的煽动,毛对周恩来的谈判表现提出严厉的责备,并要他对基辛格表示强硬。于是,周恩来便在随后的谈判中大谈美国的种族主义问题以及西方外交史(以体现毛当时所着力宣扬的他对世界大势的判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周恩来此举终于使一贯对他恭恭敬敬的基辛格失去了耐心。他直言不讳地当面调侃和讽刺周恩来道,周要在美国内政问题上说三道四并期望美国会接受,这是一种白日梦;周有关西方外交史的论说就算是正确也只是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气,可惜这世界不是按照大学教授的思维运转的(大意)。
基辛格的最后一句话从英文表达方式来说可谓十足的凶狠,恶毒,毒汁满满,实际上是对周恩来的多重无情讽刺挖苦——西方外交史属于基辛格的学术专业领域,不是周的,周显然是在班门弄斧,不堪一击,不值得一驳;基辛格先前是美国顶尖大学哈佛大学的教授,周恩来不是(周恩来二十世纪初到日本留学,连官费留学生资格都没考上,不得不铩羽而归)。基辛格如此说大学教授,好似是在我嘲讽,自我调侃,其实是在跟周恩来玩居高临下,调侃周。
这些记录读起来犹如戏剧,话剧。
一边铲雪,一边看孩子玩雪橇,一边思绪纷飞。铲雪的动作节奏有意无意地放慢下来,刚才的气喘也平息下来,算是达到了运动平衡。
小男孩的妈妈出来,陪他们兄妹玩。妈妈带着妹妹,跟妹妹一道滑雪橇。雪橇从高坡上滑下来,哥哥突然跑到滑道上。妈妈惊呼要他闪开,怕撞上他。哥哥躲闪不及,妈妈刹不住车,还是撞上了一点。幸亏滑行速度不快。
滑到头之后,妈妈站起来回头教训小哥哥:Why did you do that? It’s dangerous(你这是干什么呐。太危险了)。
妈妈调子很高,看来真是急了,生气了,也顾不得跟小哥哥说汉语了。
看着这一母子互动的景象,觉得好玩。大声对那妈妈说:That’s a learning process (这是个学习过程呐)。以那小男孩的聪明和乖巧,相信他一定学到了教训。跟聪明伶俐的孩子和学生打交道总是让人心旷神怡,成就感满满。
再低头继续铲雪。
往年这时候可以看到水仙和风信子叶片窜出地面。最令人惊讶的是,水仙花的叶片可以从冻得棒棒硬的土中冒出来。今年有没有水仙冒尖现在下了雪无法查看。但没下雪的时候也没想到查看。
铲着雪,英文短语“forgetful snow”(令人遗忘的/健忘的雪)在脑海中跳闪出来,徘徊不去。提起forgetful snow,许多人就要想到20世纪英文世界现代派最有名的诗歌,托·斯·艾略特的“荒原/The Waste Land”的著名的开头:
April is the cruellest month, breeding Lilacs out of the dead land, mixing Memory and desire, stirring Dull roots with spring rain. Winter kept us warm, covering Earth in forgetful snow, feeding A little life with dried tubers. 四月天最是残忍,它在荒地上生丁香,掺合着回忆和欲望,让春雨挑拨呆钝的树根。冬天保我们温暖,大地给健忘的雪覆盖着,又叫干了的老根得一点生命。(赵萝蕤译)很多很多中文世界(以及英文世界)讲艾略特这首诗歌名作的文章都说这开头充满反讽/戏仿,但却语焉不详,闪烁其词。一直不明白它们为什么不肯痛痛快快地点出它与早期现代英语最著名的诗歌、杰弗里·乔叟的长篇叙事诗《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的著名开头的关联,从而让读者、让学生得以进行对照、对比,比对,从而可以品尝欣赏艾略特在英语诗歌领域的继承和创新?
《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开头:
Whan that Aprille with his shoures soote The droghte of March hath perced to the roote, And bathed every veyne in swich licour Of which vertu engendred is the flour; Whan Zephirus eek with his sweete breeth Inspired hath in every holt and heeth The tendre croppes, and the yonge sonne Hath in the Ram his halfe cours yronne, And smale foweles maken melodye, That slepen al the nyght with open ye (So priketh hem Nature in hir corages);...四月以它甘美的阵雨把三月的干旱彻底穿透,以这种液体沐浴了所有的筋络,甘霖的力道催生出花朵;西风也以它甘甜的气息吹动各处树林和野地的柔嫩植物,初春的太阳行过了半个白羊宫座, 小鸟纷纷发出鸣唱,彻夜睡眠睁着眼睛(大自然就这样刺激它们的内心);...在乔叟笔下,四月充满阳光和生机。在艾略特笔下,四月则是一个最残忍的月份,谢天谢地,艾略特的四月被令人遗忘的雪覆盖着,但偏偏有不合时宜的春雨来搅动这份安宁...。
非常注重传统并认为新作品必须根植于传统方能获得意义的艾略特写出这个开头,明显是跟英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乔叟别苗头,并以此使他的诗歌获得历史的厚度和现代的意义。
艾略特这种别苗头大致相当于中国诗人跟杜甫的名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别苗头,很难很难,千难万难。
老邻居鲍勃(在拥有全世界最好的鸟类研究的康奈尔大学获得鸟类研究硕士)本科就读于耶鲁大学,主修早期现代英语。最初跟他说起《坎特伯雷故事集》时,他当场朗朗上口地背诵出这著名的开头。
当时跟他说,据说这首长诗的语言已经很接近现代英语,虽然看上去怪异,但大声朗读出来就容易明白。他好似漫不经心地回答道:好像不那么容易明白。
鲍勃是一个典型的英语世界的绅士,说话极其含蓄,委婉。他的意思显然是说,所谓的容易懂之说是误导,其实很不容易懂。这些年来,每次重读这著名的开头,都要想起鲍勃的话。确实是很难懂。或曰,很不容易懂,阅读理解障碍比比皆是。
太太从家里走出,走到车道上,走到身边。
调侃她:啊呀呀,你干嘛出来了呀?真稀奇,你不是一贯是逃避干公家的活嘛。
一边说,一边不禁想起纳博科夫夫妻。太太与维拉的差别,恰如这边跟纳博科夫的差别。
太太一如既往,对这边的调侃不接茬,只是平淡地说,还不是怕你累了嘛。
“啊呀,你真好。为什么不从工具屋把另一把雪铲也找出来,咱一块并肩铲雪,增进夫妻感情?”
“工具屋里还有一把雪铲?我从来没看见过啊。”
“有。绝对有。我看见过。就在工具屋靠窗的地方”
“那我去找。”
说着,她转身踏雪去工具屋。不一会儿空手而返。
“那里哪有雪铲啊?”
“就在靠窗的地方,我都跟你说了。”
“没看见哪。”
“好。我现在要是去能找来,你要给我什么嘛。”
“给你一百dollar。”
“好,这可是你说的。我转眼就到手一百美元,太棒了。”
一路踏着她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很快走到工具屋。开门进去,很快拿到雪铲。
一路往回走,一路惊讶她从来都是眼神很好用、超级好用,怎么这次给了她明确的指示,她居然还是没看见。
日常生活中出人意料的事情总是有。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