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的缺席與遺忘

近一兩年疫情關係減少外出,在舊照片底片堆裡找回一些舊記憶成為自己生活的一部份,當追溯到1989年5月到6月期間,驚覺自己只留下三張照片。那一年我剛成為一名設計系學生,正值思想大解放之時,對當時北京學生民主運動非常雀躍,也參與過不少遊行活動,理應會立此存照,找著找著,結果只能找到三張幻燈片,我甚至覺得這三張拍得很醜的照片並不是出自我手筆。照片中有我的背影在製作一張橫額,估計是為「五四」周年的遊行所製作,上面寫著的是有些現在看來很無聊幼稚、有關民主的口號,大概是當年我深受「達達主義」的影響,著迷於當時藝術家玩弄的 word play,這張橫額一開始就被其他熱心的遊行人仕拿去展示,後來也不知所終。
難道當時候我的經歷就只有這些嗎?當然不是,當年除了「五四運動」記念游行、歷史上百萬人上街,民主歌聲獻中華、黑色大靜坐等等我從不缺席,都是單人匹馬去參與;當北京宣佈戒嚴時,掛著八號風球跑到灣仔前新華社門口靜坐示威,灣仔道的雨水如川河流過自己褲管的情景我現在還歷歷在目,當然少不了屠城慘劇後那種被人掏空心肝的震蕩,而到今天被別人問起,我卻只能拿出這三張沒有面孔的照片。
當時作為一個攝影的初學者,對攝影的熱情本應是最澎湃的時候,雖然只有一台破爛相機,也未致於無機可用,本應不會放過任可以值得拍攝的機會,我卻有感召去選擇放下相機,選擇作為參與者的角色,對各種示威行動覺得要全心全意參與,當年思想比較青澀,不太去深究這種內心鬥爭。這段記憶縱然只有這三張蒼白的影像去觸發,但沒有影響它們刻畫腦海的能力。
或許很多人會說這些角色之間並沒有衝突罷,事實是否如此?很多年前讀過一本很有趣的攝影文集叫《Photographs Not Taken》,由美國攝影師 Will Steacy 編輯,邀請了62 位知名的攝影師分享他們一些沒有拍照的時刻,有些是當事人純粹忘掉帶相機,或在一個不容許拍照的場合,甚至是忘了在相機裡安放菲林,拍完才發現這一類經典的烏龍情境等等;但更多的是攝影師選擇捨棄拍攝的機會,例如不希望破壞與他人建立的互信, 又或是觸及自己的道德底線,有些卻是因為當時的行為跟其攝影師角色的相左,如當時剛誕下一對龍鳳胎的 Elinor Carucci,為照顧兩名初生嬰兒疲於奔命,作為攝影師她有本能的衝動去為孩子們去拍攝,每當她選擇拍照時,她就覺得「每張照片就成是令我疚悔的一秒鐘,是我疏忽照顧孩子的一秒鐘,是我只會想著光線、構圖或曝光的一秒鐘,卻與我的子女扯不上關係。」Carucci 形容每天攝影師的角色都會跟作為母親的角色宣戰,然而很多時候,是作為母親的她會取得勝利。Carucci 的為母之道(mothering)大概可以解釋我希望保留作為參與者的那份純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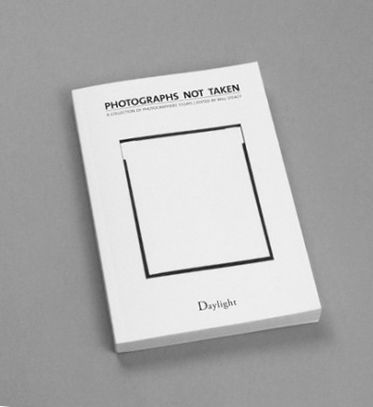
這些攝影師繪型繪聲把那些沒有拍照的場景描畫得細緻入微,影像的缺席並沒有令他們的記憶褪色,他們對一段段回憶無不珍而重之。當然照片作為觸發記憶的功能,在社交媒體爆炸的年代,「有圖有真相」的年代,沒有圖像襯托的記憶可能被視為不夠矜貴,其他人也會因此提不起發佈轉述的興味。
有段時期支聯會舉辦的六四燭光晚會,被一些年青一代認為是行禮如儀,嫌棄維園球場遍地燭光的僵化場景,不屑參與。好了,到今天這類「行禮如儀」的集會被各種形式打壓或污名化,以至刑事化,大家可能要有一個更崇高的任務:就是怎樣去拒絕遺忘,不要讓話語權被消費,經驗被扭曲,怎樣讓你的記憶好好保存,轉述。除了佔據報紙頭版外,我們以往仰賴每年維園這一張遍地燭海的照片,來作為薪火相傳的憑證,甚或是精神的支柱,應該以後也不會復見;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其最後名作《明室》(Camera Lucida)裡藉著一張作者母親五歲時拍攝,名為「冬日花園」的照片,對已逝母親的思念化為穿越時空的靈光湧現。這本小書裡基本上所有提及的攝影例子,都不會吝惜付上插圖,就是偏偏這張把整本書起了關鍵作用的照片,就刻意在書中缺席,引來及後無數讀者的遐想,甚至有學者認為這本來是一張沒有存在過的照片,巴特也在書中半帶暗示地說:這張照片只為我一個人而存在。對巴特而言照片的缺席是有意義的,照片只是他回憶母親的方式;在巴特的描述中,更重要的是照片帶來思考時間流逝、記憶調節、喪失、傷痛與死亡等事情的機會。
少了一張照片,真的不是一個遺憾,不用擔心因此失焦,再而被人遺忘,而是她被沉澱到更深層次的記憶領域,被好好的袒護著,讓其昇華為一份冼鍊的意志。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