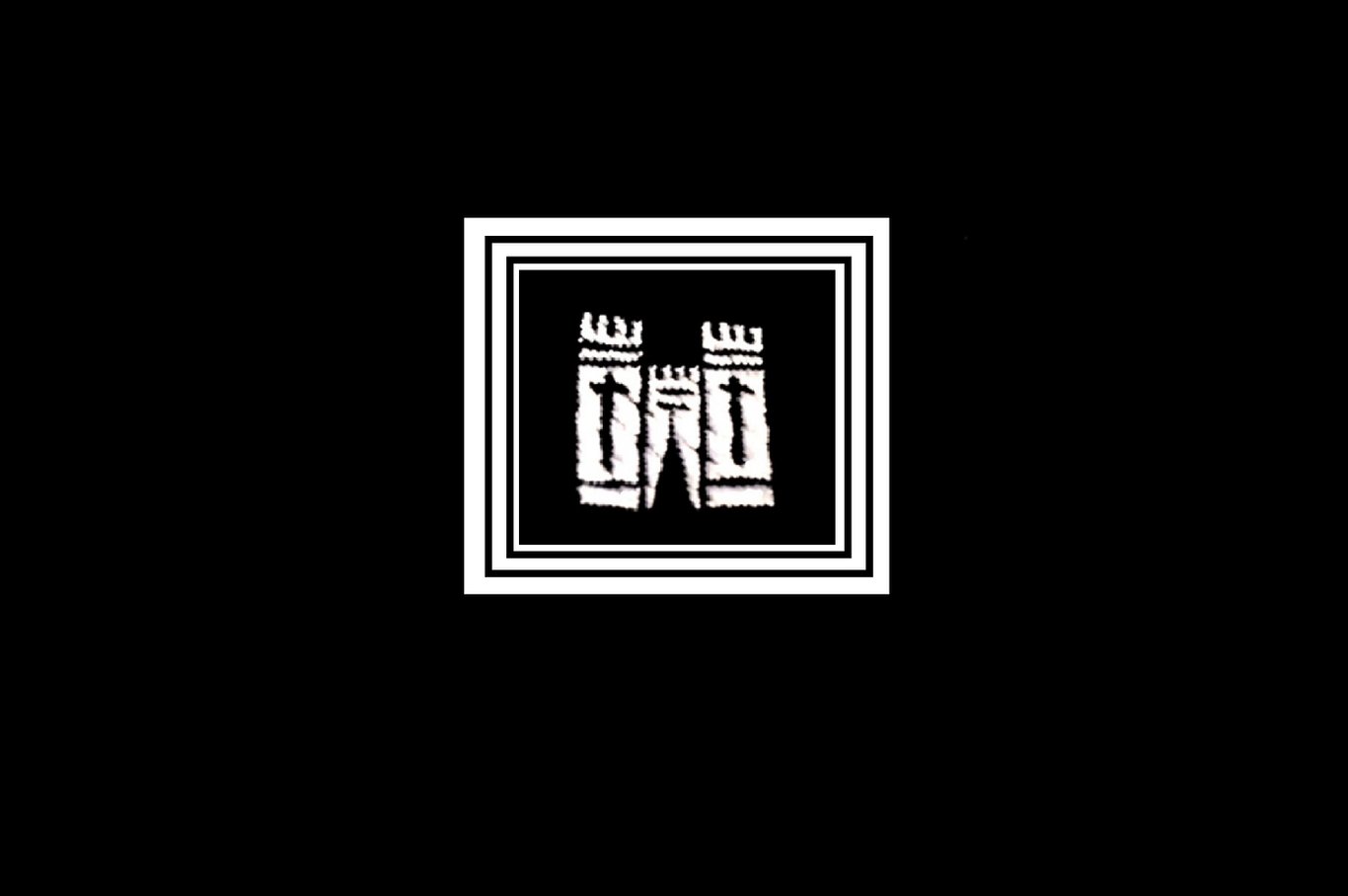唐山事件背后的父权同构
(原文发表于公众号,故而有所自我审查)
一件事情在不同的解读下有不同的面貌。
发生在唐山的这起恶行暴力事件,它既是明显的性别的问题——男人骚扰女人不行于是殴打,甚至劝架的也只打女人(这里先仅谈现象);它也无疑是治安的问题——施暴者此前劣迹斑斑,却没有受到治安系统有效的矫正。如同大多数严重犯罪都是从小事逐渐升级而来一样,公检法系统对他们此前的任何包庇(请参考起底施暴者身份的文章)都促成了这起事件的发生。
正常的思维来说,站在其中一个角度分析问题,并不是在否定另一个视角的存在和合理性。只不过是谈话者站在自己的视角所做的选择。那么,为什么有人从一个视角发声当中特意去否定另一个面向?
我想我可以理解物哀其类(的女人)对唤起人们对女性处境的认识,所以无论天然地从情绪上还是策略上都采取前一种视角。可是,非说这个仅仅只是治安事件,女人都是在“挑起性别对立”的人是怎么回事?有什么能比光天化日之下无差别攻击另一个性别更挑起性别对立的呢?是慌张于自己话语权的丢失,还是对女性或是女性积极呼唤权力身影的憎恶?还是紧抱自己传统利益与地位的男人和打压女权主义的呼声的权力体制的相互串通利用?
说到这里,分析便不能只停留在简单的事实层面。我要提出的是,治安机关对于这几个渣滓可能的包庇、他们对于女人挥起的拳头和酒瓶、以及舆论场上这些指责女性挑起了性别对立的声音其实都是父权制的不同方式的呈现。
父权制并不仅是一种性别的尊卑秩序,也不仅是一种家族体制内家长的权力垄断和安排。它还长期地植根于我们社会的大家长式的统治和权力结构当中,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基本底色。
本案中的施暴者性骚扰不成于是暴力殴打女性,显然是抱有一种将女性当成是应当被男性支配的性资源和下位者的观念。治安机关对他们的纵容和包庇,表明在这种一切对上负责的权力机构中,得宠的下位者可以凭借弄权的“坏家长”肆意撒泼,而其他的无权者对此无能为力。
更进一步地,无数生长生活于这个体制的个体早已把这种基于性别和尊卑的系统内化成为自然,对于他们来说,男人不该是侵犯女人,也应该去保护女人(参考胡锡进的微博发言和相关讨论),一如国家不该侵犯国民,而是应该去庇护他们。而提出“不需要男性保护好女性,只需要男性不去伤害女性”,以及任何希望借此事件呼唤女性意识和进行性别公共教育的人,才是秩序的僭越者。故而掌控舆论者刻意地要将舆论从性别的角度偏移,辅以数不清的“网友”继续着在社交媒体上对“女拳”的污名化。
继续沿着父权制的角度谈下去,我很欣慰于身边足够多的朋友们在一次次地为了正义发声。可遗憾的是,许多有力量的声音都被关在社交媒体的回声室里,最终消弭。当权的大家长对于任何能够产生社会自组织的团结于是潜在地削弱自己的权威的文化和有利于社会力量的机构(如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向来是采取打压的姿态。在这些文化意识中,性别议题曾是最后一个允许讨论的方面(没有任何贬低其重要程度的意思),但是当它在对立之上逐渐塑造起社会团结时,也确凿无疑地成为了家长打压的矛头所指,并被父权家长制的拥护者和维护传统性别秩序者或有意或无心地唾骂。
环顾四周,我们实在没有任何自下而上地动员社会力量去呼吁和敦促改变的能力。许多朋友(也许是基于舆论误导)看不上进来席卷西方世界的Metoo和BLM之类的运动,觉得那代表着民主代议制的乱象和“有毒的”政治正确。可是无论怎样,在社交媒体上受到推动的运动也在街头大规模地进行着,这才保证了它们广播社会各个角落,也自然包括上层制度的运动影响和遗产。我们的运动不止没有这样发展的可能,就连形单影只地在街上拍摄手里举着标语的艺术作品也风险重重。
在舆论场和社交媒体上的情况更并不必多谈。我们当然不是在自由中展开讨论,而要时刻应对着具有力量和睿智见解的言论遭受审查而留下的真空。剩下的支离破碎的情绪和暗讽则会被体制的维护者讥笑为不成气候的胡闹。
当然,我们好像还有种选择,那就是沿着体制为我们设定好的路子“建言献策”,譬如说争取将进来的种种事端反映到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去。这确实是一条受允许的正路。沿着它走,就只好再度把议程设置交到大家长手中去。苏格拉底把自己比作雅典城邦政治的牛虻,我们好似算不上牛虻,也许勉强是努力在大象身上爬动,希望能够有朝一日引起瘙痒将它唤醒的蝼蚁吧。
故而我对在回声室中积极发声的朋友们,有两种话谈:
假如你是被这件事唤醒了无论是基于性别问题的情绪或者对公共事件的意识。那么请你试图理解更多——为什么此前已经有那么多人就相似的事情呼吁过,还是会一再出现这类事;为什么你应当同样关注和理解受父权体制所广泛支配的其他社会与政治方面,而不仅仅是女性的安全问题和为自身发声的正当性;以及为什么你应该试图去团结和唤醒各种反父权制的力量,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性别化的,或者说女权的视角。
假如你已对审查和打压的议题有所认识,可是仅采取孤立的性别视角(或者是治安视角)作为发声的基点——这样更安全,更“就事论事”,但是这样也离实现发声所应有的目的无限地遥远,不是吗?对铁链女和唐山事件的记忆会被慢慢淡忘,可是父权体制压迫的方方面面仍然持续地存在着,甚至是变本加厉。在开展公共舆论的底线都不能保证的情形下,孤立地呼吁这一件事情真的有什么效果吗?那些潜在的性别施暴者是否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都成问题,更不要说形成对他们的威慑了。
当然,认识到了这些,可能仍然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因为我们终究不被允许以大家长和他所倡导的以外的任何事为中心而团结。而孤立的我们,似乎左右不了除了自己轨迹以外的任何东西。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