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吧!?——愛國主義與世界主義(下)

文|豬文
難度:★★★★★
前言
上回說到愛國這種一般會被視為美德的態度,如何淪為某些哲學家眼中的道德罪惡。這個認為國族身分沒有任何價值的想法,是種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立場,而世界主義又以自由主義式的道德觀作為基礎。然而,不少哲學家都頗為不滿這種道德觀。有別於世界主義與自由主義者,他們不認為道德的基礎只在於世界公民身分所包含的理性思考能力,反而主張道德必然要建立在我們的限定身分(local identities)之上,例如家庭與國族身分。如此想法,可稱為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
世界主義與社群主義的辯論最為有趣的是,當世界主義者控訴愛國的態度窒礙了人的道德思考,社群主義者同樣指訴世界主義者要求放棄我們國族身分,破壞了人的道德生活。究竟,國族身分對我們的道德生活為何重要呢?[1]

愛國主義者,愛的是甚麼?
在正面說明社群主義的論證之前,必須先簡單回應一下世界主義對愛國主義的批評。首先,其中一個批評是,愛國主義的態度基本上就是不理性且不道德。因為愛國主義並不如世界主義般,可以抽離一切限定身分,然後客觀地檢視判斷合理與否。國族身分的認同,是愛國主義者不可或缺的特性:如果失去了這種認同,他便不再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了。
這特性在世界主義者眼中,正正是不理性的。因為國族的好與壞,也應該如其他一切事情,放在陽光底下反省,而非無條件地擁抱自己的國族身分。愛國主義者甚至可說是不自由的,因為他的思考必然受國族身分綑綁。
面對這個批評,愛國主義者也會承認自己不能像世界主義般自由地批判其國族身分。話雖如此,我們必須先公平地理解愛國主義。這裡的關鍵,不是在於某個愛國主義者不能自由地批判的東西(愛國主義也不可能否認有這東西)是否存在,而是愛國主義者不會批判的東西究竟是甚麼。澄清了這點之後,我們才能正式評估世界主義的批評。
那麼,免受愛國主義者批判的東西是甚麼呢?這絕對不是任何掌權政府或者具體政治行動。任何當權政府或者具體政治行動,其實都在愛國主義者的理性批判範圍之內,愛國主義者並不會因批評政府而自打嘴巴。
哲學家 MacIntyre 曾以二戰時的納綷德國外交官Adam von Trott 為例說明這一點。Adam von Trott 在二戰期間一直為納綷德國工作,並隱藏着自己其實深徹反對希特拉以至納綷德國。到了 1944,Adam von Trott 終於執行了暗殺希特拉的計劃。最後,Adam von Trott 當然暗殺未遂。希特拉死裡逃生,Adam von Trott 也隨即被納綷德軍槍決。

Adam von Trott 故事的重點是,他的目標是從內部取代希特拉,而不是全面推翻納綷德國。因為他相信全面推翻納綷德國會導致這個幾經辛苦在 1871 年才建立起來的國家 —— 德國 —— 趨向滅亡。即是說,一直驅動着 Adam von Trott 行動的並不是世界公民這個身分。他要刺殺希特拉,也不是為了所謂整體世界公民的福祉。他的動力來源自德國人的身分,他是為了德國才這樣做。[2]
這個例子說明了的是,愛國主義者從來不用無條件地接受當權者所有決定。當權者也在愛國主義者的批判範圍之內。Adam von Trott 作為愛國者,他一樣可以刺殺希特拉。更重要的,是 Adam von Trott 的故事也說明了甚麼才是愛國主義者真正不能放棄的東西:國族作為一個共享著生活、文化、歷史的政治群體的延續。延續的計劃與理想,方是愛國主義者不能批判的東西。 Adam von Trott 可以批判納綷的侵略,批評希特拉,但他始終沒有放棄的,是延續德國的理想。也正正是這個理想,他才要暗殺希特拉。
對愛國主義者而言,一切個別領袖、政府、政治舉動、政體都可以批判,視乎它們究竟推進抑或破壞了延續國族的計劃。在澄清了這點之後,愛國主義還算是不理性嗎?可能算(世界主義甚至會覺得一定算),但起碼愛國主義已沒有起初看起來盲目,因為愛國者能自由地批判的東西其實也有很多。唯一不能批判的只是國族的延續本身而已(這一點很合理,因為若然他不希望國族的延續,他便不能算是愛國主義者。而國族的延續,很多時必須依靠同胞過得幸福。所以同胞的幸福亦成了愛國主義者所不能批判的東西)。
那麼,我們下個問題便要問,為甚麼這個共享着生活、文化、歷史的政治群體的延續是如此重要?愛國主義(或社群主義)的答案是:失去了這個群體,我們也無所謂道德生活。
要愛別人,先愛你自己?
為甚麼群體是道德不可或缺的部分?我們可以聯想到一個十分日常的講法:你連自己都不愛,怎可能愛別人?箇中想法是,我們不是全能的上帝,不可能站在一個全能者的角度,一開始便愛着所有世界公民。即使世界主義是對的,我們不應只愛我們的家人朋友同胞,也應該愛所有世界公民,我們能夠做到這點,也是因為我們一開始懂得愛我們身邊的人。這種由親及疏、「擴張式」的圖像,可說是我們對道德學習的最平常理解。如果我連同屬一個國族的人都不愛的話,我又怎可能去愛那些素未謀面、有着截然不同生活形態的所謂世界公民呢?
可是,這個論證對世界主義者可說是無力的。首先,如此看來很符合常識、「擴張式」的圖像真的是對的嗎?Nussbaum 便曾質疑過這種圖像並非唯一可能的理解。她認為小孩並不是從愛父母、愛鄰居、愛同胞擴充開去,才學習到要愛一切人類:回想一下與小朋友相處的經驗,其實他們從一開始便對其他人的痛苦便十分敏感,例如當我們帶小朋友去窮困國家旅遊時,他們看到那些貧窮的人,比起成人總會更有同情心。他們的關心就是如斯單純有力,反而是我們這些所謂成熟的大人,受到國族的意識形態的污染,變得冷漠。Nussbaum 認為小朋友早在未學懂國族的區分之前,便對人的價值有種原初的理解(”they know something of humanity”),他們只是透愛身邊的人去實現這種想法。[3]
另外,即使這個就道德學習的理解是正確也好,對世界主義者來說,這只說明了道德生活的發生歷程,並不能說明道德的本質。當中講法就好比在說:「因為我們必然要在某個具體時間,某個具體的課室,與一班具體的同學,向某個具體的老師學習數學。所以,沒有社群便沒有數學。」這想法顯然說不通,因為我們如何學習數學的過程,與數學真理的內容與證成、為甚麼我應該受數學真理的規範等問題都沒有關係。我們不會說「1+1=2」是建立在我與那些同學、老師的相處經驗之上,縱使我們學懂「1+1=2」是透過這些經驗。換言之,即使我們通常甚至必須在特殊的群體生活之中學習道德,並不代表道德規則的內容與證成、為甚麼我要過道德生活等問題的答案,是建立在那些特殊的群體生活之上。
沒有普遍理性?
因此,社群主義者不可能停留在道德學習的層面上說明國族身分與道德的關係。討論下去,便必關聯到另一個極度麻煩的問題:道德規則是如何被證成的?社群主義的大體想法是,社群共同的生活經驗是這些道德規則得以證成的最主要(甚至唯一)來源。[4]
問至那些具體生活經驗在證成道德規則扮演甚麼角色時,我們同時也在問純綷理性可以為我們指引甚麼。一些立場較極端的社群主義者會認為,普遍的理性根本是無力,甚至不存在;單靠理性本身是不能告訴我們應該做甚麼、不應該做甚麼的。對於世界主義所高舉的普遍理性,社群主義者極度懷疑。
社群主義認為我們的道德思考從來不是一種非個體的(impersonal)的角度出發,思考究竟有甚麼必然是對的。反而,道德思考更像一種摸着石頭過河的進程:我們一直與身邊的人共同站在一艘道德的船上,這艘船是我們要反省、調和、改進、擴張的對象,但也提供了唯一的工具與資源,使我們可以反省、調和、改進、擴張它。
回到上述 Adam von Trott 的例子,德國文化本身就是他唯一的資源,使他能夠判斷納綷德國是個錯誤的判斷。當納綷德國把那些猶太德國人送進集中營時,本身就違反了德國文化。例如這些猶太德國人當中,可能有很多曾經在一戰為德國獻身,勇敢地為國效勞。按德國文化,他們都是十分卓越的人,應該受其他德國人以至政府的尊敬。納綷德國的反猶意識形態,本來是就不為德國的國族身分所容許。可見 Adam von Trott 的判斷並不需要也不應該訴緒於所謂整體的世界公民。「這是為了整體世公民的好處」一類的說話,要嘛是句只有修辭效果的廢話,要嘛就難以單純由理性證明,受所有理性存有者(rational beings)所同意。
究竟有沒有普遍理性呢?承自康德的自由主義者當然會認為有,有些道德規則是所有世界公民只要運用理性便會同意,例如人不應該為了獲利而說謊。然而,這個回應又能否成功反駁社群主義者?
理性能告訴你甚麼?
世界主義與社群主義的大辯論,當然不可能這裡三言兩語說明足夠,但即使你覺得社群主義對於普遍理性的懷疑態度過於極端也好,你仍必須認真思考社群主義的想法。因為即使退一步,社群主義者同意理性可以獨立地告訴我們一些普遍的道德判斷也好,他們仍然會說理性能指引人的東西實在少之又少,少得只佔據我們道德生活中十分狹窄的部分。
或許,理性的確可以告訴我們甚麼行為是錯的、不被容許的,如為了獲利而說謊是錯誤的。然後呢?認識到甚麼行為是被容許/不被容許,只是我們的道德生活中的的很小部分。我們還想知道甚麼是好、甚麼是勇敢、甚麼是仁慈、甚麼是有意義的。恰當地回應這些問題,明智選擇,才能令我們道德生活如此豐富、精彩與複雜,但這卻似乎不是單純運用理性便足夠。
例如我們認為孝順父母是好的。可是,真的是理性本身就能夠證成的嗎?設想一下,一種沒有家庭生活的外星生物來到地球,你還真的可以單憑理性向他證成孝順父母的價值嗎?如果他不被你說服,他便因此是不理性嗎?我們發現,要證成這些倫理規則,靠的就是社群共同的生活經驗。為甚麼孝順父母是好的?因為一段美好的父母與子女關係,可以使你的人生變得美滿。為甚麼這樣的人生是美滿?因為我自己、我身邊的人以至我們的社群都曾享受過或正在享受這種生活形態。能夠證成孝順父母是好的,就正正是那些活生生的、具體的、由整個社群共享的生活經驗 ── 那頓與父母一起吃的飯、過年時一家團聚時的笑聲、父母關心你的說話。對於沒有與我們共享這些經驗的外星人來說,上述倫理規則是不可解的,我們也難以單憑理性向他們證成這些規則。邀請他們進入這種生活,方是我們最能夠做的。

就這一點,哲學家 Putnam 便曾批評世界主義以為理性或者世界公民的身分是道德生活唯一的合法基礎,想法荒謬。他說:「要理解(世界主義的)這個錯誤,可以想像某人認為好的音樂應該建立在普遍理性之上,而不應該預設任何跟音樂傳統的扣連 ── 我們會對他說甚麼?(To see the error, imagine what we would say to someone who argued that good music should not presuppose any prior acquaintance with a musical tradition, but only universal reason)」。[5]
我們要規劃自己的人生,思考怎與他人相處,不只需要知道對與錯,更要知道何謂好與壞,有價值與沒有價值,仁慈與殘忍,恰當與不恰當。這些問題都不是理性本身就能夠告訴我們的,缺少了社群共同的生活經驗,我們都無從尋找答案,也無從過道德生活。MacIntyre 說:「我在我個別的社群中,找到我跟隨那些道德規則的理由。除去這些社群生活,我便再沒有理由變得道德了。(It follows that I find my justification for allegiance to these rules of morality in my particular community; deprived of the life of that community, I would have no reason to be moral)」[6]
道德動力?
最後,社群也提供了我們行道德的動力。我們都不是全能的上帝,按道德規則處事對人類來說,十分艱難。社群正正是協助我們遵循道德極其重要的動力。我之所以願意做一個道德的人,是因為我們都是道德的人。我之所以願意跟隨道德規則而活,是因為我們都一起如此做。一個共同的道德群體,是我行道德時必須預設的背景。
唯有被置在一個分享着道德生活的社群之中,人才有動力行道德。沒有了身邊人的尊重與批評,我們無法成為一個道德行動者(moral agent)。當然,這不是說一個「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孤獨的「道德英雄」不可能 ── 即使可能,也不是我們受驅動去行道德的典型。對大部分一般人來說,社群是不可缺少的。
價值真空的現代社會
失了國族這些社群,我們無法學習道德;失了國族這些社群,我們無法證成道德;失了國族這些社群,我們沒有動力去行道德。因此世界主義對國族身分的負面態度,才正正威脅着道德。
與國族成員之間的共同生活經驗,讓我們得以學習道德、證成道德、有動力去行道德。因此,延續國族的正面態度,反而是整個倫理世界的基礎。
回想當今的世界,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原子,或曰獨立的世界公民,國族等社群似乎不復存在。社會不再是一個共享着倫理生活的群體,而只是個體之間互相合作的場所。世界公民的身分真的足以把我們連在一起嗎?取消了社群的世界真的比從前變得更加美好嗎?
注腳:
[1] 本文主要參考了社群主義哲學家 Alasdair MacIntyre 一篇名為 ”Is Patriotism a Virtue” 的文章。
[2] 這裡關於 Adam von Trott 的描述源出 MacIntyre。我並沒有查證過是否準確,或許有熟悉納綷德國史的室友會有所質疑,十分歡迎各種指正。不過即使 Adam von Trott 事實上並非如此也好,這並不影響 MacIntyre 的論點,因為只要這個版本的 Adam von Trott 是我們能夠想像且不太罕見的話,MacIntyre 的論點便能成立。
[3] Martha C. Nussbaum For Love of a Country: Debating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
[4] 由於問題實在太過複雜,牽連太多道德哲學問題,在此只能盡量從略而務求不失準確。
[5] Hillary Putnam, “Must We Choose between Patriotism and Universal Reason”.
[6] Alasdair MacIntyre, ”Is Patriotism a Virtue”.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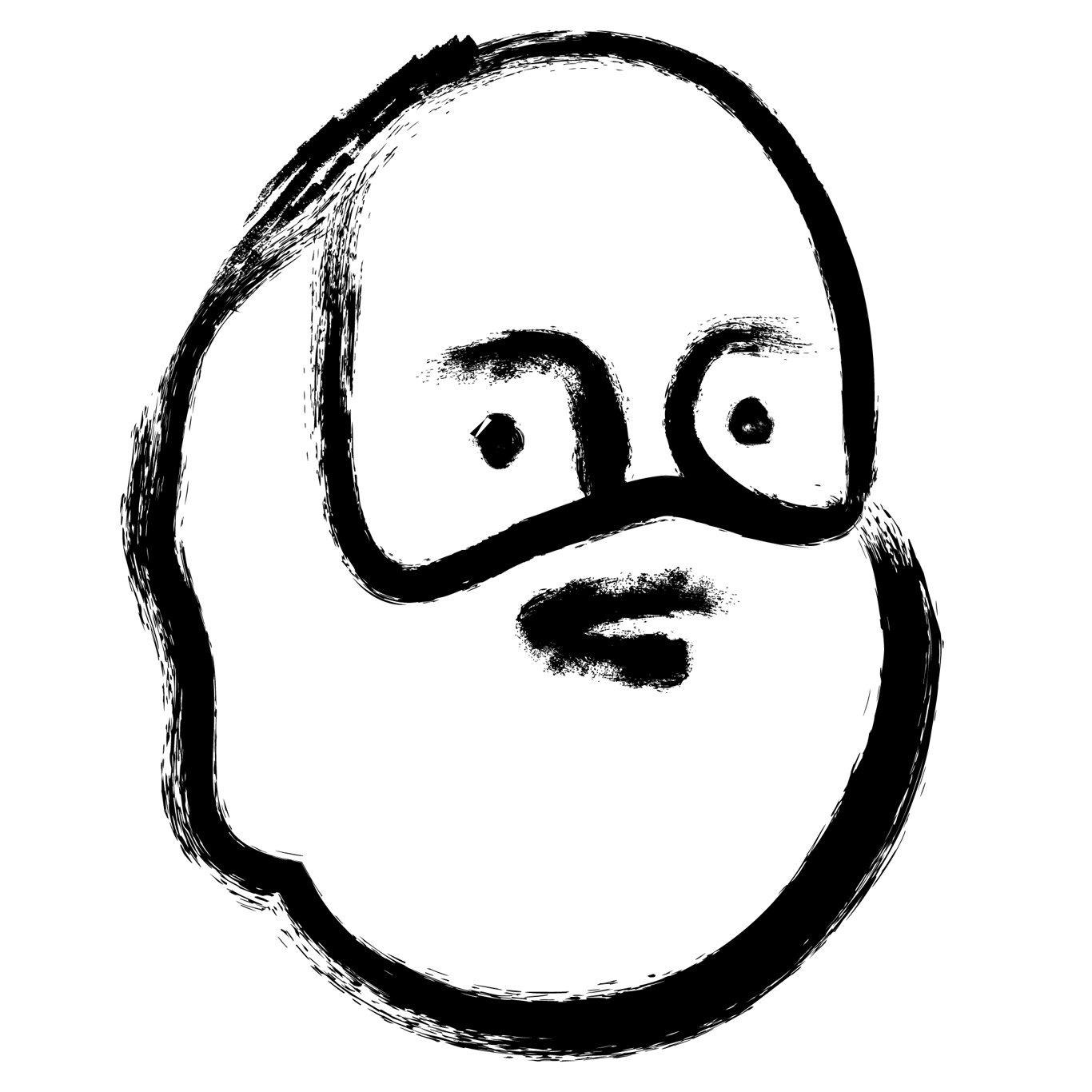
- 选集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