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思考抵抗狂熱,用愛擁抱日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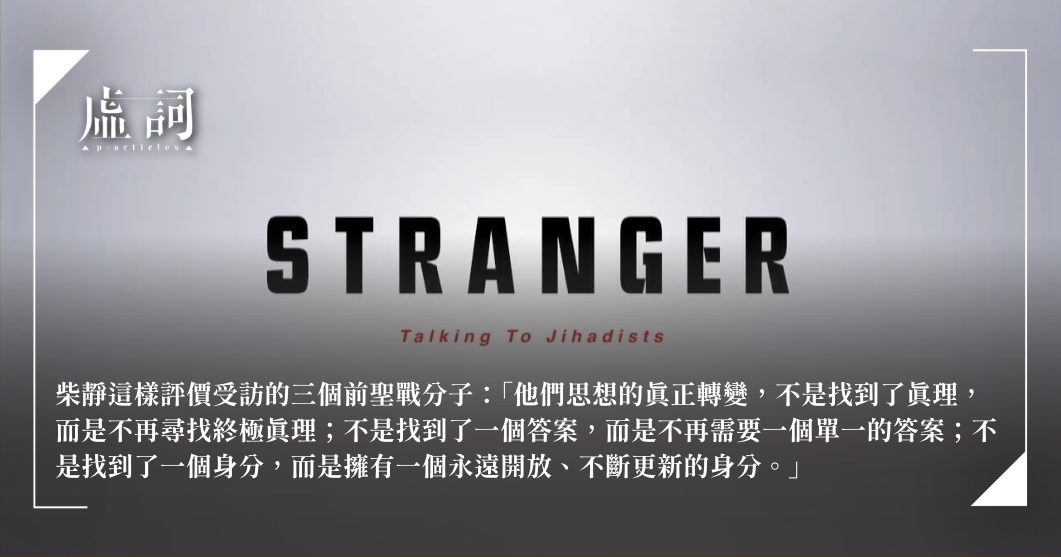
文|Sir. 春風燒
「我接觸過暴力型的精神病患,這三個人都不是這個類型。他們沒有幻聽幻覺,沒有人說腦子裡有人下令讓他們殺人。狂熱者是對一個抽象的目標執迷,他們來自不同國家,說不同語言,但都自稱薩拉菲主義者,談論的是同一個被宗教概念包裹的政治目標,那就是要在全世界實施字面主義的伊斯蘭教法……人們認為恐怖分子是瘋子,但是從我的採訪感覺來看,他們不是精神病學意義上的瘋狂,殺人是推理的結果。人類立法者是假神,宗教成了政治,暴力就成了表達虔誠的最高方式。地獄天堂作為獎懲制度,殺人自毀就成了功利計算,一旦進入他們的邏輯軌道完全封閉,就像我女兒的玩具小馬,一旦打開開關就按照設定路線走,它絕不拐彎,僵直向前走到牆邊,碰墻也不停下來,兩眼直瞪,不斷地抬起腿,踢在牆上。因為它看不到障礙,也不承認牆的存在。」
——柴靜《陌生人》第二集《絕路》
昨晚,六集紀錄片《陌生人——柴靜對話聖戰分子》連載完畢,每集看完令人心生敬佩又心有戚戚。柴靜在2017年離開北京,舉家搬到巴塞羅那生活,打算結束自己20年的記者生涯。一天傍晚,她在家做晚飯,窗外忽然傳來槍聲,沒過多久,一架直升機飛過屋頂。她意識到,恐襲發生了,她一手把聞聲走出陽台的女兒抱回屋內,而她的丈夫此時在回家路上,遲遲沒到家,幸好是因為恐襲發生後封了路,要繞道才晚了點到家。原來,聖戰分子駕駛一輛貨車闖入步行街,瘋狂撞擊逃避的人群。開到蘭布拉的中心米羅馬賽克(畫著巴塞羅那心臟的標誌)上,車才停下,而停車的原因,是捲入車底盤的人太多,車開不動了。幾個小時後,凌晨一點,離巴塞羅那100公里外的小鎮坎布里,又有一輛汽車衝入人群,五個人從車裡鑽出來,他們身上綁著爆炸物,用刀子和斧頭殺害了一名女性,並刺傷了五個平民和一名警察。
在策動本次襲擊的組織裡,1/3的人收入良好,1/3的人有犯罪記錄,有高中生和未成年人,還有西班牙本地的皈依者。我們很容易理解有暴力傾向或收入偏低的人會參與其中,可是,為甚麼被吸引進這個群體裡的,還有工作穩定的人、家庭富裕的人、父母雙全的人、名校在讀的人、無犯罪史的人?為甚麼他們進入了這個群體之後,就像感染了某種病毒,所有人都只剩下一張殘暴而狂熱的臉?
柴靜決定重新撿起記者的身分,自資自製一部紀錄片談論恐怖主義。「不要沉默,談論它。恐怖要靠神秘才能夠維持;曝光它,它將會失去所有的控制力,從空中塌落。」柴靜如此說道。
柴靜採訪了三名前聖戰分子(或者說,前薩拉菲主義者)、部分學者以及受害者家屬。放諸全球,採訪聖戰分子並不算得甚麼新鮮事,但就中文世界而言,意義非凡。加之,柴靜以女性身分涉足薩拉菲主義的議題,本身就是一場勇敢的冒險。聖戰分子一面支配、淩虐、出售女性,用暴力壓抑和掩蓋自己的慾望,但另一面又幻想死後能上天堂,坐擁七十二名對他們又愛慕又崇拜的處女。前伊斯蘭激進傳教士法里德・本耶圖與柴靜有這麼一段對話:
「男人天生總被女人吸引,女人天生就想勾引男人,因此女人是低一等的造物,是撒旦用來轉移人們對宗教注意力的最好的工具。女人最好的位置就是家,待在家裡,照顧孩子,前提是你還得交一些賦稅。」
「如果我拒絕賦稅會如何?你會把我殺掉嗎?」
「很不幸,會的。那個時候的我,不可能把你當人看。從神學上說,你這個種類是不存在的。」
「那你把自己視作人類了嗎?」
「我是最好的那種人類。」
柴靜白眼。
古蘭經聖訓確有記載,給上天堂的人最小的獎賞,是一座有著八萬名奴隸和七十二名處女的住所,雖然很多穆斯林學者認為這只是一個寓言,而且對此可以有很多種解讀。「但對聖戰者來說,沒有神話,一切從字面理解。」柴靜說。
「字面主義」是薩拉菲主義者的行動指南,你只需要一根筋地遵照聖訓的字面意思執行,不准提問、不許質疑、不聽不看異教徒的說法和書籍,甚至不用考慮聖訓寫作時的歷史背景。他們反對理性,理由是人的理性和推理有可能犯錯,而神的旨意完美準確——由此引申:人類創立法律和社會制度是妄想自詡為神,是一種瀆神行為,因而被上帝選中的他們就要用暴力懲罰這些遵守世俗法律的人,直到他們臣服為止。本耶圖說:「古蘭經聖訓和伊斯蘭教法只能從字面上刻板執行,任何人類解讀都違背『認主獨一』(Tawhid),是想要淩駕于真主之上,就是Shirk(偶像崇拜),必下地獄。」
本耶圖有個學生叫謝里夫・庫阿奇,他是2015年法國巴黎查理周刊總部槍擊案兇徒之一,他自稱薩拉菲主義者。「薩拉菲」的本意是虔誠的先輩,只承認先知與前三代聖門弟子,自認是真正的穆斯林,所以他們從穿著到生活方式,都要回到一千多年前,對一切行為分成「許可」和「禁止」兩個部分,音樂、酒精和男女混合都讓人遠離真主、導向Shirk——崇拜足球明星是Shirk,拍照和雕塑也是Shirk,因為人想要創造形象,就是把自己當神。Shirk無所不在,必須活在對它的恐懼中。總而言之,你的人生裡,崇拜對象只能有一個,那就是真主。
伊斯蘭教法有「Hudud」的說法,意思是上帝規定的界限——偷竊者要砍手,有婚外性行為者受石刑,搶劫者釘十字架,等等。任何不從字面意義上遵從伊斯蘭教法的人都可以視為罪犯,而違反真主意願的人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罪犯,殺死他們是理所應當的。柴靜說:「千年以來,Hudud沒有被普遍地使用過,但是聖戰者正是把它當成意識形態的純潔性象徵,必須從字面上執行。而一旦追求所謂的絕對純潔,離恐怖就不遠了。」
然而,他們真的能做一名「純潔」的教徒嗎?本耶圖對著鏡頭坦承他從來做不到。正如字面主義一樣流於表面,他們的「純潔」也只是一場公開表演。柴靜指出,尼泊爾的襲擊者一邊造炸藥一邊找妓女,謝里夫・庫阿奇的電腦中有戀童的照片,911劫機者在襲擊之前去看大腿舞,而本拉登住所裡也發現了大量的色情文檔。為甚麼狂熱的原教旨主義者會做與自己宣稱的信條完全相悖的事,結果連最基本的戒律都守不住?因為他們要的根本不是虔誠,只是要表演虔誠和表達虔誠,表面嚴肅,實則放蕩。自欺欺人的「絕對純潔」便於他們執行家法時獲取某種合法性、正當性,甚至是神性,掩耳盜鈴以自洽。忠誠?不過是一種膚淺的姿態罷了。
薩拉菲有三個派別:進修派是從社會底層推廣,政治派則通過政治方式來推行,而聖戰派是要用暴力強迫別人接受這個目標。聖戰分子中,一部分人負責膚淺地解讀經文字面意思,就以神之名傳播教條,另一部分人則負責發動襲擊,把傳教士灌輸的未經審視的教條毫不動搖地付諸實行。謝里夫在襲擊之後大聲喊道:「我沒有殺人,我們是先知的守護者。」對他們來說,他們面前的不是人,而不過是通往目標的障礙,殺掉他們就是解放他們,而如果自己戰死了,就能上天堂。古蘭經說,不允許無辜虧害殺人;古蘭經又說,你們不要自殺,安拉(Allah)確是憐恤你們的。——顯然他們都置若罔聞,不太感興趣。
他們一只眼睛回望過去,追溯原教旨、從字面意義上執行教法,另一只眼睛前瞻未來,期待上天堂後坐擁數之不盡的處女和奴隸,卻沒有一個視角留給「當下」,他們對現實視而不見,或者說,他們逃避現實。柴靜在一個恐怖襲擊遺留的廢墟裡找到信的殘片,發現恐怖分子把敵人稱為十字軍罪人、不義者、腐化者,署名是安達盧西亞土地上的士兵。她發問:「十字軍是基督教的軍隊在14世紀早已消失,而穆斯林統治安達盧西亞是八百年前的事情,他們到底生活在甚麼時空?在與誰為敵?」
極端主義創造了抽象的敵人和時空,壓制信徒的感受和懷疑,讓他們去攻擊具體的人,但這些被壓製的東西是可以被喚醒的。前聖戰者曼瓦爾・阿里在這十五年來,讀了許多以前被他稱為「異教徒所寫的書」,這讓他遠離了肯定和單一,轉而擁抱懷疑和多元。他說:「先知說,知識雖遠在中國,亦往求之。知識可以來自任何人,印度教、錫克教、世俗者、穆斯林、非穆斯林、砍繆尼斯特、餿席嘔李斯特,誰在乎知識來自哪裡?你會變得不那麼淺薄,思想更開放,視野更開闊,會更加感激你是誰——我是一個人(human being),我是他們的一部分。因此,我勸說人們放棄對任何理念的強烈依戀,無論是宗教還是政治。如果15年前你跟我對話,我對伊斯蘭教充滿信心,我知道它意味著甚麼,一個永恆的、無與倫比的、超過任何形式人類關係的——那就是安拉,你的主和我的主。看了十五年雜書以後,我學得更多、讀得更多、聽得更多,現在你再問我事情,我會說我不知道。這就是自由。」
曼瓦爾說,要防禦他這樣的招募者,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孩子們從童年起學會提問。他說:「神是甚麼?為甚麼神必須存在?這種問題並沒有冒犯誰,一切都應該拿到桌面上來討論,你可以去學校跟十五六歲的孩子說:『在伊斯蘭教中有一種說法,說穆斯林應該用石頭砸死通姦者,你怎麼看?』所以這無關伊斯蘭教說甚麼或學者怎麼說,你要做的就是問人們怎麼想,如果你連這都做不到,他們怎麼能知道如何與自己的良心、和人類價值觀聯繫起來……它們不是禁忌,從來沒有禁忌,也不應該是禁忌。」
本耶圖在監獄中考取了國家護士文憑,進入護理學院。當他第一次為陌生女性病人做心電圖時想過逃避,但他知道面對抉擇的人生時刻到了。他細心地幫助病人吃飯、走路、換護具,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為他人提供了幫助,舊信仰自此坍塌。他第一次感受到親近具體的個人、遠離抽象的宏大敘事,是這種感覺。他說:「過去我堅持一種意識形態、打擊腐敗、在地球上建立公正的秩序,到頭來只給人帶來死亡,而在那裡通過小事。」而在被柴靜問到是否覺得自己背叛了宗教時,他說:「沒有。我現在沒有背叛我的宗教,而當我是聖戰者的時候才是背叛了我的宗教。」
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在解釋啟蒙為何物時說,啟蒙就是「Dare to know」(敢於知道)。筆者想,用常識、理性和人道主義對抗狂熱,在求知和接觸個體認識自我以及周圍的一切,以此抵抗各式各樣的蒙昧和狹隘,是文明世界中每個個體的責任。
在紀錄片的尾聲,柴靜這樣評價受訪的三個前聖戰分子:「他們思想的真正轉變,不是找到了真理,而是不再尋找終極真理;不是找到了一個答案,而是不再需要一個單一的答案;不是找到了一個身分,而是擁有一個永遠開放、不斷更新的身分。人類的身分建立在一個故事上,恐怖主義的招募要靠講故事,而這些脫身而出的人,可以成為有力的反敘事者。」
Individual(個體)的詞根來源於「divide」(切分)。古蘭經說:「神切分人類,是為了讓他們相互認識。」而不是相互仇恨和屠殺,不盲從權威、不把狹隘的刻板解讀強加於人。如果一個個體可以學會在全景中獨立思考,關注目下的每個生活小日常,戳破宏大敘事的粉紅泡沫,避免活在別人篡改和粉飾過的過去和虛幻的未來,也許可以稱得上為人類福祉作出丁點貢獻了吧。
虛詞・無形網站
虛詞・無形Facebook
虛詞・無形YouTube
虛詞・無形Patreon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and clap, let me know that you are with me on the road of creation. Keep this enthusiasm toge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