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人的阅读史
一个人的阅读史

一个人的阅读史
一个人的阅读史
微信读书 | “你的阅读时长是3527个小时,注意保护视力噢!”
互联网教会了我们“关注”(或“追踪”)表示“喜欢”,教给我们“拉黑”与“被拉黑”的滋味,也教会了我们“下载”和“卸载”——“我为什么要把微博给卸了,因为我一打开微博就忍不住想去看她的信息。”可是心里的感情无法像手机APP一样可以被轻松卸载,也不像按下删除键一样真的能删个干净。
我们的头发连成一片排着队的云
不管生命如何累加,我们的头发仍然连在一起生长,接天莲叶无穷碧,这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云朵在排着队变白,这极其普通的一生。
占有书籍已令人羞愧,更何况将它们展示出来
我们仍在使用阅读纸质书的“老旧”方式阅读电子书,但也没有因为纸张的消失而增加多一条抵达的路径。
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 | 《呼兰河传》笔记(一)
扎彩匠到了阴间再开扎彩铺是不是又要租人家的房子,卖豆芽菜的女子要怎么活下去,大昴星升起时昨日清晨开过的牵牛花要落去了。

为鬼而做的盛举 | 《呼兰河传》笔记(二)
在“请神”的世界观里,女人的地位这样高,恐怕是因为她的肉身已有一半脱离了凡胎,真的成了“仙”。
梅葛 | 史诗传说里无缘无故的神
天神找人种,山山箐箐跑,遇着小松树:“小松树,小松树!你是好树子,你若有好心,请你告诉我,你看见人种没有?”“人种我没见,要是遇着了,我的叶子硬,戳也戳死他。”
源氏物语 | 爱路常险阻,旧客亦痴缠
为了恋情,源氏公子一生一世不得安宁。

后弦:我又从西厢过,十二年前的白日梦
我后来才知道,《昆明湖》是后弦游北京颐和园中昆明湖冬景后做的一场梦,歌里的昆明湖既不是当时颐和园中的昆明湖,也不是今天昆明的滇池,而是一个只存在他梦里的故事。

我的围炉:生于火塘边
篝火是未被驯服的火,是暂时借来的,很快就要还于天地。而火塘的火,是睡在堂屋中央的卡尔西法,人醒来它也醒,人睡去它也睡。
胡续冬:是雾霾中成群的阿童木再度起飞,去一张字条里找你
我们的诗在闪电上金兰结义,而我们的人却就此散落人间,不通音息。
年轻时幻想与文字结伴
妈妈,我更新一下我的梦想:成为诗人。

金粉世家 | 这月亮太好了,不可辜负它
你放心,我决不能让你有什么为难之处,灯在这里,我要是有始无终,打不破贫富阶级,将来我遇着水,水里死,遇着火,火里……

成年女性的阅读时间
这很卑鄙,但我终于知道了,那些存在于我想象中的女人,她们究竟如何生活。

当女性谈论性感时在谈什么
怎样才能跨越衣服、妆容和社会对美的普通观念,到达身体?

让更多的女人上山喝茶
我说了这么多的误会,也多得你一路听下来。

九十年代的“小女人散文”与女性主义
有人称90年代的文学是都市的文学,90年代的都市是女人的都市。

节日快乐,社会主义的女儿们
不管人们如何愤怒,如何有意识,女性确实陷入了一种空前的绝境。所有讨论都像是女人被锁住之后的声声哀鸣,我们也一样被囚禁了很久。“节日快乐,社会主义的女儿们”,这像是一种持续的诅咒。

云南人上街去买草
清代到云贵来做官的吴其濬写道:“余留滞江湖,久不见蔓菁风味。”

从 It’s my duty 到“最后一代”
从过去那种永恒的一去不复返的青年状态,退回到三五岁的孩童时期,不惜以自刎的方式来惩罚“令他伤心的大人”。几千年来如此,几千年来都是哪吒自刎。

边疆、民族与宗教:我小时候的宗教经验
我的回族同学,那个百口莫辩的穿青人,还有我自己的民族身份,统统被隐去了,只剩下一个“云南人”,进而笼罩在“中国人”这个更大的身份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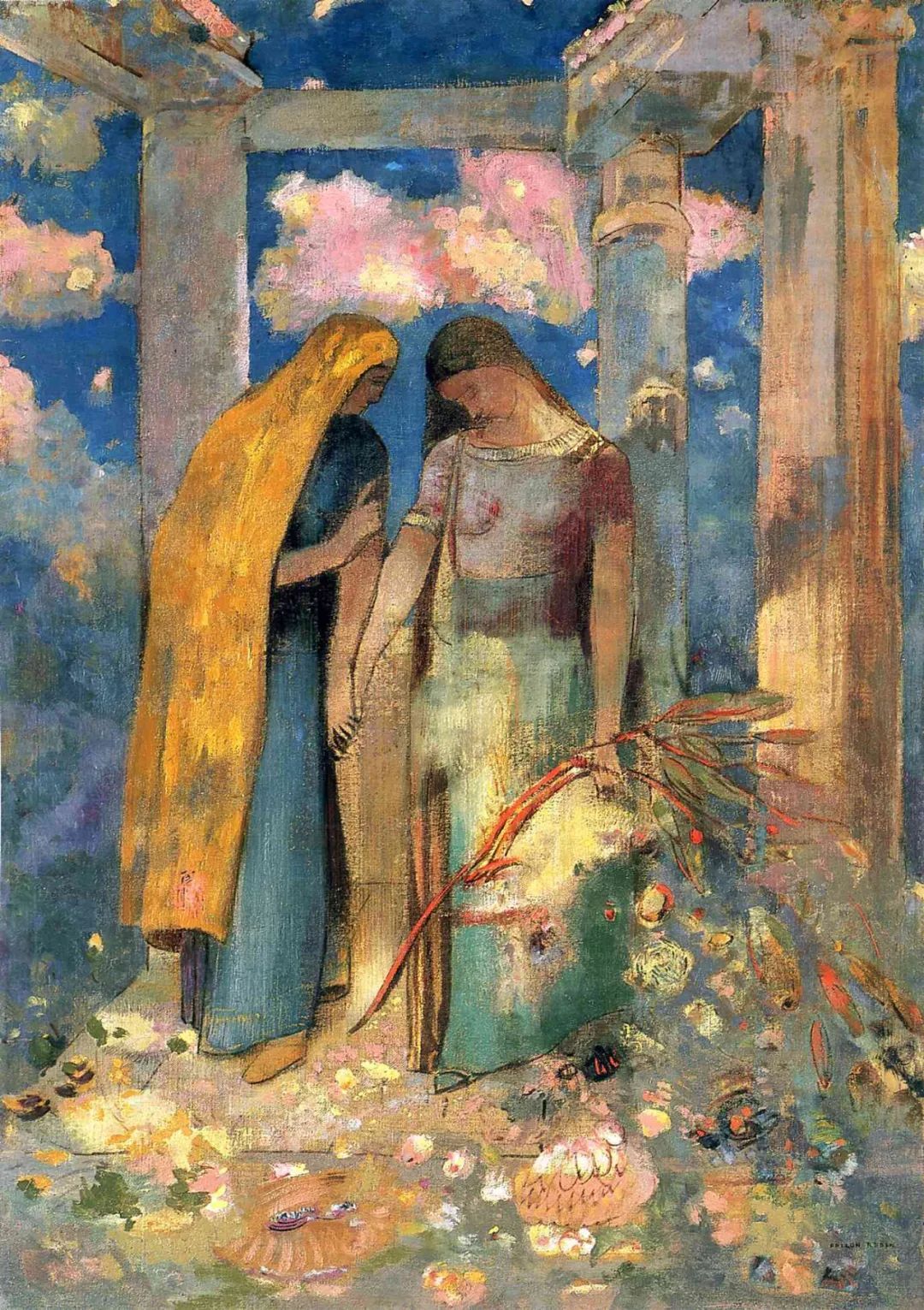
边疆、民族与宗教:感谢上帝冒雨到教堂
他问我从哪里来,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但我想他日常也是这样问的,主要还是针对基督徒,或许对方会回答他,自己是来自哪里的教会。但我没有这样的答案。

总有一天我要生活在现实世界里吗
“爱丽丝,总有一天我要生活在现实世界里了吗?”听起来就好像是在对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兔子洞发问。

边疆、民族与宗教:汉文化的纯粹飞地
到了十八世纪末,汉人已经占据了云南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二,从此奠定了云南的人口格局。云南人的前提便是中国人,不言而喻的含义便是中国的云南人。

边疆、民族与宗教:“婚姻诈骗案”中的缅甸新娘
罪犯竟摇身一变,成为现代社会里和平的“买主”,而女人变成了可以被占有和“消费”的物品。

边疆、民族与宗教:国歌不会唱,就不是中国人了
此后,约翰就在贡山、丽江、昆明三地的监狱中度过了31年。据约翰说,当时贡山监狱关押的人员有六七百人之多,后来人太多关不下,把他们转到丽江,10个人的手臂捆着排成一排,经维西到达丽江。

我不愿做祖国的儿童
每一个词条都费尽心机,千言万语只化作一句,买它,并将它当作送给自己的礼物。偷着乐吧,我的孩子们。

词汇总是让学者们感到尴尬
当他们一本正经想要寻根溯源,这些词汇背后总会有一个玩世不恭的人已经做好了准备,要狠狠戏弄他们一番。

在通往道德的途中
理性不止一次地遭到可怕的失败,野蛮从而获取最大的胜利。

假如自杀是美丽的
那时世界也每天发生数以万计的新闻,各种各样的人相继离世,有人不幸遇害,也有人在夏天自杀。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他又翻到一首秋天的诗,关于山色湖光,关于记忆中那个滔滔不绝背诵古诗的孩子。

走不出旧时代的人:大长今与韩国文学
没有新的政治想象和思想就不可能有新的文学。

我讨厌女性写作仅被视为私人生活谈论而非性别政治
将个人遭遇的性别经验,上升为性别(制度)而非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就是一种真正的“政治”行为。美国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在她那本著名的《性的政治》中,将“政治”界定为“人类某一集团用来支配另一集团的那些具有权力结构的关系和组合”,并且认为两性之间延续的,正是“一个集团按天生的权力统治另一集团的一种古老而普遍的格局”。

爱裹身之人的生存窘境
如果爱在你面前现身,不管那是什么样的爱,你还是会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吧。它就是那样的东西,不听任何劝阻,像一个白痴。

寧想白《印記》:反刍生命
那意念太过强大,一经沾染就会主动附身,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读者也心甘情愿。

被献祭的秀禾与房思琪
我们不断地挣扎,徒劳地想摆脱落入同样的墓穴的命运,却恰恰忘了追问,是谁挖掘了这些陷阱。

文学可以是怪物吗
一个共享的幻觉,在这幻觉中潜入广袤的海洋,人幻想自己是一个温柔的泡沫,是一体的一部分。畸零之心落地终成家园,庇荫成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