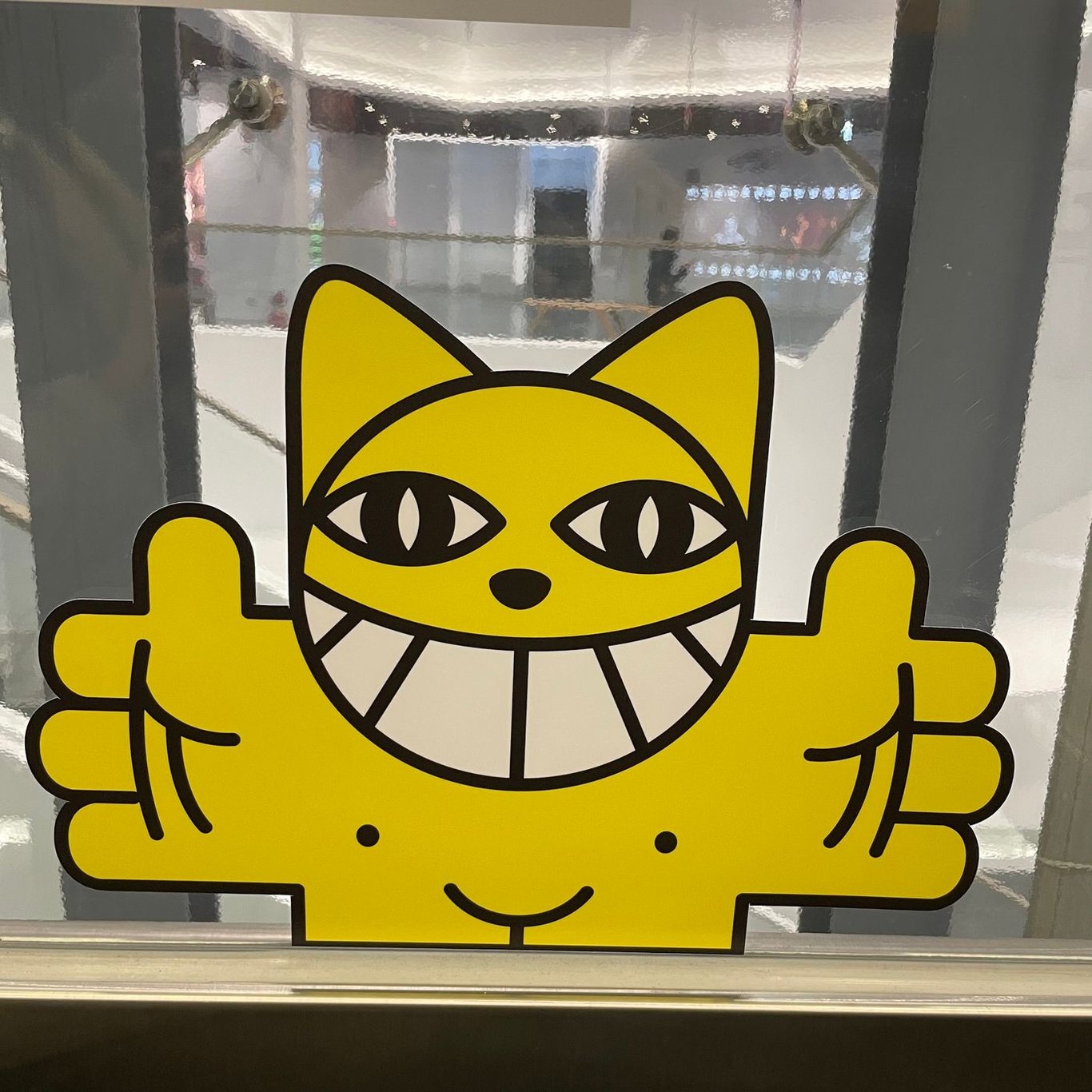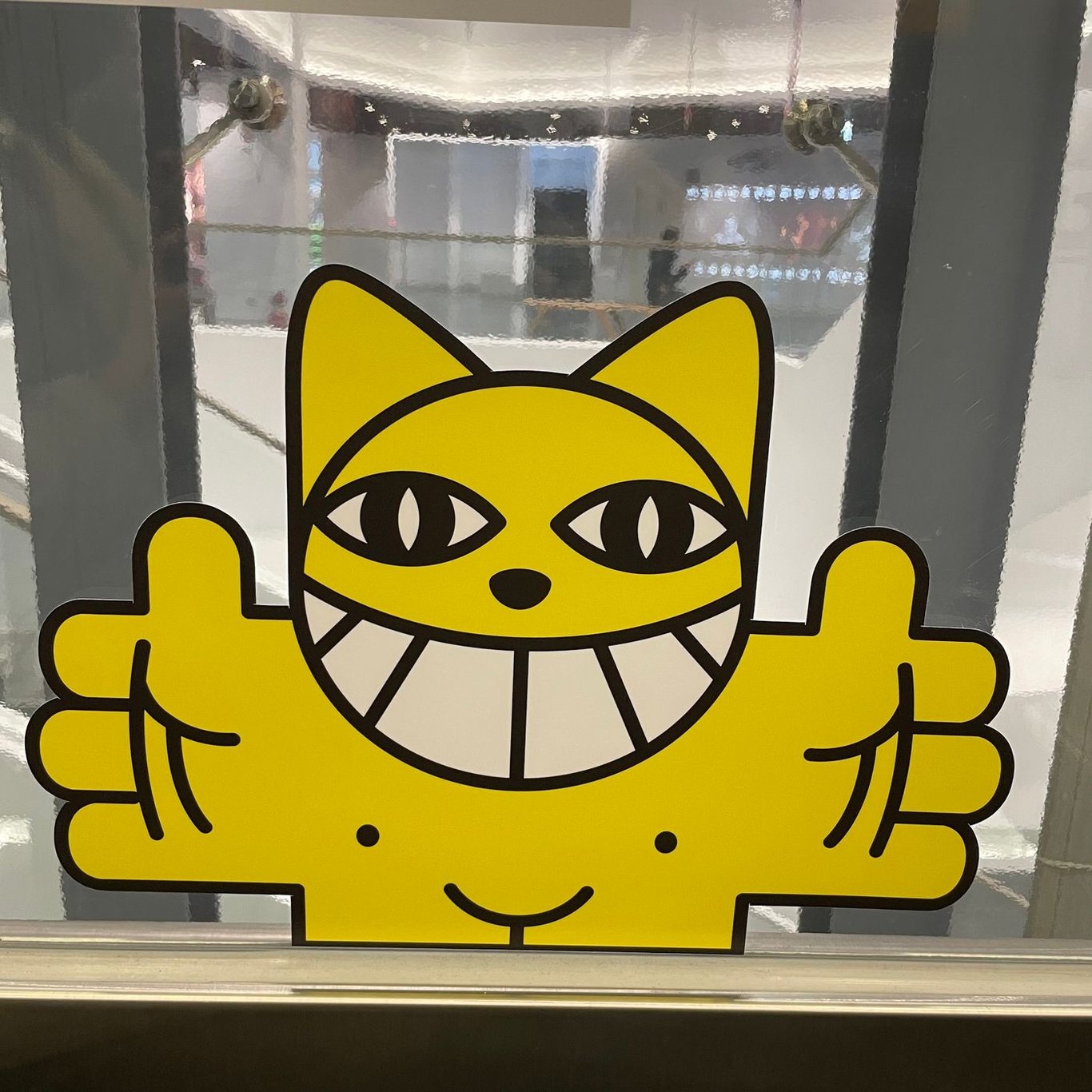七日書vol.4 |上海灘
想了又想,沒有這樣一首典型的歌謠躍然紙上。粵語、閩南語、寧波話、侗語、蒙古語……我都能想到對應的歌,常德語卻沒有,這讓我有點失落,彷彿確證了我不完全屬於常德。但由這個題目,我想到了另外的東西。
兒時的印像裡,常德是個「玩樂屬性」蠻重、過小日子的地方。麻將館、跑鬍子(一種字牌)、歌舞廳、錄影廳星羅棋布,很適合「合家歡」。我就有和外公外婆小姨去看戲聽歌的記憶,去的地方叫「熱帶雨林」,聽的歌似乎是山歌,或是對歌。劉三姐是家喻戶曉的形象。那樣的女性聲音悠揚、廣遼,能破開歌廳的穹頂與山野相望。
小姨談戀愛也去「熱帶雨林」,我記得裡面用垂吊的藤製鞦韆當座位,我和小姨坐在一邊,她的對象坐另一邊,那時放的就是時興的流行樂了。 《走過咖啡屋》、《上海灘》、《情人的眼淚》,我跟著音樂晃我的小短腿,還品味不出歌曲之外貫通年歲的集體情感。
不知道上世紀的湖南青年,是不是都有著豐美的,唱歌跳舞的記憶,是不是某種音樂性,或者對舊時情懷的感念,也纏繞著他們往後現實人生的另一面,留下一絲隱晦的卻是逝去的古浪漫。如同外婆的青春,充滿了唱歌跳舞的印記;我媽和小姨在興盛的流行樂、交誼舞文化裡舒展初生的少女青澀(據說我媽的初戀就是彼時跳舞跳得最好的男孩) ;我爸彈吉他,嗓音現今也屬在ktv能一展風采的。
時代總是那個共同的背景,文化藝術各領域都在噴湧著蓬勃的創造力,個體攜帶了這樣環境流淌下來的情感共鳴。在常德聽《上海灘》與在上海聽《上海灘》不同的只是個體在那個當下具體發生著什麼、和誰在一起。人生命的獨特性不就是一個個當下組成的?小姨離開湖南,來到廣州後,還時常放起《上海灘》,和另一些同年代的、我知道對她意義深切的歌。她通常是躺在床上,那張和外婆分享著,他們母女各佔一半的床,自己默默聽著。
但有些東西,其實不必逝去、也本來可以不逝去。
在常德聽到的歌,有過的經歷,放在一生的長度來說,也許堪堪僅稱得上是“人生的切片”,過度沉湎還會被說成是“軟弱的懷舊”、“不活在當下」。但我們忽略了,有些切片,是最根本的切片,沒有他們,人就散了,匯不成面、匯不成體。品格、心性、寶貴的情誼、生命的熱情……若這個當下的我已不是我,我又如何活在當下?常德其實是我家中最根本的支持性土壤,而非在奔向大城市後去刻意疏離的「鄉下」。回到個體的生命體驗裡,在常德聽《上海灘》才是那個味兒。
對於小姨,其實還有更多想說,但語言是被感傷淤堵住了。我看到的小姨,已是折了翼的天使,正因為深知自己曾如何閃耀過,才無法乾脆的推開過去。在已沒有力量補起斷翅(甚至不奢望重新飛翔)的現狀裡,我僅能用一張收錄了小姨所有喜愛之歌的光盤告訴她,我也還記得,我也很喜歡,不是過去意義的喜歡,是現在也喜歡。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