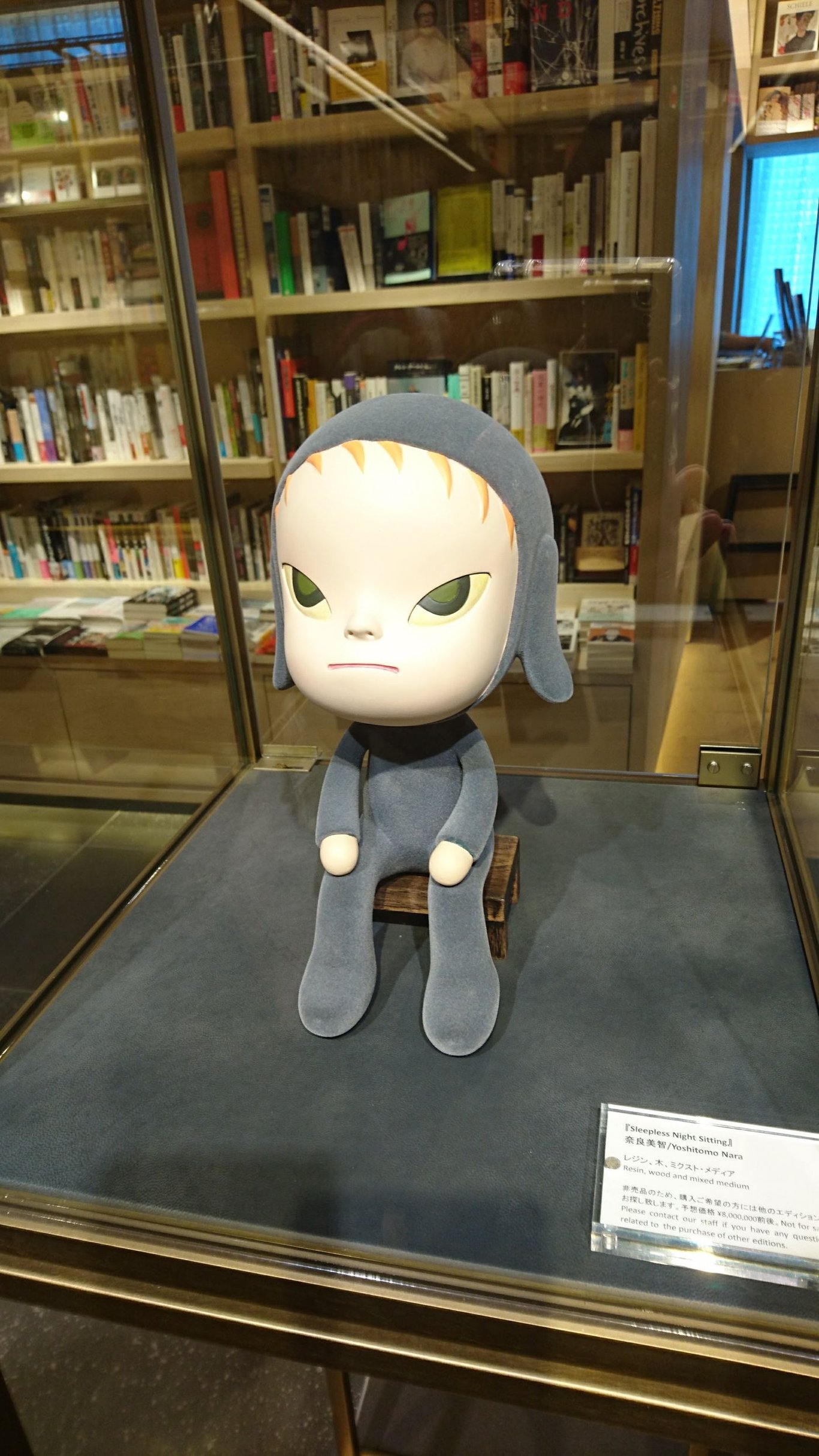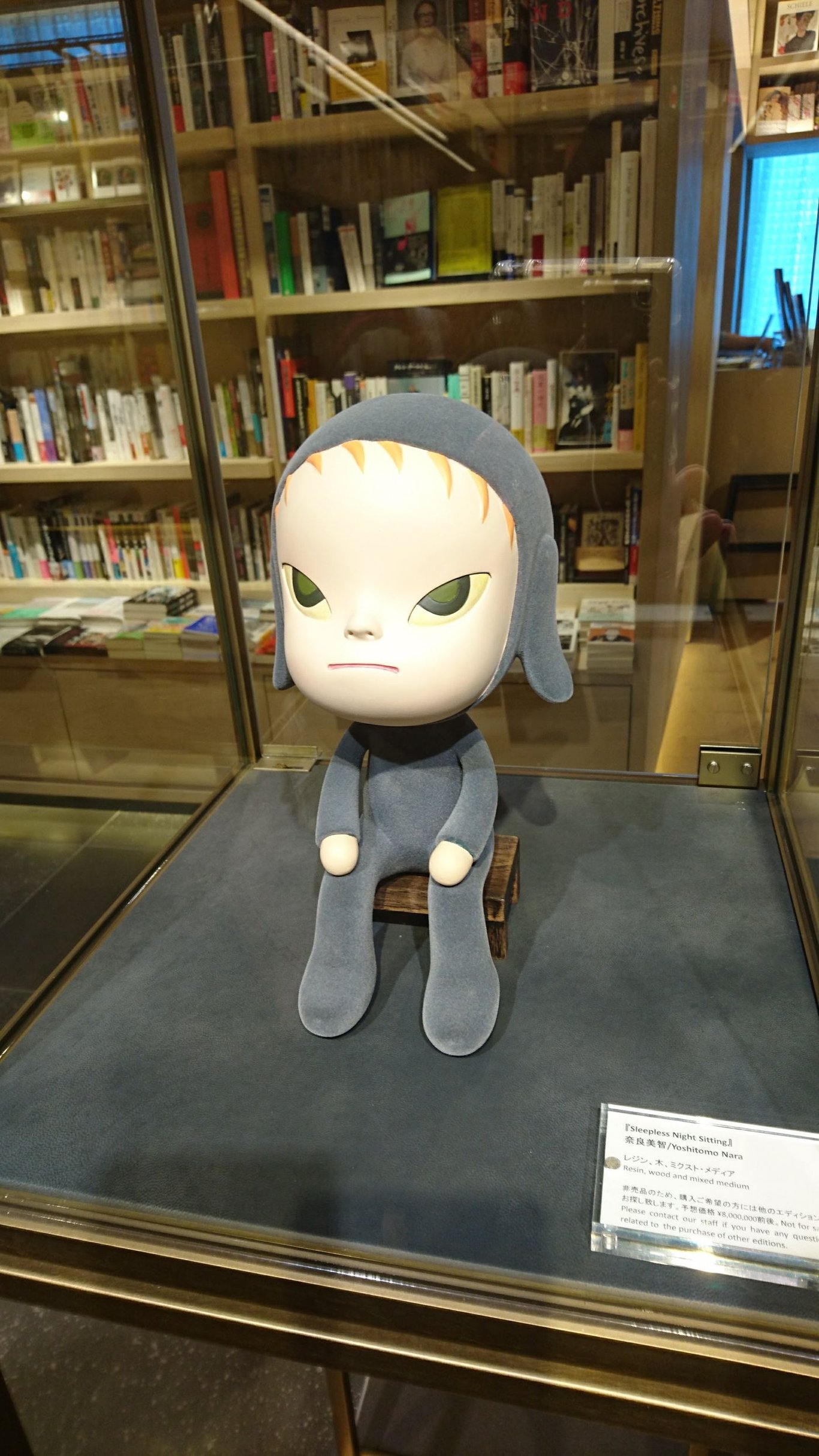外婆,阿嬷
今年三月初,清明节,我和妈妈在河南乡村呆了好几天。距离,我上一次,来到这里,是2020年12月。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呆这么久。
一天下午,我问妈妈,如何看待自己被遗弃的经历。妈妈,是过继给外婆的。她的生父母,是外婆的亲姐姐。外婆家,妈妈是老大,还有她的妹妹,她的弟弟。 (我的小姨,我的舅舅)。在生父母这边,我妈妈排行老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那几天,我们就住在,她的大姐家。
对于这个问题,妈妈并不想多做回答。
外婆也去世了好几年。
(至于,她亲生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我不了解,也从没有问过。)

2019年,农历春节假期过后,我乘动车来到上海,开始一年新的工作。没过几天,我在办公室里,收到了妈妈的微信:「你姥姥走了!18号出殡」
这消息多少让我举棋不定,如果要去参加葬礼的话,得坐十几个小时火车回漯河,还得向老板请假。去漯河,最方便的方法是经由我家武汉中转。但我刚从武汉离开,又回一趟显得多余。我妈妈微信告诉我,「你就不过来了」、「远」、「麻烦」,尽管在她告诉我外婆去世前,她问我:「这几天休息吗?」
我已经四年多没有见过外婆,她在北方的村子里,死前几年还去外面小城市打过临工。在国庆要回家的时候,我妈妈问我,「想不想看下你姥姥」。那次微信对话中,我才得知外婆得了痴呆症,半身不遂家里躺了半年。
我询问了具体病情,她回答:「刚开始不知道她有那么严重,在说我一直在忙,回家看她就不能走路了。去大医院也没有那么多钱,她没有医保,她不让我带她去。」 「在家小医院看了,也用不了多少钱。」 「早就大小便失禁」 「看能不能熬到过年」「我没办法照顾她」 「现在只有多给她买点她喜欢吃的!我只能做到这点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只是回复:「你不要太难过,很多事情也都是命运。」
在这些对话前,我妈妈第二次问我,「问你想不想看下她」。我说,「可以啊。」 这不是真的想法,过了几分钟后,「我其实还好」 「因为感觉我无法做什么」 照片中,我的外婆睡在没有席梦思的床上,盖着带鲜花的绿颜色被子,她微张着嘴,满是皱纹,农村老人的黑皮肤。这个砖瓦房很简陋,到了冬天很冷,因为没有暖气。
最后,我告诉妈妈,上班地方离上海华山医院很近,可以问问这样的病该吃什么药。她告诉我这些没有用的。我什至在支付宝上,找到了对应科室预约了一名教授医生。后来几天,我一直没有去,最终也没有去。
1.
妈妈问我想不想要去看外婆,可能是想给我一个机会,怕我留下遗憾。现在想来,我确实觉得这是一个遗憾,是生命中留有缝隙的遗憾,一种委屈,一种自我。
我觉得我的外婆很可怜,她只参与她后代(也就是我)生命中很小的一段。在我少年前,记事起,我只回过一次河南。那是个夏天,阳光明媚,暴雨过后,会有成排的蜻蜓经过院子,轻轻用手就能捉到一只,其中一个舅舅还是追鸟能手,他向我展示抓到的野鸟,鸡能扑哧地飞到树上,一口井很深。我趴着往里看,心里凝注,生怕被困进了里面。大人们,在一旁说,有个女人就淹死在了井里(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人,就是我亲舅舅的妻子,最后舅舅疯了,后来一直折磨我的外婆)。那个时候我五岁多,但上面说的我都记得,不是现在追忆或想象而来。
但我不太记得外婆,除了我从家里出门在院子外面玩,总是弄丢了火腿肠。发现时,又重新回屋子里,找大人要。村民们都在笑话我。现在想来,不厌其烦给我火腿肠的人,是我的外婆。她可能是一个吝啬的人,但她没有太在意。不过外婆不知道的是,我当时根本不可能会吃便宜的双汇火腿肠,「喂狗吃的」,武汉的街坊都这么认为。
那趟去河南,除了我和妈妈,还有我的父亲,奶奶,和奶奶从小养到大的堂姐。从微妙的变化中,我感觉奶奶对这里和外婆不太满意,这也是她第一次到河南,她觉得招待的食物太差了,外婆看起来不太卫生,没有文化,「你姥姥很抠」,我长大后奶奶有次谈到那次旅行。
那次旅行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外婆,一直到上初中。第一次,我妈妈带我去河南过春节。我很诧异,为什么几乎没有联系过的外婆,她看起来非常疼爱我。顺便一提,我的外婆是妈妈的养母。因此到了农村,她先带我见了亲身母亲(但她只是说「见姥姥」),进了屋,我感觉久违和远方的「外公外婆」对我很冷漠,给了我好几百块钱压岁钱,就不再有任何言语。我很失望,感觉陪妈妈在外地过春节不是个好选择。
意外之外,我们坐了一会儿,妈妈就同他们告别。我很纳闷,妈妈说去见另一个「姥姥」(农村姊妹多,我以为只是另一个亲戚)。不耐烦,和她往着同一个方向走,心里想着什么时候能结束。
疯子舅舅来接了我们(让我有了些记忆,因为小时候,我对这个又高又瘦的疯子还有印象),他冲了我笑笑,穿过一条道,门前有棵小树,眼下的房子比之前的显得破旧又寒酸。怎么会这么穷,我心里想。但我得知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时,心里更觉得无法接受。
这个时候,我的外婆从灶台里跑了出来。她瘦小、皮肤干瘪,但从眼窝、面孔等样子,能看出外婆是一个专横、强硬的人。她来到我们面前,手紧紧抓着我妈妈的手,眼里布满泪花。她松开了我妈妈的手,走到我跟前,同样是满是泪花的眼睛看着我。我当时心里有些难过,或者是一种无法想出的情感,我感觉眼下的外婆和刚刚的外婆完全不一样,那一秒,我觉得我们也是亲人,便不再遗憾要住在这简陋的平瓦房。
妈妈的村庄,在过年时也很无趣。外婆家没有电视,我们去姨夫家里看春晚。外婆不爱说话,只是抽烟。她不会说普通话,也不想要河南话为难我(可能只是寡言),在她家时(她几乎从不去其他亲戚家),外婆只是呆在我旁边。我同她讲话时,她安静的听着,用眼神看着我,像是一个聋人。
她拿出了红包,递给了我。当时我觉得,可能只是意思一下(至少在妈妈的村庄,人们基本只给几十块钱当春节红包)。打开后,我很吃惊,里面是一千多块。在武汉,亲戚们就相约后,各自都有小孩就不互送红包。但姑妈常会塞我红包,奶奶也会给小辈准备红包,那一年春节,以及过往,都是一百块或两百块。我很吃惊为什么外婆给我那么多钱。
同母亲春节时回河南,从那年一直持续到我大学毕业。后来,我得知外婆给他后辈(一样是外孙)春节红包只有几十块,我的弟弟妹妹要比我小快十岁,小姨和姨夫都是一个乡的,除了大姐,另外两个孩子和他们在武汉长大。
我问了妈妈几次为什么?她给了我不同答案:「你外婆更疼你」 「因为你是城里长大」 「你很少回去」
这几乎是我和外婆仅有的交集,每年短短几天的相处。她从没有到过武汉,至少我没有在武汉见过她,她也没有拜访过我们在武汉搬了三次的家,房子越搬越大。
2.
尽管我一直在武汉生活,二十岁前,几乎没有在外地呆过一周。坦白说,我一直对这个城市缺乏认同感,这有很多原因,同小时候要非常敏感有关。
没有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无意得知,我出生时户口属于「河南漯河」,过了几年,才随着我妈妈的户口一起划进父亲的城市口。当时我觉得很奇异,没有想到我和农村沾上了关系(那时我还没去过河南),户口对我来说很新鲜,好像人的命运要被人为左右一样。
妈妈在年轻的时候,算是个比较漂亮的女人(不是普通人称「我妈妈当时很美」的那种),我父亲年轻时还算很帅,但那时他已经离过婚了,他大我妈妈大概八岁。回到我妈妈,我妈妈漂亮但平日不会打扮,人的性格」大大咧咧,不在意别人开玩笑」,但那时已不像一个农村人了。由于我父亲有些懒散,且日渐寡言,管教幼童的事情都在我妈妈身上。
她常拿着衣架追着我跑,有时我故意冲她喊:「回你河南,种玉米地去。」,她会很生气,但我不以为意。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这样说,可能是也有邻居偶尔这样开玩笑,我只是模仿。也有可能,我潜意识觉得,这样能和我妈妈划清界限,抵消户口给我造成的困恼。
有一次,我妈妈和邻居诉苦,因为我年龄太小了,她对我的在场视而不见,「我儿子说什么,要我回去种玉米,太不像话。」 这样的时刻反而让我今后的记忆更完整。当时我觉得,这样做可能不多,我妈妈在这里毕竟也是外乡人。
这种身份造成的隔阂,其实本来可能完全不会存在,它很巧合地出现了,不仅是我幼年时敏感,最终是因为我的一段楼房生活。更多是因为奶奶,我感觉她一直对我妈妈很苛刻,她有三个儿子,我也偶尔感觉她对我父亲更忽视,但最终因为他是长子,选择住在了一起。她对另一个媳妇,表现得更尊敬,对我妈妈则很尖酸冷淡,甚至在两个媳妇,包括我同时在场时,她也不掩饰这一点。
我很好奇哪里出了问题。
3.
在我们家没有彻底和奶奶家住在一起前。我一个人,离开了父母,搬去和爷爷奶奶住。那是一个七十年代建起的楼房,还算宽敞的二居室。
有一天,我的嬢嬢(武汉话,意指叔叔的老婆,姑且用阿姨指代吧)的母亲,要来奶奶家拜访。即使在武汉,两个亲家走动地并不多。阿姨是一个脾气暴躁,爱打小算盘,指责讽刺别人。不过随着年龄增长,现在的脾气要好很多了。
在武汉,我们管外婆叫家家(姑且就说“家家”吧)。这个家家是上海人,她可能是下乡,或者因为婚姻的缘故来到武汉。她戴着眼镜,头发很洋气,只见过几次面,但感觉她挺和蔼。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小学生,在楼房生活非常无聊,所以我很喜欢有人做客。
小时候,我很礼貌,尤其对待大人,我和这个客人讲了好几次话,就要称呼「家家」、「家家」。阿姨在一旁,她突然笑笑,开玩笑的说,「你看黑黑叫的几亲热额,家家家家的,因为他没有家家。」
听完,我非常生气,想要阿姨道歉,「我怎么没有家家,难道我家家死了吗?」 阿姨无视我,「你本来就没有家家。」 ,只有她母亲试着安抚我,平息这个争吵。这时奶奶过来,我慌忙说了原委,没有想到的是,奶奶叫骂我,把我赶出了房间。阿姨用武汉话对奶奶讲,「我说的是,他们那一块又不喊家家。」
客人走后,我再提起此事时,奶奶也没称阿姨做的不对,只是怪我很不礼貌。这让我多少对事情的看法持有一些失望。从我童年开始和奶奶一起生活后,一直到奶奶在我十八岁去世。奶奶对我并不算很友好,妈妈带我出去玩,回到家里时,奶奶的脸总是阴沉的,有时会当面斥责干嘛回来这么晚。我的堂姐,是奶奶从小养到大,她对堂姐很宠爱,因为她父母离婚,叔叔是个吸毒的人,常找奶奶要钱。我不妒忌这种爱,但堂姐小时候性格跋扈,加上奶奶在家庭里独断、严厉,父亲几乎常年出差,这种以上微妙带来的关系偶尔就迁怒我和妈妈。
细节不需展开,无关隐私,只是影响了叙述。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常常会怀疑武汉的亲戚会不会太坏了,同时我同母亲的亲戚也无接触。在初三时,外公和疯子舅舅来了武汉,试图帮父亲在城郊开的小工厂打工,赚点钱,妈妈也在那帮忙,几乎不回家里。那个时候我稍微独立了些,碰到周末,就会去城郊找父母。
我也碰到了外公,他很矮,不同于我外婆的好斗顽强(她逼死了媳妇,最终跳井),外公看起来老实巴交的,是个没什么办法的人。很快,他们离开了武汉,因为舅舅发疯时那妈妈为难,妈妈打发他们走了。 (记得小学时,陪妈妈去电话亭,妈妈很伤心,她说舅舅把老家的房子一把火烧了。)
很久后,我奶奶得知,我的外公来了武汉,她怪我妈妈没有把外公请到家里做客。很大纬度看,奶奶是一个宽宏大量、有决断力、对他人很好的人,但这个尺度取决于她对事情的评判。我也很想知道,我妈妈为什么从不请外公外婆来过武汉的家。
我感受到奶奶的善意很晚才出现。十七岁时,在外面参加补习班,发现有几个同学拥有iPod touch3,他们递给我,但我不会玩这个新奇的电子产品。回家时,我在饭桌上称自己也很想要,说不定能学英语。我怕拒绝,称iPod shuffle也可以听东西。奶奶说,MP3好像早就过时了,你去买你说的小电脑吧,她给了我快2000块钱买touch第四代。这是她第一次特别为我买东西。奶奶毕竟听过叔叔很多谎话,她肯定知道我不是为了学英语,或者对我能好好学习抱有侥幸,但更有可能的是,她觉得我确实很想要,而我看到有人拥有了,奶奶不喜欢后辈在外面受委屈。
这些让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从来我都奶奶的总体感觉不是讨厌,或有恨意的,很多愉快的时光我们一起度过了,但同时她的冷淡与对妈妈的排挤,让我将这两种感知综合了,这让我对奶奶留给我的「纪念空间」越来越空和小,现在来看我奶奶,我的情感变得平庸又单薄。
我很少和外婆接触,我都没在书面文字中称她为姥姥。外婆给了我很多留白,也有一些遗憾,从某个程度,外婆(不是指涉个人的加粗汉字)可能是我与世界进行共处间的一个秘密。某个时刻,我想到外婆时,我越来越怀念她。我觉得她也代表了我记事时所开始带来的很难说明的委屈,这个委屈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不可见,但一直存在。
但我的外婆已经死了。我很唏嘘她坎坷的一生,尽管我不知道前因后果,以及丰富的细节。我的外婆在河南漯河一个村庄的坟头,现在可能长满了荒草。我不知道我的疯人舅舅会不会偶尔去那发呆。
END
此作品获Nomad Matters 游牧者计划支持。近期,将更新外公、与妈妈返乡等。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