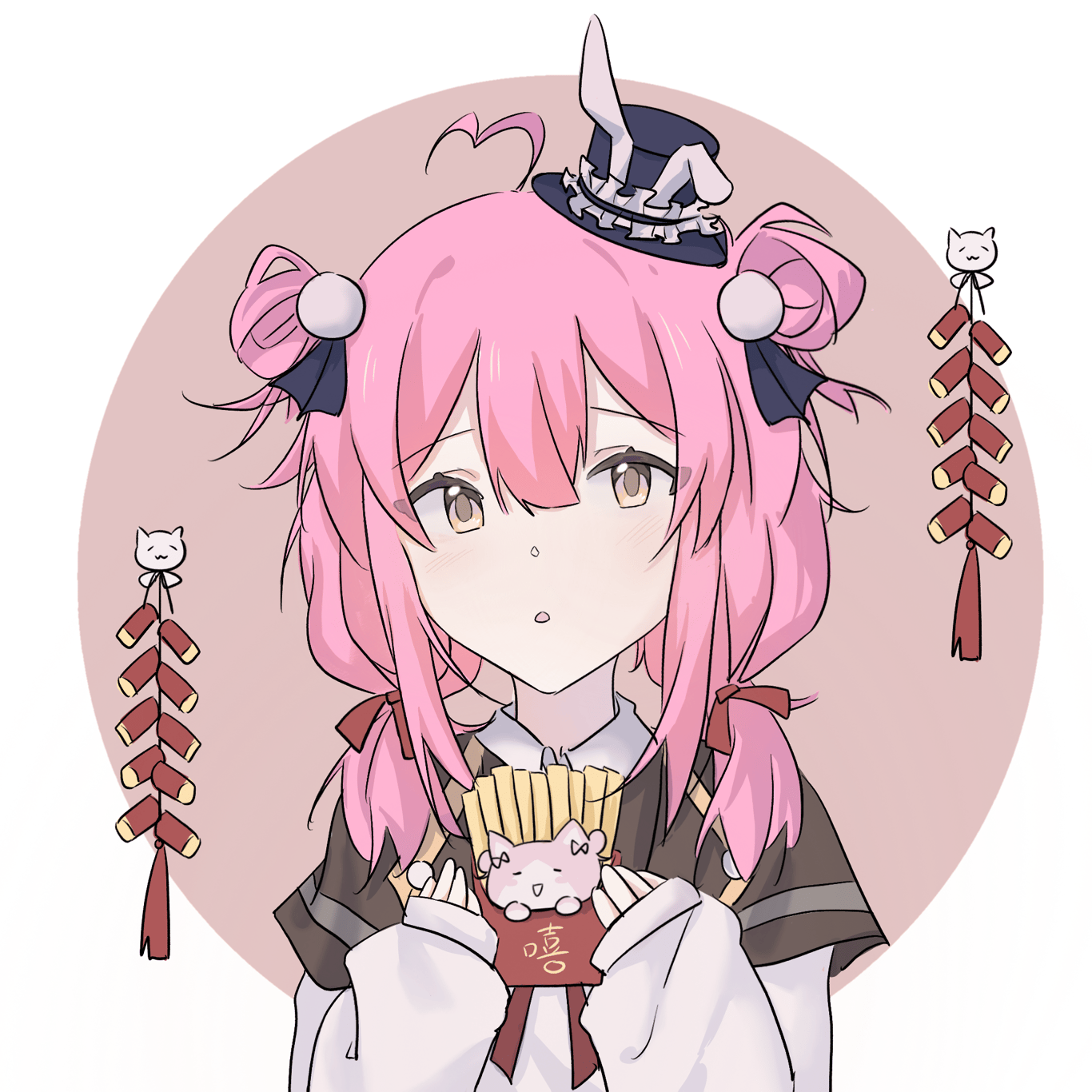巴勒斯坦的赤裸生命
作者:Jordan Street
媒體: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發佈時間:2013年5月4日
譯者:Spadetaffy
原文url: https://www.e-ir.info/2013/05/04/bare-life-in-palestine/
奧蘭普·德·古熱(Olympes de Gouges),一位在法國大革命中被判死刑的革命女權主義者,在臨死前哀悼說:「如果婦女可以走上斷頭台,她們應同樣有權利參加議會。」(朗西埃,2004年,299頁)。法律統治了她,但她無權支配法律。而巴勒斯坦人民,尤其是飽受壓迫的加薩走廊(Gaza Strip)和其他被佔領區的巴勒斯坦人,也遭遇類似的狀況。他們對統治他們的法律沒有發言權,同時還要受到外來軍事統治的壓迫,並且同樣「可以走上斷頭台」。本文會試著將喬吉歐‧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哲學應用到巴勒斯坦上,並試圖檢驗巴勒斯坦人是否符合阿甘本的「赤裸生命」(Bare Life)定義。我們可以看到:以色列政府的政策創造了一種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在其中,巴勒斯坦人的生命陷入了外部主權(Sovereign)的決斷中。但另一方面,巴勒斯坦的抵抗運動使得阿甘本的理論在此無法完全應用。因此,本文也參考了弗朗茨·法農(Franz Fanon)和喬治·奇卡里奧羅·馬厄(George Ciccarello Maher)來進行全面的理論分析。我認為:例外狀態理論和抵抗運動是相容的,後者在被佔領土上以「象徵性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形式運作。然而,這種象徵性暴力實際上幫助了主權建構一個更純粹的「例外狀態」。
本文將從宏觀和微觀的角度,根據歷史上和當代的資料來支持以上的論點。我們將提及諸如2008-2012年的加薩戰爭,以及黎巴嫩南部的拘留營,作為血腥壓迫的證據。我們將考察巴以關係,以及每日可見的在佔領區的壓迫和虐待。為了敘事方便,本文會將以色列預設為一個民主國家,儘管並不完美,並且學術界的許多人質疑這一點。
巴勒斯坦、以色列、「例外狀態」和「赤裸生命」的分析
自1948年,以色列國家建立的開始,該國就採用了英國1945年對巴勒斯坦管制時期的「緊急條例」(Pappe, 2008年,148頁)。自此,以色列開始採用多種方式來限制巴勒斯坦人獲取諸如水源,土地,工作,資源,家園……並彈壓所有的抵抗運動。而以色列國家有數百條法律,能夠使得其政府隨時宣布巴勒斯坦人的聚居區為「軍事禁區」(Pappe, 2008年,148頁)。以色列自建國以來,佔領了巴勒斯坦歷史領土的77%,包括加薩走廊和約旦河西岸(West Bank)。這些佔領區條件惡劣,充滿壓迫。加薩走廊築滿高牆,並且有多個以色列士兵看守的檢查點,他們控制人員,貨物的流動,並且維持對當地領空,領海,人口,稅收和基礎服務的控制(Korn, 2008年,116頁)。毋庸置疑,以色列軍隊是當地巴勒斯坦人的控制者。當地的巴勒斯坦人,自從被以色列控制以來,就一直生活在近似於貧民窟(ghetto [1] )的地域。 (Korn,2008年,122頁)
最近,加薩地帶已經從這個「近似貧民窟的地域」變成了活生生的戰場。在2008年和2012年,以色列發動了數次壓倒性進攻,導致了幾百名平民的死亡。巴勒斯坦人被佔領區的法律管制著,但對其沒有任何發言權。這些巴勒斯坦人既被法律納入,也同時被排除。這樣的一種動態是喬吉歐·阿甘本研究的重點,也是我們這篇文章將要敘述的。
基於卡爾·施密特(Karl Schmitt)和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思想,阿甘本以「例外狀態」評價當代民主體制。阿甘本語境下的例外狀態,是一個由主權決斷的,無法區分政治和法律的地帶(阿甘本,2003年,10-11頁)。這並不是我們常說的無政府狀態,也不是托馬斯·霍布斯語境下的“自然狀態”,它還是處於準運行狀態的。然而,例外狀態之下,原本朦朧的權力變成了主權統治,他能隨時「棄置」(abandon)一些人,並剝奪他們的「合法」權益。儘管「例外狀態」一詞聽著只是國家緊急狀態下的權宜之策,但實際上,它已經逐漸發展為主權與生命的壓迫關係,因為主權能夠決斷例外狀態,它事實上能夠隨意擺佈那些處於,或可能處於例外空間的人們的生死。 (Mills,2008年,59-62頁)
例外狀態下的生命被縮減到了生命的原初形式:阿甘本稱之為「赤裸生命」(阿甘本,1998年,11-13頁)。赤裸生命是主權的固有結構和原初功能方式(Mills,2008年,61頁)。它本質上是壓迫者能被縮減到的最低級的生命形式,以政治化的方式被暴露於死亡之下(阿甘本,1998年,88頁)。當那些以“主權轉移”,“憲法變更”為名義的例外變成常規時,例外狀態就完成了(Pappe,2008年,152-156頁)。在無區分的例外空間內,那些法律的例外變成了唯一的準則,而裡面的生命被縮減到了赤裸生命。在這至高例外的生命既臣服於法律,又被「無意義的法律所掌管」(Mills,2008年,64頁)。生命在其中仍然是政治化的,但是是以最赤裸的形式,生命被主權“棄置”,並且後者握有對其的生殺大權(阿甘本,1998年,90頁)。透過這套理論,我們將要檢視巴勒斯坦的抵抗和鬥爭。
巴勒斯坦佔領區服從以色列國家的一切法律:不管是條例還是司法。他們被外部主權政治化,但又同時被從城邦中排除出去。這種排除性的納入,如我們之前所說,就是主權的基本行為典範。以色列對佔領區有憲法賦予的管轄權,同時將當地的所有生命的各個面向置於自己的掌控之下。雖然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和「哈馬斯」都宣稱自己代表了巴勒斯坦人民,但實際上他們都被以色列這個外部主權所限制,這個主權可以隨時懸置法律並對佔領區人民採取更嚴厲的措施。巴勒斯坦人並不生活在「無法制」的社會,而是生活在法律的反面(Korn,2008年,123頁)。更簡單地說:如果說無政府狀態代表一個掌控生命的外部主權的缺失,那麼巴勒斯坦的狀態就是無限制的國家權力的實踐(Korn,2008年,123頁)。阿甘本的理論,主要是討論現代民主國家如何透過棄置生命於例外空間來運作其壓迫機器(阿甘本,1998年,10頁)。所以說,如果我們把以色列定義為一個現代民主國家,那麼它的政策似乎是不斷地將巴勒斯坦人變成赤裸生命。如同Robert Lentin所說:
從以色列複雜的緊急條例制度,以及司法機構、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之間對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和生活在佔領下的巴勒斯坦人的作用來看,我們似乎很快就能將巴以的狀態(和赤裸生命)聯繫起來。 (Lentin 2008年,6頁)
根據國際法,加薩地帶自1967年來一直處於被佔領狀態,該地的所有人員流動,需求和服務都由以色列軍方控制。因此,對一個已經是佔領區的地方發動戰爭顯得沒有法律依據。 (Haajar and Levine 2012)因此,最近的兩次:2008年和2012年的戰爭,本質上是違反國際人道法的。這兩次,以色列政府都根據一些掉落在他們境內的飛彈(實際上沒造成傷亡)宣稱他們在自衛。這一點並不是很站得住腳,尤其是在最近,巴勒斯坦方面宣稱一次導彈襲擊是出於一個5歲巴勒斯坦小孩誤入邊境遭射殺而進行的報復(Haajar and Levine 2012)。在兩次以色列方面的軍事行動,2008年的鑄鉛行動(Operation: Cast Lead)和2012年的雲柱行動(Operation: Pillar of Defense)中,以色列軍隊殘忍地進攻平民區,並且殺害了大量的巴勒斯坦平民。這更加使得以色列的自衛言論讓人懷疑。在鑄鉛行動中,有證據證明以色列使用了白磷彈無區別地殺死了1300巴勒斯坦人。在最近,又有160餘人被以色列政權殺害,其中許多是婦女和兒童,已經達到了戰爭罪行的程度。婦女和兒童和男性被以相同的比例屠殺是一種種族滅絕的現象,是國際法所絕對禁止的。
在以上的例子中,我們都看到了阿甘本語境下的例外狀態。以色列政權採取法律手段來保證對佔領區的控制及發動軍事行動。主權則透過以色列國防軍(Israel Defense Force)的坦克,飛機,直升機,砲艇和狙擊手來顯現自己。然而,更令人憂慮的是,在國際人士,以色列人,甚至巴勒斯坦人看來,這兩場衝突都不是例外。在他們眼裡,這就是常態。也因此,如同Mark Levine和Lisa Hajaar所說,以色列將加薩走廊和約旦河西岸置於了常態化的例外狀態之下(Haajar and Levine 2012)。
這顯示了加沙,這樣一個以色列人強大到隨意頒布任何政策的地方,其情況是多麼令人絕望。他們以這樣的方式掌控巴勒斯坦人的生死:他們可以殺死巴勒斯坦人而「不犯殺人罪」(阿甘本,1998年,83頁)。他們被捕獲至一個自然界和人類共同體的邊界,或如阿甘本所說的「無區分地帶」(zone of indiscernibility)(阿甘本,1998年,4頁)。諸如鑄鉛行動和雲柱行動一類的軍事行動,將巴勒斯坦人的生命縮減為純粹的赤裸生命,他們被棄置,生死被掌握在以色列人手中。
這個論題的另一個縮影就是位於黎巴嫩南部由以色列國防軍掌控的安薩爾拘留營(Al-Ansar Detention Camp)。在1982年至1985年,以色列軍隊在此關押了15,000人左右,其中許多人沒有或僅犯小罪。囚犯們的食物來源、醫療照顧和必需品都極為有限,他們常被毆打,被折磨,囚室裡屎尿橫行,有些甚至堆到了膝蓋的高度(Khalili,2008年,101-102頁)。這種在國外建立虐待型設施的行為是由憲法修正案中的一項緊急狀態措施條例所保障的。如同Laleh Khalili所說,以色列「創造了一種特殊的法律和政治機構『戰俘營』來剝奪囚犯們的合法權益,甚至擴展到了治外法權來擴展主權的權力。」(Khalili,2008年,114頁) 。她進一步提到,當局有權懸置任何法律或條例,並且能夠隨意地使用任何法律。 (Khalili,2008年,106頁)
本質上,這個拘留營就是例外狀態最純粹的形式,可怕的暴行透過主權對法律的修改而時時上演。以色列將「潛在的暴力和衝突推到了普通懲罰體系之外,將暴力的軍隊放到一個安全區,讓他們放開拳腳」(Khalili,2008年,112頁)。安薩爾拘留營的囚犯們近乎陷入「昏迷狀態」了,他們對施加於自己的壓倒性暴力無能為力。主權透過修改法律掌握了這些囚犯的生殺大權。在這種情況下,任何抵抗都是無用功,都會被以最殘酷的方式鎮壓。
Catherine Mills指出,這種反抗—鎮壓的動態是將最純粹的赤裸生命形式與其他類似的案例區分開來的。她說,在這樣的過程中,「值得質疑的暴力(Aporetic Violence)…阻礙了在框架內反對生命政治政權的任何嘗試」(Mills,2008年,75頁),這在安薩爾拘留營中得到了體現。然而,正如我們在先前對加薩攻勢的案例研究中所看到的那樣,巴勒斯坦是有一些抵抗的方法的(無論它們是否可行)。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如果我們要將阿甘本的分析成功地應用在巴勒斯坦鬥爭中,是否還缺少一些東西?
象徵性暴力:透過顯現來抵抗
第一部分所展現的兩個案例體現了主權是如何在例外狀態中對赤裸生命進行掌控的。它們再現了赤裸生命最純粹的形式,一個由某種“機制”,而非“預設”所創造的生命[2] (阿甘本,2005年,88頁)。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除了這兩個案例之外的巴勒斯坦人就沒有生活在例外狀態之下,這是一個由類似案例創造的純粹的存在。除了這些案例,基於對司法懸置的佔領和壓迫仍然存在。在檢查站進行殺戮,貧窮造成的死亡,以及集中營裡的折磨依然是屢見不鮮。然而,不可否認,巴勒斯坦人展示了一種和例外狀態不完全一致的生存狀態。
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邁克爾·哈特(Micheal Hardt)表示阿甘本預設生命基本上總是和主權處於被動關係(哈特和奈格里,2000年)。在巴勒斯坦,很顯然,被動臣服並非是佔領區人民反抗壓迫的唯一手段,這說明阿甘本的分析可能有一點問題。但Lentin基於自己對阿甘本的解讀對此提出質疑,認為例外狀態確實包含了潛在的抵抗。 (Lentin,2008年,11頁)。與之類似,Catherine Mills也認為抵抗存在於例外狀態之中,她認為在阿甘本那裡,抵抗並不是憑空出現的,並且可能會起到反效果。然而,不論是在Mills的解讀,還是在阿甘本的原著中,都沒有提到抵抗運動的起因和效果。
在巴勒斯坦,我們看到各種各樣的抵抗,其目的自然是為了反對以色列創造的壓迫系統和例外狀態。但人們其實沒有充分認識到抵抗的目的是什麼,抵抗的過程是什麼,抵抗的最終效果是什麼。在劉易斯·戈登(Lewis Gordon)對弗朗茨·法農的解讀中,法農描述了一個進程:被壓迫者(原文是黑人,此處為敘事方便說成巴勒斯坦人)被放置到非存在的地獄,一個似乎顯現(appearance),似乎不顯現(disappearance)的場所。這與阿甘本的思想不謀而合,此處的顯現和不顯現和排除和納入是一樣的。戈登認為,在這個過程中,唯一可接受的存在就是非存在,就是非顯現(disappearance),就是臣服。我們又看到了那不能掌握自己生命的赤裸生命。然而,正如我們所說,巴勒斯坦確實是有抵抗的。就這一點,法農的《黑皮膚,白面具》進行了解釋。
他認為,在長期的佔領和壓迫下,抵抗不僅是常見的,而且是被期待的,預期的。法農的分析認為被壓迫者終究會到達無法忍受被壓迫的境地,並且將殖民者驅逐出家園的願望(法農,1967年)。這種心理變化的過程是值得分析的。為了擺脫壓迫,擺脫赤裸生命的境地,被壓迫者會做出他之前所做的相反的事,就是去顯現(appear)。顯現就是為了抵抗,不去顯現,抵抗就不會有希望。然而,這種顯現可能會有相反的效果。對此,戈登寫道:
如果想改變現狀,就要去顯現,但是顯現必須要透過暴力,因為顯現對被壓迫群體是非法的。這裡,暴力毋須是身體上的強制,毋須是火槍的破壞,它只須是顯現。 (戈登,2007年,12頁)
即便以抵抗為形式的顯現僅僅名義上是暴力的,它其實已經失去了其本體論上的功能。
巴勒斯坦人希望擺脫壓迫和不義,他們希望擺脫「棄置」。為此,他們挑戰那「把存在和非存在分隔開的排除之牆,這樣的破壞使得顯現表現為純粹的暴力。」(奇卡里奧羅-馬厄,2010年)。法農認為以暴力顯現的抵抗,例如飛彈和自殺式攻擊,是「無論從表像或內在,都不可與壓迫者的暴力同日而語的。」(奇卡里奧羅-馬厄,2010年) 。此時,顯現的本體論功能變得無效了。此外,那些飛彈和自殺式攻擊,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和以色列國防軍的空襲和轟炸比擬的。
此外,法農認為被壓迫者之所以採取暴力的形式,是因為暴力是由統治者先發起的。他寫道:
(對被壓迫者)他們一直喋喋不休:暴力才是他們唯一聽得懂的語言,於是以武力傳達訊息。但是我們的原住民也被這些殖民者洗腦了,足夠諷刺,當原住民開始抵抗時,他們也開始說什麼「暴力才是他們唯一聽得懂的語言」之類的話了。 (法農,1967年,15-16頁)
這有些有趣的動態,以及顯現的慾望,足以說明為何抵抗總是以像徵性暴力的形式出現。以巴勒斯坦常發生的飛彈和自殺式攻擊為例,他們確實是暴力,但也有自己的本體論功能。飛彈體現了這樣的顯現原則:雖然其執行者清楚:飛彈攻擊不會帶來什麼實際性傷害或傷亡,但是他們成功地被目擊而後顯現出來。自殺式炸彈攻擊可能有更顯著的本體論功能。 May Jayussi在她的對巴勒斯坦人使用自殺式襲擊的解讀中提到:自殺者如此急於擺脫赤裸生命的地位,以至於他們發動自殺式襲擊,來重新從以色列人手中奪回掌握自己生死的權力。這個想法令人矚目。因為對壓迫的抵抗被認為是如此重要,以至於人們願意結束自己的生命,而不是讓壓迫者再控制它。
在巴勒斯坦,兩種抵抗方式都試圖打破例外狀態,並且重新掌握自己的生命。然而他們的效果卻與想像的不同。這裡我們就要重返阿甘本了。 Catherine Mills對阿甘本的解讀中提到「任何嘗試透過自然生命來克服至高例外對生命的捕獲的方法,最後必然淪落到在生命的政治化過程中對自然生命的重新捕獲。」(Mills, 2008年,76頁)。阿甘本的意思,簡而言之,就是被壓迫者採用以暴制暴的方法會造成一種他們想要被納入,卻被進一步排除的矛盾狀態。
阿甘本的分析可以解釋巴勒斯坦在過去六十五年來的抵抗顯得如此徒勞無功的原因。從赤裸生命過程出發的抵抗陷入了一個兩難:那些不願受壓迫的人的唯一選擇(暴力)進一步助長了壓迫。在這種動態中,飛彈和自殺式攻擊等抵抗方法被主權用作採取更過分暴力措施的理由,主權力量不斷重複著這種動態。 「兩頭不討好」(Damned if you do, damned if you don't)這句格言似乎完全適用。在試圖被顯現的過程中,被壓迫者在更大程度上變得不被顯現。在試圖被納入的過程中,主體會在更大程度上被排除。在試圖控制自己的生命時,被壓迫者會更失去對自己生死的控制。巴勒斯坦人的抵抗往往激起以色列方面更大的反應,以色列方面會藉機將壓迫措施升級並發動新的攻勢。 Catherine Mills提出,抵抗理論的意義,在阿甘本看來,是必須將抵抗的可能性置於製造赤裸生命的主權結構之外(Mills,2008年,76頁)。主權,這個不斷捕捉赤裸生命的結構,使被壓迫者永遠無法透過內部途徑完全贏得鬥爭,只有透過外部壓力或幫助才能摧毀例外狀態。被佔領區作為例外狀態至少持續了三十年,但其不斷又徒勞的抵抗,似乎支持了這個論點。雖然法農和戈登為解釋抵抗理論和它們的內在矛盾做出了貢獻,但阿甘本最終還是給了答案。訴諸於赤裸生命的抵抗會使得壓迫以更純粹和可怕的方式顯現。
結語
本文提出的論點反映了馬哈茂德·達爾維什所痛惜的與生命相伴的死亡。本文利用喬吉奧·阿甘本的分析以及弗朗茨·法農和喬治·奇卡里奧羅·馬厄的理論,將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領土的佔領假定為一種例外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巴勒斯坦人淪為赤裸生命。透過對加薩地帶近期衝突的分析,以及對黎巴嫩安薩爾拘留營的簡短歷史研究,我們可以看到以色列司法-政治體系如何將自身轉化為殺人機器(阿甘本,2005年,86頁)。透過對阿甘本著作的解讀,我們可以看到佔領區的日常狀況構成了一種"永久性的空間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是潛在的神聖人(homino sacri)(阿甘本,1998 年,169,84)。我們分析的案例研究顯示了以色列強加的最純粹形式的主權暴力,加薩地帶和約旦河西岸的這種永久性例外狀態造成了巴勒斯坦人無法控制自己生死的局面。
針對壓迫者的象徵性暴力形式的抵抗,其作用是為被壓迫者提供顯現的機會,並在某些情況下將他們的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在過去的35 年中,抵抗得到的回應是更惡劣的日常生活條件、暴力軍事行動以及進一步滑向純粹的例外狀態,我們可以看出:阿甘本的觀點,即以赤裸生命為形式進行抵抗,會導致壓迫進一步惡化,似乎在巴勒斯坦得到了體現。巴勒斯坦人的生命緊鄰彼此,他們活著,但又沒有活著。
參考書目
Agamben, Giorgio (1998) Homo Sac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P.
Agamben, Giorgio (2005) State of Excep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Ciccariello-Maher, George (2010) “Jumpstarting the Decolonial Engine:Symbolic Violence from Fanon to Chávez.” Theory and Event 13.1.
Darwish, Mahmoud (2004) “Don't Apologize for What You've Done.” Now, As You Awaken. (date accessed 11.12.2012 http://www.bigbridge.org/DARWISH.HTM )
Fanon, Frantz (1967) Black Skin, White Masks. New York: Grove.
Gordon, Lewis (1997) Existence in Black: An Anthology of Black Existential Philosophy. New York: Routledge.
Gordon, Lewis (2007) “Through the Hellish Zone of Nonbeing Thinking through Fanon, Disaster, and the Damned of the Earth.”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Self-Knowledge. pp. 5-12.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Jayyusi, May (2004) “Subjectivity and the Public Witness: An Analysis of Islamic Militance in Palestine” (Unpublished paper for the SSRC Beirut Conference on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Middle East, October)
Khalili, Laleh (2008) “Incarceration and the State of Exception: Al-Ansar Mass Detention Camp in Lebanon.” Thinking Palestine. By Ronit Lenṭin. London: Zed. pp. 101-16.
Korn, Alina (2008) “The Ghettoization of the Palestinians.” Thinking Palestine. By Ronit Lenṭin. London: Zed, pp. 116-31.
Lenṭin, Ronit (2008) Thinking Palestine. London: Zed.
LeVine, Mark, and Lisa Hajjar (2012) “International Law, the Gaza War, and Palestine's State of Exception.” Al Jazeera. (date accessed 11.12.12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2/ 11/20121121103831534612.html )
Mason, Victoria (2012) “'No Permission to Shoot in Gaza Is Necessary': Israeli State Terror against Palestinians during Operation Cast Lead.” Counter-terrorism and State Political Violence: The “war on Terror” as Terror. Ed. Scott Poynting and David Whyte. London: Routledge. pp. 116-139.
Mills, Catherine (2008) The Philosophy of Agamben. Montreal: McGill-Queen's UP.
Pappe, Ilan (2008) “The Mukharabat State of Israel: A State of Oppression Is Not a State of Exception.” Thinking Palestine. By Ronit Lenṭin. London: Zed. pp. 148-71.
Ranciere, Jacques (2004) “Who Is the Subject of the Rights of Man?”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03.2-3. pp. 297-310.
[2]譯者註:此處應該是想表達創造赤裸生命是一種將生命排除性納入的機制,而並非透過法律或標記來預設赤裸生命。
[1]諷刺的是,ghetto一詞原意是歐洲城市的猶太人聚居區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