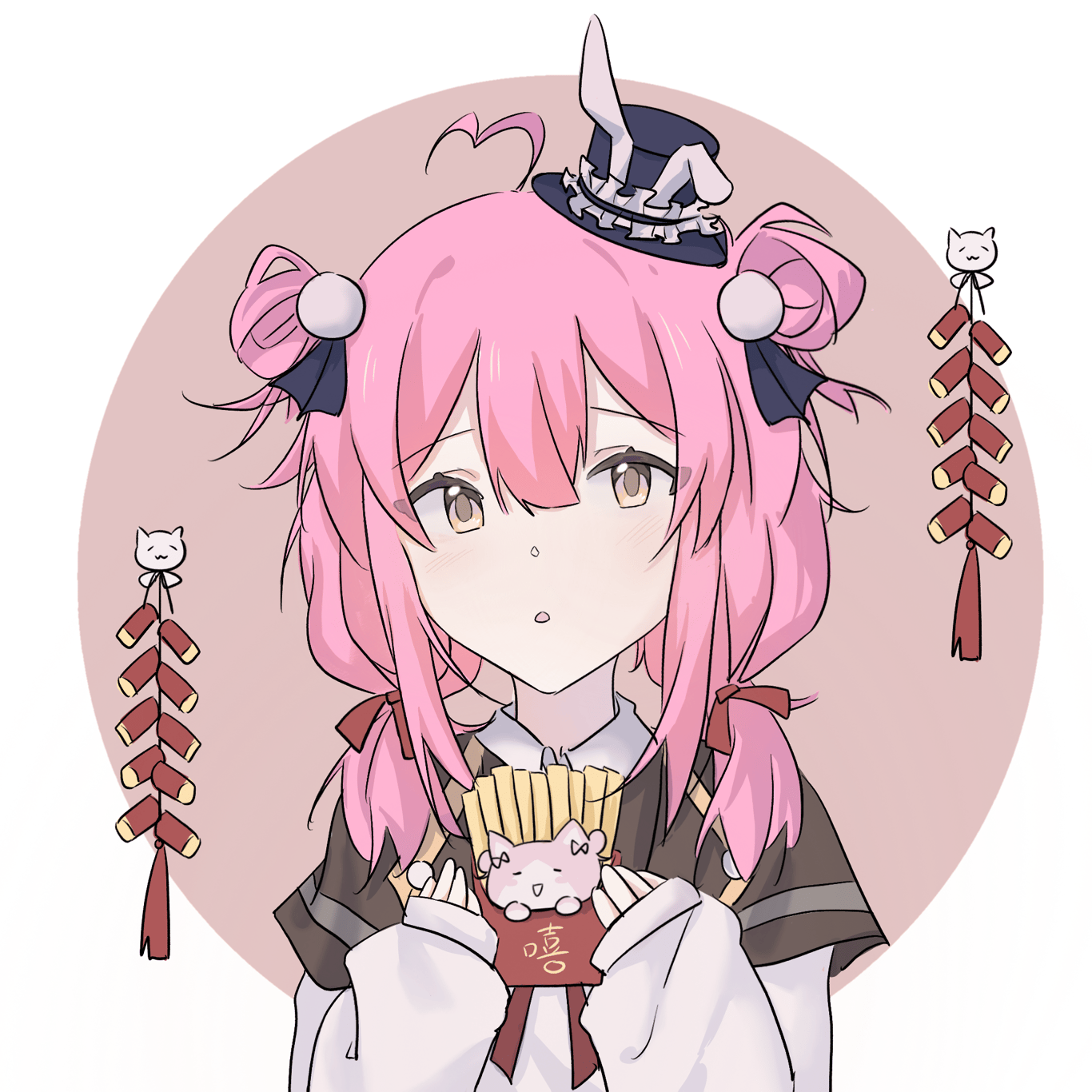随笔:革命的政治学
一切政治行动(对于政治行动的定义,我比较认同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君主论》中的定义,即对现实的改造)都需要有一套正当性背书,这大致为政治家提供了两个方向:一个是遵照当前占统治地位的正当性进行政治行为,例如在民主国家竞选公职;另一种就是否认当前的正当性并创造新的正当性作为政治行动的基础,这种行为就是革命。从这个定义而言,不是所有革命者都会发动革命,但革命者一定是将革命预设为目标且作为志业的人。并且由于革命本身特殊的性质,即一场改造现实的运动,革命者一定是一名政治家,革命一定是一种政治行为。
在此首先要解答的问题是,既然通过当前正当性允许的方式同样可以改造现实,那么革命的意义何在?首先,从最实际的角度而言,革命所提出的现实诉求大多违背了当下占统治地位的正当性:很现实的一点在于,正当性并不是一个空中阁楼,而是切实地基于其本身所依赖的基础和已经做出的政治决断;因此,一旦革命所提出的诉求不正当,其就必须创建新的正当性来满足这一诉求。在这一基础上,革命的行为就变得更有必要,因为对新的正当性的创造就必须基于对旧的正当性的扬弃或者毁灭。就这一点而言,中国革命的教训无疑是值得警醒的,共产党没有完全消灭国民党的势力,使得前者既无法继承中华民国的正当性,又碍于现实原因无法采纳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当性,只得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幌子悬置关于国家体制问题的决断,事实上,这一问题至今仍没有明确的结果。
那么,我们就可以归纳出革命的两个原则性要素:1. 宣布废除当前正当性的必要性,乃至于在实际上将其废除;2. 宣布建立新的正当性的必要性,乃至于在实际上建立之。为了继续关于革命性质的讨论,必须解答一个问题,即革命是否一定是暴力的,又是否一定会撕裂国家导致内战?
理论上而言,并非所有的革命都会导向内战,甚至可以说不是所有的革命都会包含暴力。从历史的经验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决定革命导向的要素:
当前的统治机关和其背后的正当支配形式越是脆弱,革命所带来的暴力就越少,导致内战的概率也会降低,反之亦然。俄国的二月革命就几乎是和平结束的,因为沙皇政府所依仗的军事力量已经背弃了皇帝,使得国家杜马可以直接接收原本的官僚机构并夺取全国的权力。
革命对当前正当性的否定越坚决,对新成立的正当性贯彻得越坚持,新的正当性相较于当前的差距越大,就越容易导致暴力和内战。圣雄甘地否认了大英帝国对印度殖民统治的正当性,但并没有果决地驱逐殖民者,同殖民当局进行有限的谈判,并且并没有过分关注新印度国家的国家体制问题,这一切使得印度得以和平地从英国独立。相反,钱德拉•鲍斯激进的主张最终使得其必须以武力达成独立的目标。但需要澄清的一点是,达成革命目的的手段无论多么温和,都必须遵守之前论及的革命的两个原则性要素,否则就算不得革命,也必定会迎来失败的结局。
在各方面落后的国家,革命就更容易导致内战和暴力。这一点很好理解,主要源自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地方掌控力的低下使得反对派更容易在地方建立政权、啸聚山林;其次是在这种国家参与政治的成本很高,高到许多人不得不使用暴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统治大陆时的中华民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经过这番讨论,我们已经了然暴力并非是革命的必须要素。相反,对暴力的迷信与滥用往往会导致革命的失败。也是从这个角度,革命必须被纳入政治的范畴。因此,现实的革命策略就变得至关重要。
革命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是当前正当性是否牢固,如果是,那么贸然发动革命就无异于自杀,因为革命本身包含了对当前正当性的否定,如果这份否定都不够正当,那么革命本身也不会正当,作为一种政治行为的革命也不会成功;在此时,协商,非暴力斗争,合法政党政治显然是更好的手段。如果不是,那么便是发动革命的好时机。以执政者的逻辑而言也是一样的,面对没有触及根本的反对派一般不会镇压,而是采取招抚,贿赂或者协商的策略;而面对已经提出革命的纲领的反对派就会果断地予以镇压。照此相反行事的政治家往往都会遭遇失败,比如蒋介石不顾一切地弹压一切反对势力,最终导致反对派主张越发激进,越发地有组织,以至于导致了自己的败亡。因此对于革命者而言,遇到这种庸劣的暴君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遇到精明的,难以对付的政治老手,这种人对于政治行为的尺度是十分明晰的,也更能够维护当前的正当性。
这样一来,一个几何学模型就出现了:我们想象一个线段,中间取一中点。中点左边的部分就是反对派尚处于合法状态,没有满足之前提到的两个原则性要素时的部分,中点右边的部分就是已经破旧立新,发动革命的部分,这我们已经讨论过了。那么这个中点代表什么呢?就是反对派运动不再合法,但又没有创立新的正当性的状态,这种状态我们将其称为叛乱(insurrection)。
美国南方的邦联政权就是典型的陷入了尴尬的叛乱状态的政权的例子。美利坚联盟国没有否认当前政权的正当性,尽管它否认了联邦政府在南方十一个州统治的正当性,但并没有否认联邦政府本身存在的正当性,也没有采取新的国家体制,更没有宣称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无论从什么角度而言,美利坚联盟国都不具备存在的正当性,对此,法学家可以进行更多的论辩,但我们的目的已经达成:革命者从中可以学习的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其运动无论如何不能沦落到叛乱的状态,否则只会迎来最严厉的镇压和最惨痛的失败。与之相对的,美国独立战争就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例子,开国元勋没有止步于宣布十三个殖民地脱离大英帝国;相反,他们援引包括洛克在内的政治学和法理学学说,谴责乔治三世是一名暴君,论证君主正当性在北美殖民地已经不再适用,并吸取了共和主义价值观树立新的民主正当性取而代之,因此,美国人将独立战争称为“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是恰如其分的。另一个成功范例,印度,也是类似的,只不过其直接的正当性来源则是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诉求,当一群人已经以民族的形式聚集起来,他们统一表达出的诉求便已经天然地具有正当性,无需再援引什么事物去证明。
另一方面,只要政治的诉求具有了足够的正当性,那么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正当的,正如凯撒所说:为了正当目的可以不择手段(exitus acta probat)。弗拉基里尔•列宁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列宁政治决断的正当性已经被证明:一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专政的正当性,二是制止俄国临时政府不得人心的战争政策。因此,列宁可以毫不顾忌地接受德国人的帮助回到俄国。这不仅不是列宁的污点,反而体现了列宁天才般的政治禀赋,这一禀赋在之后列宁毅然发表四月提纲,发动十月革命,以及解散制宪会议都得到了证明。事实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影响就在于他赋予后者政治家的视阈,正如我们所讨论过的,无论对现实进行什么样的改造,都需要正当性的推力,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列宁所选择的正当性,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有丰富的政治经济学意义,更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学内涵。与此相对的,汪兆铭之流的曲线救国之所以必然失败,就是因为当时没有人,哪怕共产党,也无法否认抗日战争赋予国民政府的正当性,因为它并不是像俄国与同盟国的战争那般已经失去了持续的意义和理由。
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学难题就是不断扩张的主权权力和人民逐渐被挤压的政治生活间的矛盾。革命,无论其实现的难度有多大,永远是对此难题的唯一解答。主权以保卫宪法和正当性为名进行的独裁只能以新的宪法和正当性取而代之才能消灭。主权独裁和革命有一种奇妙的联系:他们都无效化了当前的法律,创造出了一个例外空间。区别在于,革命的目的是扩大甚至创造人民的政治生活;而主权独裁则是要竭力地压缩之。这也就呼应了本雅明说的,为了结束当前的例外状态(法西斯主义),必须要创造一个新的例外状态(革命)。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