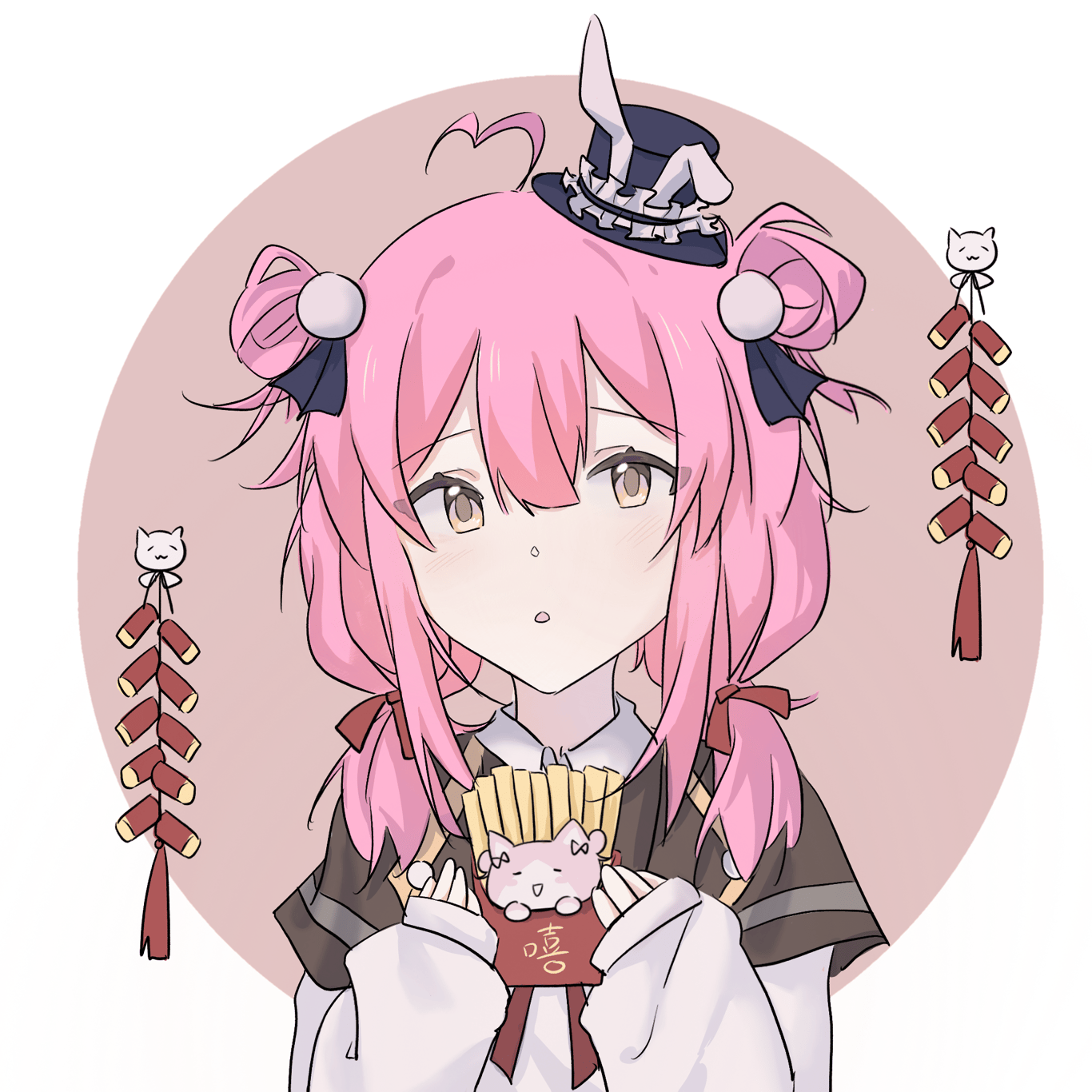巴勒斯坦的赤裸生命
作者:Jordan Street
媒体: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发布时间:2013年5月4日
译者:Spadetaffy
原文url:https://www.e-ir.info/2013/05/04/bare-life-in-palestine/
奥兰普·德·古热(Olympes de Gouges),一位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判处死刑的革命女权主义者,在临死前哀悼说:“如果妇女可以走上断头台,她们应同样有权利参加议会。”(朗西埃,2004年,299页)。法律统治了她,但她无权支配法律。而巴勒斯坦人民,尤其是饱受压迫的加沙地带(Gaza Strip)和其他被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也遭遇着类似的状况。他们对统治他们的法律没有发言权,同时还要受到外来军事统治的压迫,并且同样“可以走上断头台”。本文会尝试将乔吉奥·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哲学应用到巴勒斯坦上,并试图检验巴勒斯坦人是否符合阿甘本的“赤裸生命”(Bare Life)定义。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政府的政策创造了一种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在其中,巴勒斯坦人的生命陷入了外部主权(Sovereign)的决断中。但另一方面,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使得阿甘本的理论不能在此处被完全套用。因此,本文也参考了弗朗茨·法农(Franz Fanon)和乔治·奇卡里奥罗·马厄(George Ciccarello Maher)来进行全面的理论分析。我认为:例外状态理论和抵抗运动是相容的,后者在被占领土上以“象征性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形式运行。然而,这种象征性暴力实际上帮助了主权构建一个更纯粹的“例外状态”。
本文将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根据历史上和当代的资料来支持以上的论点。我们将提及诸如2008-2012年的加沙战争,以及黎巴嫩南部的拘留营,作为血腥压迫的证据。我们将考察巴以关系,以及每日可见的在占领区的压迫和虐待。为了叙事方便,本文会将以色列预设为一个民主国家,尽管并不完美,并且学术界的很多人质疑这一点。
对巴勒斯坦、以色列、“例外状态”和“赤裸生命”的分析
自1948年,以色列国家建立的伊始,该国就采用了英国1945年对巴勒斯坦管制时期的“紧急条例”(Pappe, 2008年,148页)。自此,以色列就开始采用多种方式来限制巴勒斯坦人获取诸如水源,土地,工作,资源,家园……并弹压所有的抵抗运动。并且以色列国家有上百条法律,能够使得其政府随时宣布巴勒斯坦人的聚居区为“军事禁区”(Pappe, 2008年,148页)。以色列自建国以来,占领了巴勒斯坦历史领土的77%,包括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West Bank)。这些占领区条件恶劣,充满压迫。加沙地带筑满高墙,并且有多个以色列士兵看守的检查点,他们控制人员,货物的流动,并且维持对当地领空,领海,人口,税收和基础服务的控制(Korn, 2008年,116页)。毋庸置疑,以色列军队是当地巴勒斯坦人的控制者。当地的巴勒斯坦人,自从被以色列控制以来,就一直生活在近似于贫民窟(ghetto[1])的地域。(Korn,2008年,122页)
最近,加沙地带已经从这个“近似贫民窟的地域”变成了活生生的战场。在2008年和2012年,以色列发动了数次压倒性进攻,导致了几百名平民的死亡。巴勒斯坦人被占领区的法律管制着,但对其没有任何发言权。这些巴勒斯坦人既被法律纳入,又同时被排除。这样的一种动态是乔吉奥·阿甘本研究的重点,也是我们这篇文章将要叙述的。
基于卡尔·施密特(Karl Schmitt)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思想,阿甘本以“例外状态”评价当代民主体制。阿甘本语境下的例外状态,是一个由主权决断的,无法区分政治和法律的地带(阿甘本,2003年,10-11页)。这并不是我们常说的无政府状态,也不是托马斯·霍布斯语境下的“自然状态”,它还是处于准运行状态的。然而,例外状态之下,原本朦胧的权力变成了主权统治,他能随时“弃置”(abandon)一些人,并剥夺他们的“合法”权益。尽管“例外状态”一词听着只是国家紧急状态下的权宜之策,但实际上,它已经逐渐发展为主权与生命的压迫关系,因为主权能够决断例外状态,它事实上能够随意摆布那些处于,或可能处于例外空间的人们的生死。(Mills,2008年,59-62页)
例外状态下的生命被缩减到了生命的原初形式:阿甘本称之为“赤裸生命”(阿甘本,1998年,11-13页)。赤裸生命是主权的固有结构和原初功能方式(Mills,2008年,61页)。它本质上是压迫者能被缩减到的最低级的生命形式,以政治化的方式被暴露于死亡之下(阿甘本,1998年,88页)。当那些以“主权转移”,“宪法变更”为名义的例外变成常规时,例外状态就完成了(Pappe,2008年,152-156页)。在无区分的例外空间内,那些法律的例外变成了唯一的准则,而里面的生命被缩减到了赤裸生命。在这至高例外的生命既臣服于法律,又被“无意义的法律所掌管”(Mills,2008年,64页)。生命在其中仍然是政治化的,但是是以最赤裸的形式,生命被主权“弃置”,并且后者握有对其的生杀大权(阿甘本,1998年,90页)。通过这一套理论,我们将要考察巴勒斯坦的抵抗和斗争。
巴勒斯坦占领区服从以色列国家的一切法律:不管是条例还是司法。他们被外部主权政治化,但又与此同时被从城邦中排除出去。这种排除性的纳入,如我们之前所说,就是主权的基本行为范式。以色列对占领区有宪法赋予的管辖权,同时把当地的所有生命的各方面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虽然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和“哈马斯”都宣称自己代表了巴勒斯坦人民,但实际上他们都被以色列这个外部主权所限制,这个主权可以随时悬置法律并对占领区人民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巴勒斯坦人并不生活在“无法制”的社会,而是生活在法律的反面(Korn,2008年,123页)。更简单地说:如果说无政府状态代表一个掌控生命的外部主权的缺失,那么巴勒斯坦的状态则是无限制的国家权力的实践(Korn,2008年,123页)。阿甘本的理论,主要是讨论现代民主国家如何通过弃置生命于例外空间来运转其压迫机器(阿甘本,1998年,10页)。所以说,如果我们把以色列定义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那么它的政策似乎是在不断地将巴勒斯坦人变成赤裸生命。如同Robert Lentin所说:
从以色列复杂的紧急条例制度,以及司法机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间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和生活在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的作用来看,我们似乎很快就能将巴以的状态(和赤裸生命)联系起来。(Lentin 2008年,6页)
根据国际法,加沙地带自1967年来一直处于被占领状态,该地的所有人员流动,需求和服务都由以色列军方控制。因此,对一个已经是占领区的地方发动战争显得没有什么法律依据。(Haajar and Levine 2012)因此,最近的两次:2008年和2012年的战争,本质上是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这两次,以色列政府都根据一些掉落在他们境内的导弹(实际上没造成伤亡)宣称他们在自卫。这一点并不是很站得住脚,尤其是在最近,巴勒斯坦方面宣称一次导弹袭击是出于一个5岁巴勒斯坦小孩误入边境遭射杀而进行的报复(Haajar and Levine 2012)。在两次以色列方面的军事行动,2008年的铸铅行动(Operation: Cast Lead)和2012年的云柱行动(Operation: Pillar of Defense)中,以色列军队残忍地进攻平民区,并且杀害了大量的巴勒斯坦平民。这更加使得以色列的自卫说辞让人怀疑。在铸铅行动中,有证据证明以色列使用了白磷弹无区别地杀死了1300巴勒斯坦人。在最近,又有160余人被以色列政权杀害,其中很多是妇女和儿童,已经达到了战争罪行的程度。妇女和儿童和男性被以相同的比例屠杀是一种种族灭绝的现象,是国际法所绝对禁止的。
在以上的例子中,我们都看到了阿甘本语境下的例外状态。以色列政权采用法律手段来保证对占领区的控制及发起军事行动。主权则通过以色列国防军(Israel Defense Force)的坦克,飞机,直升机,炮艇和狙击手来显现自身。然而,更令人忧虑的是,在国际人士,以色列人,甚至巴勒斯坦人看来,这两场冲突都不是例外。在他们眼里,这就是常态。也因此,如同Mark Levine和Lisa Hajaar所说,以色列将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置于了常态化的例外状态之下(Haajar and Levine 2012)。
这表明了加沙,这样一个以色列人强大到随意颁布任何政策的地方,其情况是多么令人绝望。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掌控巴勒斯坦人的生死:他们可以杀死巴勒斯坦人而“不犯杀人罪”(阿甘本,1998年,83页)。他们被捕获至一个自然界和人类共同体的边界,或者如阿甘本所说的“无区分地带”(zone of indiscernibility)(阿甘本,1998年,4页)。诸如铸铅行动和云柱行动一类的军事行动,将巴勒斯坦人的生命缩减为纯粹的赤裸生命,他们被弃置,生死被掌握在以色列人手中。
这个论题的另一个缩影就是位于黎巴嫩南部由以色列国防军掌控的安萨尔拘留营(Al-Ansar Detention Camp)。在1982年至1985年,以色列军队在此关押了15000人左右,其中很多人都没有或者仅犯小罪。囚犯们的食物来源、医疗照护和必需品均极其有限,他们常被殴打,被折磨,囚室里屎尿横行,有些甚至堆到了膝盖的高度(Khalili,2008年,101-102页)。这种在国外建立虐待型设施的行为是由宪法修正案中的一项紧急状态措施条例所保障的。如同Laleh Khalili所说,以色列“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法律和政治机构‘战俘营’来剥夺囚犯们的合法权益,甚至扩展到了治外法权来扩展主权的权力。”(Khalili,2008年,114页)。她进一步提到,当局有权悬置任何法律或条例,并且能够随意地使用任何法律。(Khalili,2008年,106页)
本质上,这个拘留营就是例外状态的最纯粹形式,可怕的暴行通过主权对法律的修改而时时上演。以色列将“潜在的暴力和冲突推到了普通惩罚体系之外,将暴力的军队放到一个安全区,让他们放开拳脚”(Khalili,2008年,112页)。安萨尔拘留营的囚犯们近乎陷入“昏迷状态”了,他们对施加于自己的压倒性暴力无能为力。主权通过修改法律掌握了这些囚犯的生杀大权。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抵抗都是无用功,都会被以最残酷的方式镇压。
Catherine Mills指出,这种反抗—镇压的动态是将最纯粹的赤裸生命形式与其他类似的案例区分开来的。她说,在这样的过程中,“值得质疑的暴力(Aporetic Violence)……阻碍了在框架内反对生命政治政权的任何尝试”(Mills,2008年,75页),这在安萨尔拘留营中得到了体现。然而,正如我们在之前对加沙攻势的案例研究中看到的那样,巴勒斯坦是有一些抵抗的方法的(无论它们是否可行)。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将阿甘本的分析成功地应用到巴勒斯坦斗争中,是否还缺少一些东西?
象征性暴力:通过显现来抵抗
第一部分中展现的两个案例体现了主权是如何在例外状态中对赤裸生命进行掌控的。它们再现了赤裸生命的最纯粹形式,一个由某种“机制”,而非“预设”所创造的生命[2](阿甘本,2005年,88页)。当然,这不意味着除了这两个案例之外的巴勒斯坦人就没有生活在例外状态之下,这是一个由类似案例创造的纯粹的存在。除了这些案例,基于对司法悬置的占领和压迫仍然存在。在检查站进行杀戮,贫困造成的死亡,以及集中营里的折磨依然是屡见不鲜。然而,不可否认,巴勒斯坦人展示了一种和例外状态不完全一致的生存状态。
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迈克尔·哈特(Micheal Hardt)表示阿甘本预设生命基本上总是和主权处于被动关系(哈特和奈格里,2000年)。在巴勒斯坦,很显然,被动臣服并非是占领区人民反抗压迫的唯一手段,这说明阿甘本的分析可能存在一点问题。但Lentin基于自己对阿甘本的解读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例外状态确实包含了潜在的抵抗。(Lentin,2008年,11页)。与之类似,Catherine Mills也认为抵抗存在于例外状态之中,她认为在阿甘本那里,抵抗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并且可能会起到反效果。然而,不论是在Mills的解读,还是在阿甘本的原著中,都没有提到抵抗运动的起因和效果。
在巴勒斯坦,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抵抗,其目的自然是为了反对以色列创造的压迫系统和例外状态。但人们其实没有充分认识到抵抗的目的是什么,抵抗的过程是什么,抵抗的最终效果是什么。在刘易斯·戈登(Lewis Gordon)对弗朗茨·法农的解读中,法农描述了一个进程:被压迫者(原文是黑人,此处为叙事方便说成巴勒斯坦人)被放置到非存在的地狱,一个似乎显现(appearance),似乎不显现(disappearance)的场所。这与阿甘本的思想不谋而合,此处的显现和不显现和排除和纳入是一样的。戈登认为,在这种过程中,唯一可接受的存在就是非存在,就是非显现(disappearance),就是臣服。我们又看到了那不能掌握自己生命的赤裸生命。然而,正如我们所说,巴勒斯坦确实是有抵抗的。就这一点,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进行了解释。
他认为,在长期的占领和压迫下,抵抗不仅仅是常见的,而且是被期待的,预料之中的。法农的分析认为被压迫者终究会到达无法忍受被压迫的境地,并且将殖民者驱逐出家园的愿望(法农,1967年)。这种心理变化的过程是值得分析的。为了摆脱压迫,摆脱赤裸生命的境地,被压迫者会做出他之前所做的相反的事,就是去显现(appear)。显现就是为了抵抗,不去显现,抵抗就不会有希望。然而,这种显现可能会有相反的效果。对此,戈登写道:
如果想改变现状,就要去显现,但是显现必须要通过暴力,因为显现对被压迫群体是非法的。这里,暴力毋须是身体上的强制,毋须是火枪的破坏,它只须是显现。(戈登,2007年,12页)
即便以抵抗为形式的显现仅仅名义上是暴力的,它其实已经失去了其本体论上的功能。
巴勒斯坦人希望摆脱压迫和不义,他们希望摆脱“弃置”。为此,他们挑战那“把存在和非存在分隔开的排除之墙,这样的破坏使得显现表现为纯粹的暴力。”(奇卡里奥罗-马厄,2010年)。法农认为以暴力显现的抵抗,比如导弹和自杀式袭击,是“无论从表象还是内在,都不可与压迫者的暴力同日而语的。”(奇卡里奥罗-马厄,2010年)。此时,显现的本体论功能变得无效了。此外,那些导弹和自杀式袭击,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和以色列国防军的空袭和轰炸比拟的。
此外,法农认为被压迫者之所以采用暴力的形式,是因为暴力是由统治者先发起的。他写道:
(对被压迫者)他们一直喋喋不休:暴力才是他们唯一听得懂的语言,于是以武力传达信息。但是我们的原住民也被这些殖民者洗脑了,足够讽刺,当原住民开始抵抗时,他们也开始说什么“暴力才是他们唯一听得懂的语言”之类的话了。(法农,1967年,15-16页)
这有些有趣的动态,以及显现的欲望,足以说明为什么抵抗总是以象征性暴力的形式出现。以巴勒斯坦常发生的导弹和自杀式袭击为例,他们确实是暴力,但也有自己的本体论功能。导弹体现了这样的显现原则:虽然其执行者清楚:导弹袭击不会带来什么实际性伤害或者伤亡,但是他们成功地被目击而后显现出来。自杀式炸弹袭击可能有更显著的本体论功能。May Jayussi在她的对巴勒斯坦人使用自杀式袭击的解读中提到:自杀者如此急于摆脱赤裸生命的地位,以至于他们发动自杀式袭击,来重新从以色列人手中夺回掌握自己生死的权力。这个想法令人瞩目。因为对压迫的抵抗被认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愿意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不是让压迫者再控制它。
在巴勒斯坦,两种抵抗方式都试图打破例外状态,并且重新掌握自己的生命。然而他们的效果却与想象的不同。这里我们就要重返阿甘本了。Catherine Mills对阿甘本的解读中提到“任何尝试通过自然生命来克服至高例外对生命的捕获的方法,最后必然沦落到在生命的政治化过程中对自然生命的重新捕获。”(Mills,2008年,76页)。阿甘本的意思,简而言之,就是被压迫者采用以暴制暴的方法会造成一种他们想要被纳入,却被进一步排除的矛盾状态。
阿甘本的分析可以解释过去六十五年来巴勒斯坦的抵抗显得如此徒劳的原因。从赤裸生命过程出发的抵抗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那些不愿受压迫的人的唯一选择(暴力)进一步助长了压迫。在这种动态中,导弹和自杀式袭击等抵抗方法被主权用作采取更过分暴力措施的理由,主权力量不断地重复着这种动态。“两头不讨好”(Damned if you do, damned if you don’t)这句格言似乎完全适用。在试图被显现的过程中,被压迫者在更大程度上变得不被显现。在试图被纳入的过程中,主体会在更大程度上被排除。在试图控制自己的生命时,被压迫者会更多地失去对自己生死的控制。巴勒斯坦人的抵抗往往会激起以色列方面更大的反应,以色列方面会借机将压迫措施升级并发动新的攻势。Catherine Mills提出,抵抗理论的含义,在阿甘本看来,是必须将抵抗的可能性置于制造赤裸生命的主权结构之外(Mills,2008年,76页)。主权,这一不断捕获赤裸生命的结构,使被压迫者永远无法通过内部途径完全赢得斗争,只有通过外部压力或帮助才能摧毁例外状态。被占领区作为例外状态至少持续了三十年,但其不断又徒劳的抵抗,似乎支持了这一论点。虽然法农和戈登为解释抵抗理论和它们的内在矛盾做出了贡献,但阿甘本最终还是给出了答案。诉诸于赤裸生命的抵抗会使得压迫以更纯粹和可怕的方式显现。
结语
本文提出的论点体现了马哈茂德·达尔维什所痛惜的与生命相伴的死亡。本文利用乔吉奥·阿甘本的分析以及弗朗茨·法农和乔治·奇卡里奥罗·马厄的理论,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假定为一种例外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巴勒斯坦人沦为赤裸生命。通过对加沙地带近期冲突的分析,以及对黎巴嫩安萨尔拘留营的简短历史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司法-政治体系如何将自身转化为杀人机器(阿甘本,2005年,86页)。通过对阿甘本著作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占领区的日常状况构成了一种 "永久性的空间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是潜在的神圣人(homino sacri)(阿甘本,1998 年,169,84)。我们分析的案例研究展示了以色列强加的最纯粹形式的主权暴力,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这种永久性例外状态造成了巴勒斯坦人无法控制自己生死的局面。
针对压迫者的象征性暴力形式的抵抗,其作用是为被压迫者提供显现的机会,并在某些情况下将他们的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在过去的 35 年中,抵抗得到的回应是更恶劣的日常生活条件、暴力军事行动以及进一步滑向纯粹的例外状态,我们可以看出:阿甘本的观点,即以赤裸生命为形式进行抵抗,会导致压迫进一步恶化,似乎在巴勒斯坦得到了体现。巴勒斯坦人的生命紧挨着彼此,他们活着,但又没有活着。
参考书目
Agamben, Giorgio (1998) Homo Sac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P.
Agamben, Giorgio (2005) State of Excep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Ciccariello-Maher, George (2010) “Jumpstarting the Decolonial Engine:Symbolic Violence from Fanon to Chávez.” Theory and Event 13.1.
Darwish, Mahmoud (2004) “Don’t Apologize for What You’ve Done.” Now, As You Awaken. (date accessed 11.12.2012 http://www.bigbridge.org/DARWISH.HTM)
Fanon, Frantz (1967) Black Skin, White Masks. New York: Grove.
Gordon, Lewis (1997) Existence in Black: An Anthology of Black Existential Philosophy. New York: Routledge.
Gordon, Lewis (2007) “Through the Hellish Zone of Nonbeing Thinking through Fanon, Disaster, and the Damned of the Earth.”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Self-Knowledge. pp. 5-12.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Jayyusi, May (2004) “Subjectivity and the Public Witness: An Analysis of Islamic Militance in Palestine” (Unpublished paper for the SSRC Beirut Conference on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Middle East, October)
Khalili, Laleh (2008) “Incarceration and the State of Exception: Al-Ansar Mass Detention Camp in Lebanon.” Thinking Palestine. By Ronit Lenṭin. London: Zed. pp. 101-16.
Korn, Alina (2008) “The Ghettoization of the Palestinians.” Thinking Palestine. By Ronit Lenṭin. London: Zed, pp. 116-31.
Lenṭin, Ronit (2008) Thinking Palestine. London: Zed.
LeVine, Mark, and Lisa Hajjar (2012) “International Law, the Gaza War, and Palestine’s State of Exception.” Al Jazeera. (date accessed 11.12.12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2/11/20121121103831534612.html)
Mason, Victoria (2012) “‘No Permission to Shoot in Gaza Is Necessary’: Israeli State Terror against Palestinians during Operation Cast Lead.” Counter-terrorism and State Political Violence: The “war on Terror” as Terror. Ed. Scott Poynting and David Whyte. London: Routledge. pp. 116-139.
Mills, Catherine (2008) The Philosophy of Agamben. Montreal: McGill-Queen’s UP.
Pappe, Ilan (2008) “The Mukharabat State of Israel: A State of Oppression Is Not a State of Exception.” Thinking Palestine. By Ronit Lenṭin. London: Zed. pp. 148-71.
Ranciere, Jacques (2004) “Who Is the Subject of the Rights of Man?”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03.2-3. pp. 297-310.
[2] 译者注:此处应该是想表达创造赤裸生命是一种将生命排除性纳入的机制,而并非通过法律或者标记来预设赤裸生命。
[1] 讽刺的是,ghetto一词原意是欧洲城市的犹太人聚居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