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地震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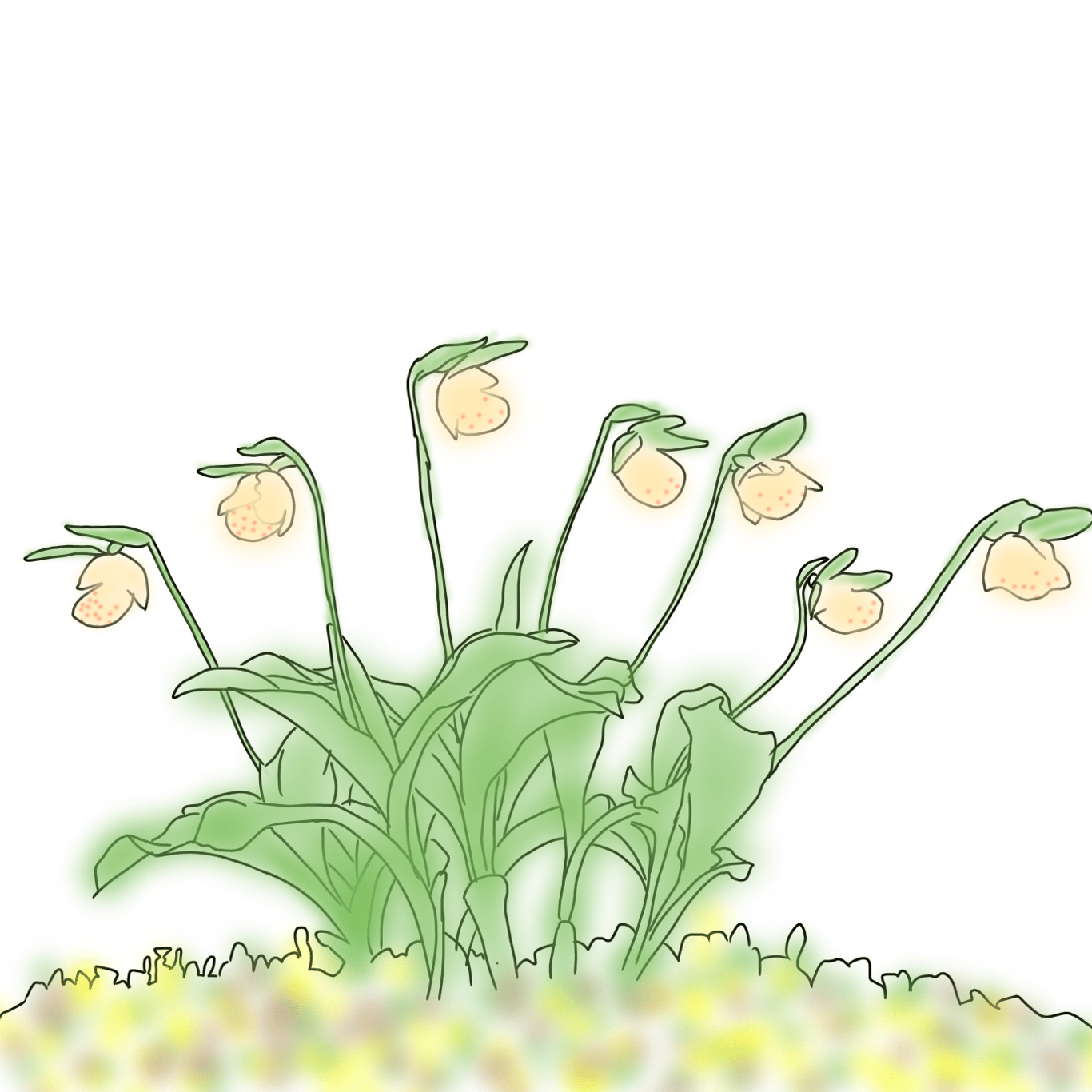
今天早上第一次收到地震警報,還在睡夢中就被一個機械的女聲叫醒,但我竟然膽敢用自己的身體和覺知來感受,試著自己判斷是否地震到需要跑的程度,其結論是沒有,然後無比安然地睡著了。兩個多小時後醒來,看到鋪天蓋地的SNS 都在說地震警報的事,才有種後怕的感覺,慶幸並沒有真的發生地震。
我想了一下,我為什麼會有這種膽子,其實來到東京以後,也經歷過數次幅度不一的震況,但我幾乎都沒有害怕過。今早我下意識還是相信了自己的感覺,可能是因為睡夢中不清醒的緣故,因為醒著的我就會知道,至少東京的天氣預報是很準的,地震警報也應該值得信賴。這樣的“膽大妄為”,可能是因為我一直住在雲南,住在地理課本上所寫的地震帶上,經歷過很多次這種睡夢中的搖晃。
自從來到日本以後,總有人在問地震的事,但其實從「世界各國1973-2017 年M≥6 大陸地震數」的統計情況來看,中國才是排名第一的國家,日本卻在第十位。 1920 世紀以來,中國死於地震的人數高達55 萬,佔全球地震死亡人數的53%。
我覺得很多中國人看到這個事實,是很震撼乃至於震驚的。就算就像是住在地震帶上的我,對地震擁有一些淺薄的經驗,還是會被事實嚇一跳,畢竟我們長久地生活在「災害新聞」只會跟踪報道日本的國家,對自己境內實際發生的災害不聞不問,恨不得藏著摀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叫人知道才好。
昨晚有年輕的朋友問我核廢水排放的事,起因是她在購物節大促銷的時候搶購了一支日產的卸妝乳。但她不直接問,這個東西能不能用──如果是這樣,評價的標準就很多了。然而她直指的是核廢水排放問題。
其實我對人這種不加自我辨別的狀態,已經到了十分厭惡的地步,但我想了一下,他們又怎麼能辨別,哪怕是一場民粹主義的狂歡,也是在政府助長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那就跟國家政策直接宣布日本的東西不能用又有什麼差別──這種事也不是沒發生過。所以我還是耐心地跟她說了現實狀況,請她放心使用。
我寫到一半才驚覺「家」已經從雲南變成了中國,這樣一個巨大的投影,這是我所不願意接受的。但其實到我這裡——我很難說是一代人,但可以說是一部分人吧,比如說中國的留守兒童、流動人口群體——「家鄉」更是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在我的童年時期,就經歷了十幾次的搬家,然後被迫丟掉一些東西,和所有相識的人告別,然後徹底地忘記他們。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家」和「家鄉」的概念也就隨之而破碎了。
我現在很難說哪裡是我的家鄉,我只會說我住在哪裡,我甚至會描述成“我媽媽的房子”,而並非我們的家。它現在位於雲南東南部的一個小縣城,除了以上所描述的地震頻傳,它還處於亞熱帶,一年四季只有春夏。
二月,我回了一趟家,已經是31 度的天氣,公車搖搖晃晃,緩慢地駛向我12 歲以後才搬進的房子。我姑且稱之為“家”,但過去是空白的,在我人生中對“家”的依戀形成的童年時期,並沒有一所房子能夠讓我的依戀棲居。
至於“家鄉”,我能在地圖上確認出一個範圍,然後便不能往下了,我的記憶幾乎和地圖一樣,是空白的,是不可查。
我想這不只是我個人的經驗,中國在這過去三十多年的城市發展過程中,人口流動是如此的迅速,「家」和「家鄉」就像是我們褪下的皮,不會永遠留在那裡,也沒有足夠的空間能夠承載它風化成記憶。
基本上再過兩年,你回到同一個地方,它就已經變化得讓人認不出來了,與「家」和「家鄉」這種恆常的、近乎可以說是永恆的概念,是相背道而馳的。
2024 年6 月3 日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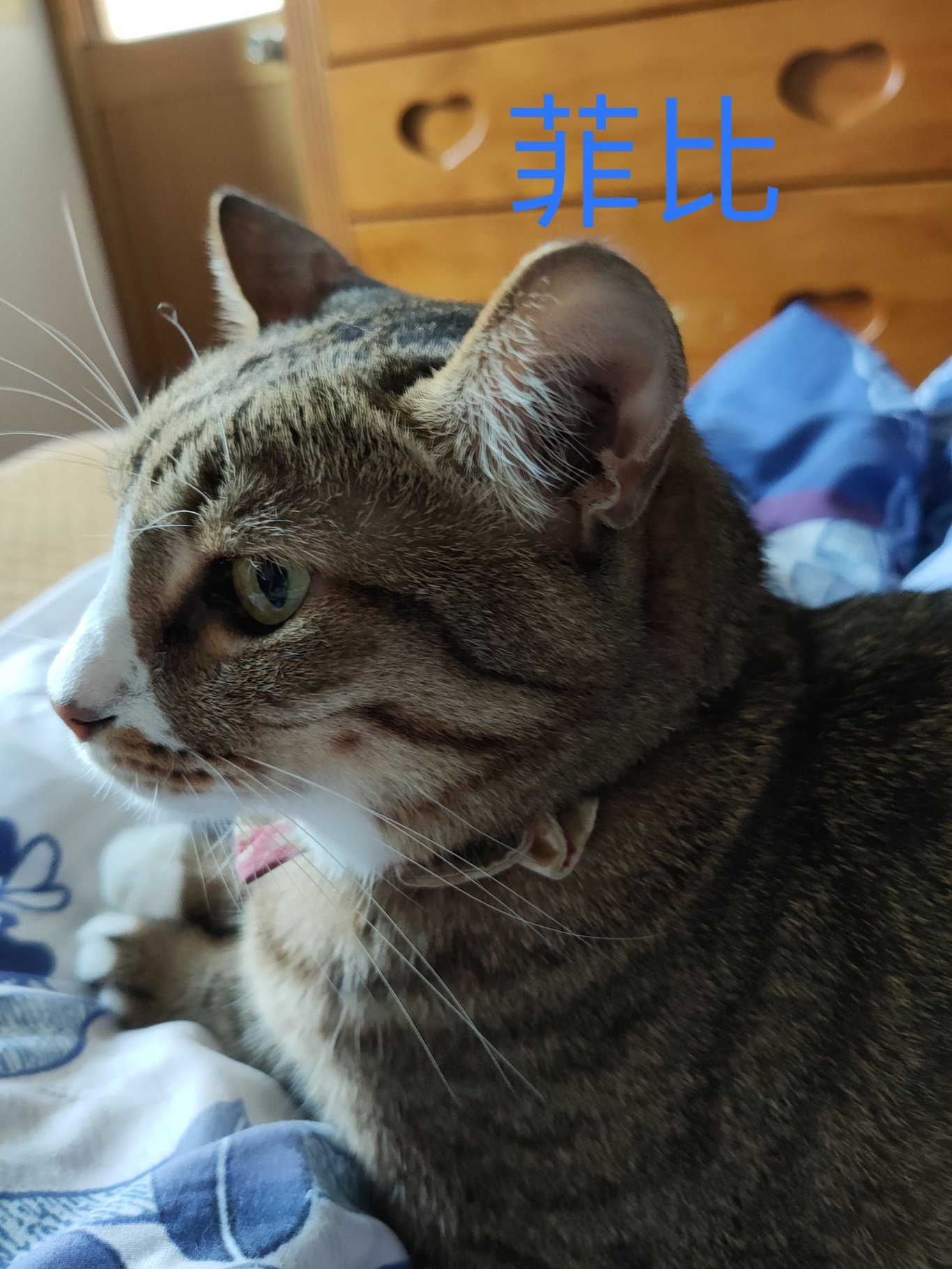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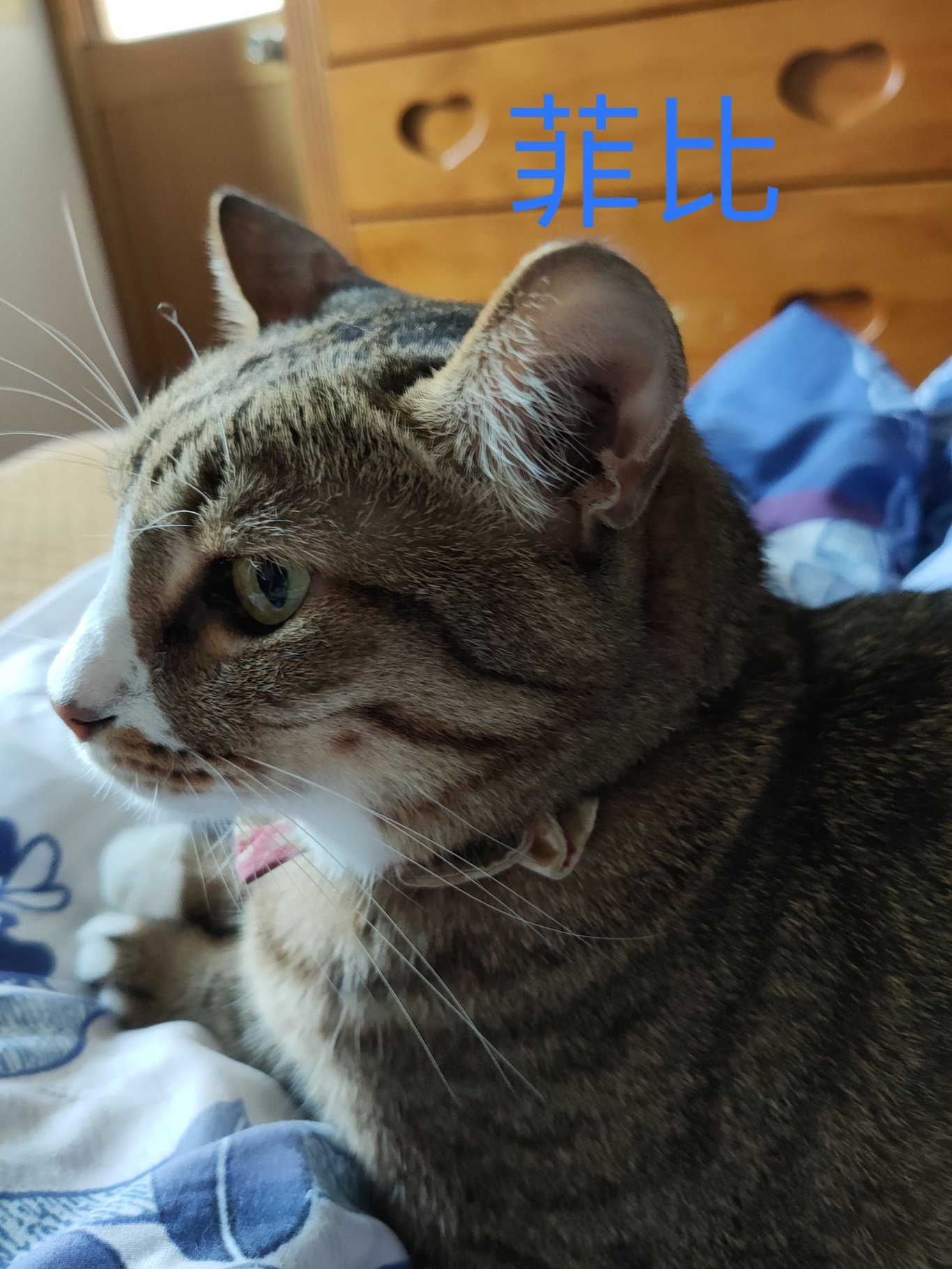








- 來自作者
- 相關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