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顆炸彈落在我們頭頂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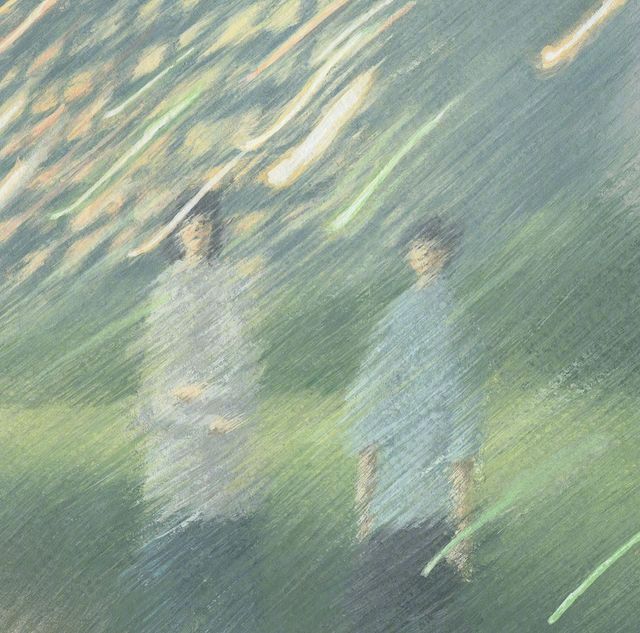
小時候在教科書上讀過的那些有關戰爭的記載,卻以為是像猛獁像一樣遙遠又古老的存在,相信偉大的現代文明會將一切衝突包裹其中,相信戰爭已經退出了人類歷史,而誕生在和平年代的我們,就好像是科幻電影裡嶄新的純白無暇的一代,閱讀戰爭也像是在閱讀人類歷史的切片,古老罕見的標本。
但也偷偷地想過,也許在有生之年會親眼目睹一場戰爭。於是看到新聞上的伊拉克,戰爭實際發生在距離現實世界那樣近的年份,地理上跨過山脈和平原,一些與我們生在同時代的兒童,卻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
現代戰爭就這樣堂而皇之的發生,在教科書上所佔的篇幅比例,卻遠遠不及那些如同猛獁像一樣古老的歷史事件。災難明明近在眼前,卻沒有人告訴孩童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關於戰爭的真相又是什麼。
我記得自己在那頁書上看到戰爭中的伊拉克兒童,穿著不能稱之為衣服的破爛褂子,抱著飯鍋,將撒到地上的米一粒粒撿起來,那副年輕稚嫩的苦相,卻幾乎承載了歷史上所有戰爭之痛的總和,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我已經忘了,當時老師是怎樣將那頁書上的痛苦一筆勾銷,進而引導孩子被刺痛的心靈,可以用仇恨美國這一方式進行安撫和治癒的。也許正因為如此,我才忘不了那張照片,忘不了戰爭中的兒童所遭受的貧困與飢餓,所以才不會去承接那種膝跳反射般的仇恨。
但那始終還是在閱讀歷史,年份很近的"標本",雖不至於像猛獁像一樣遙遠且難以想像,也僅僅是在閱讀。跨過山脈和平原到達的那個地方,並沒有真正到達。想像中與我們生活在同時代的伊拉克兒童,並沒有因為這樣對戰爭和災難的微弱感應而使我們心意相通,於是我們仍然活在相互錯位的時間中,想像遠處的戰爭,就如同想像另一個世界。
在有生之年可能會親眼目睹一場戰爭。這種想法伴隨著錯位但深刻的感應漸漸消失了,感覺像是一個最壞的詛咒,不願再隨身攜帶。即便到了青春期,希望世界毀滅、希望自己消失,也不會直接聯想到是因為戰爭,而是更加浪漫地,渴望諸如小行星撞地球、外星生物入侵之類的科幻童話,而千萬不能是戰爭,唯獨不能是戰爭——這個理由如此單薄而現實,它有鋒利的刀刃,冰冷的銃管,好像話還沒能說出口,詛咒就會輕易實現。
但戰爭還是來臨了,在恐慌與錯亂交織的時刻,也會深深地懷疑,這是否就是對孩童時期那個恐怖念頭的一種懲罰。但也於事無補了,改變不了此時此刻人類正在經歷戰爭的事實,不再是歷史中的猛獁象,也不再是感應微弱的錯位時空,那些有血有肉、在現實生活中和我們有過交集的普通人,正在經歷一場戰爭。
2022年2月24日,俄烏戰爭爆發了。俄羅斯作家柳德米拉·烏利茨卡婭在網上寫道: “我本以為生在二戰期間的我這一代人是幸運的,我們可以一生不經歷戰爭,直到'平和、沒有痛苦、沒有羞恥地'死去。不,看來並非如此。而且也不知道,這個戲劇性日子的各種事件最終會導致什麼結果。一個人和他忠誠幫兇的瘋狂行徑正主宰著整個國家的命運。痛苦、恐懼、羞恥——這就是今天的感受。”
但和我一樣成長起來的一代,被仇恨包裹卻無處可宣洩的一代,我們是如何面對這場戰爭的呢。當初網絡上流傳著眾多的"戰爭笑話",彷彿對新聞報導中噴湧的鮮血視若無睹。鼓吹戰爭的大有人在,人們談論戰爭,就好像談論一場球賽一樣疏鬆平常,而戰況就是各國所投入的努力和技巧,可以不帶任何道德判斷,像球賽解說員一樣輕易評說。
冷戰才結束不久後的1993年,彼時人們還沉浸在戰爭結束的喜悅之中,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貝格爾卻預言: “今天的殺人者很樂意接受采訪,媒體也很自豪能出現在殺戮發生的地方。內戰變成了一部電視連續劇。記者履行的只是他們的報導義務;他們向我們無情地展示著——正如他們所說——事態狀況是怎樣的,而評論員則貢獻著必要的憤怒。”
於是今天這場對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開始了,它不僅僅發生在兩個國家之間,而是像風暴一樣迅速席捲所有人類,道德的、不道德的,興奮的、悲傷的,暴力就這樣擺脫了束縛,奮力遊走在眾人之間。仇恨已經滲透到日常生活裡了,每個人都選擇與他人為敵。
但什麼時候起,我們不再談論戰爭了,在遠處屠殺持續不斷地發生,人們在挨餓,被驅逐,被折磨,被強姦,而我們卻袖手旁觀,什麼都不做,開始繼續過我們的日常生活,就好像是潔白無瑕的和平從未被破壞過。
過去人們對他們那個時代最嚴重的罪行所知甚少,或一無所知,殺戮被隱藏了起來。但如今戰爭卻發生在我們眼前,於是等同於目擊者的我們不得不面對那個無能為力的道德困境,在做出的事與展現在面前的事相背的時候,躊躇的心靈不知該往何處去。
人們暗自祈禱和平再次到來的一天,但也深知戰爭會不斷重現,不斷給平凡的人類帶來苦難。 《戰爭與和平》中安德烈的父親博爾孔斯基公爵與皮埃爾辯論,年輕的皮埃爾曾信誓旦旦地證明道:不再有戰爭的日子一定會到來。但博爾孔斯基卻帶著諷刺的口吻反駁他說: “把血管裡的血抽出來,都注上水,那時就不會再有戰爭了。”
那之後一語成讖,不論是皮埃爾還是安德烈,所有懷著純白夢想的人都飽受戰爭的折磨,一生皆葬送在一場戰爭之中,日後再成為歷史上微不足道的一筆,古老得如同孩童眼中驚奇的猛獁象。
也許正因為這樣,戰爭才一次次發生,它同時刻在興奮和悲傷兩種人的基因當中,於是有人發動戰爭,有人哭泣,世界在重複這種命運,人類歷史在重複它本身。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








- 來自作者
- 相關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