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昆德拉到阿倫特:翻譯中不可承受的平庸之惡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的英文標題是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雖然英文並非這本小說的首發語言,但其書名的結構與小說手稿所採用的捷克語(Nesnesitelná lehkost bytí)及首次出版時採用的法語(L'insoutenable légèreté de l'être)相同,因此從簡潔起見,下述討論將圍繞著中英文譯本展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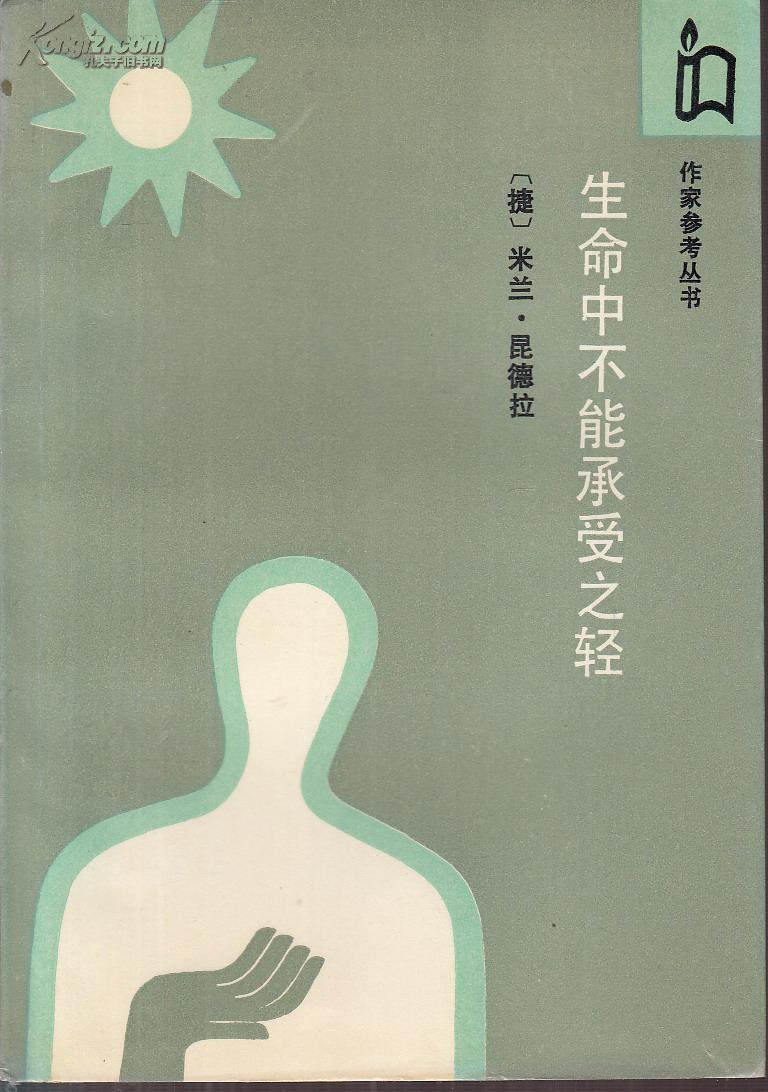
對中文較敏感的人不難發現,“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與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在結構上並不對應。這種不一致並不在於中譯把“of Being”提前變成了“生命中”;而在於“中”和“of”所暗示的邏輯關係不同。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暗示的是“不可承受之輕”是生命這個載體所承載的一種外在之物,彷彿如果作者願意,他完全可以再寫一本《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這裡輕與重的關係是平行的。然而無論是英文、法文還是捷克語,其語法所暗示的是,“不可承受之輕”是生命所具有的一種不可分割的屬性。在這個意義上,生命不再是一個承載輕與重的舞台,生命本身就是“輕”的,而這種輕讓人難以承受。
這一誤譯非常類似於中文對於福柯的誤讀。最典型的是福柯在用話語(discourse)這個詞討論權力關係時,尤其強調權力內嵌於話語之中,權力生產話語、話語內嵌權力。話語/權力並非任何個體所能獨有。可是當中文把discourse翻譯成話語權時,又默認它是一種供人爭奪的所有物或所有權。如“某某某沒有話語權……有實力才有話語權”之類表達,本身自然也有其意義,但與福柯的原意早已南轅北轍。類似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的譯法,也把Lightness當成了生命的一種所有物,而非其讓人無可奈何的本質屬性,從這個意義上,中譯似是而非地背離了原意。
在後來的中譯本中,也有人將標題改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相較於《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這種新譯法顯然更為貼近原文,因為“生命之輕”似已暗示“輕”這種屬性內嵌於生命的存在之中。不過美中不足的是,僅從中文的文法而言,“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輕”讀來似乎沒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那麼流暢,儘管它更為準確。這也是我不願苛責譯者的原因,翻譯之難,本質上是兩種語言的語法及其背後的文化、思維觀念不同構,“信”與“達”往往不能得兼,遑論“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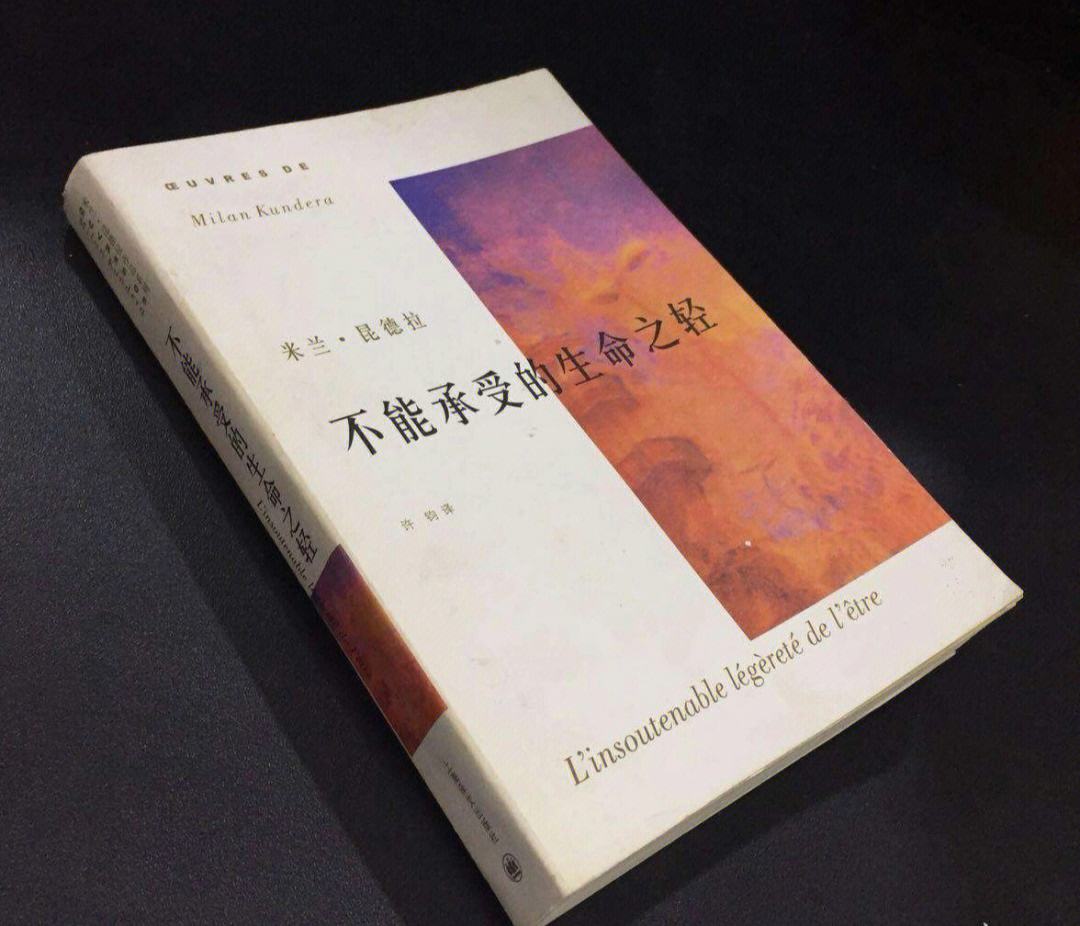
具體到這句話中,好的翻譯既要凸顯“生命”與“輕”不可分割的內在關聯,又要符合中文的語感將作為主語的“生命”前置,避免“生命之輕”這樣濃厚的翻譯腔。我的方案是只改一個字:
生命那不可承受之輕
雖然“主語+那”並非中文的主流文法,但作為一種帶有感懷性質的文學性表達也並不罕見。此外,“那”這個字暗示了“生命”與“不可承受之輕”是一種指涉而非從屬關係。不知道這個改動諸君是否認同,反正ChatGPT挺滿意的,它用英文對我的想法的複述似乎更為準確,特此貼在下方供大家評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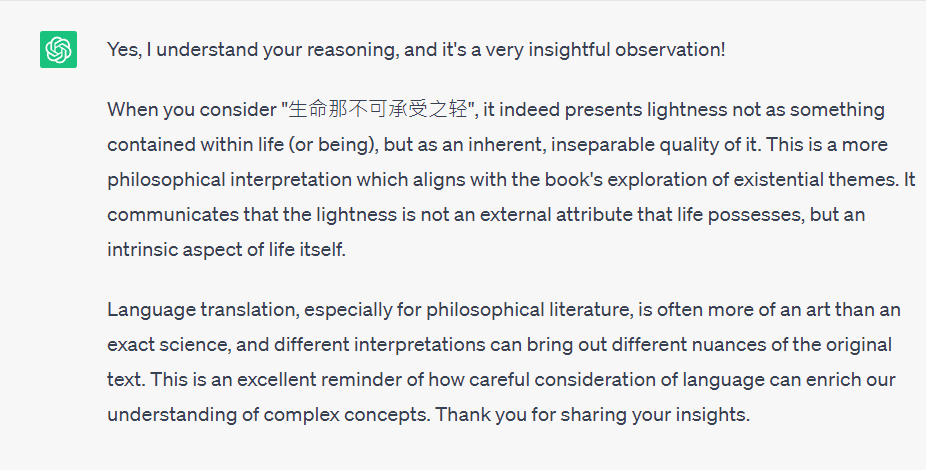
嚴格說來,即便“生命那不可承受之輕”也有待商榷,因為原文中的being是一個遠比生命更為抽象的概念,一般譯作“存在”。鑑於“存在”這一概念很大程度上也是舶來品,帶有濃厚的西哲味道,不如being對英文讀者那麼親切,因此我倒認同把抽象的being還原為具象的“生命”是一種必要的犧牲。對being這個詞的處理,提醒了我另一個典型、或許誤導性更強的人文名著的誤譯。即漢娜阿倫特的The Banality of Evil,中譯為《平庸之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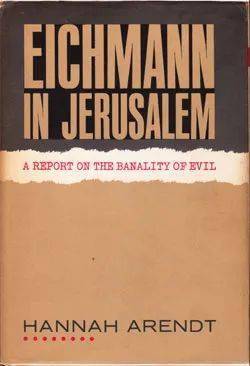
拜這個譯名所賜,中文互聯網大多數對於平庸之惡的引用幾乎都是望文生義的誤用,將之視為“平庸”本身所具有或帶來的一種惡。然而依照英文文法,作者所討論的實則是“惡的平庸性”,至於平庸這種品質本身是善是惡,是否會誘發惡行,與此書毫無關係。這本書的副標題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主角艾希曼是猶太大屠殺的納粹策劃人。但在阿倫特看來,他只是一個沉悶而普通的平庸官僚;艾希曼並不憎恨猶太人,只是不帶感情地試圖在納粹體制中向上爬,由此在不壞惡念的同時做出了歷史上最邪惡的事。
人們往往認為犯下惡行者,必然是希特勒一般惡魔化身的恐怖人物。然而艾希曼身上這種平庸與邪惡的反差,促使阿倫特提出了“惡的平庸性”這一論點,藉以警醒大眾盲從權威、放棄自我判斷力所可能導致的災難性後果。由此觀之,大部分訴諸“平庸是一種惡”的文章不過是藉阿倫特的權威繼續兜售那套“打破平庸”的雞血,抑或對“平庸者”的污名化。例如百度“平庸之惡”,就會出現下面這張圖,實屬望文生義、離題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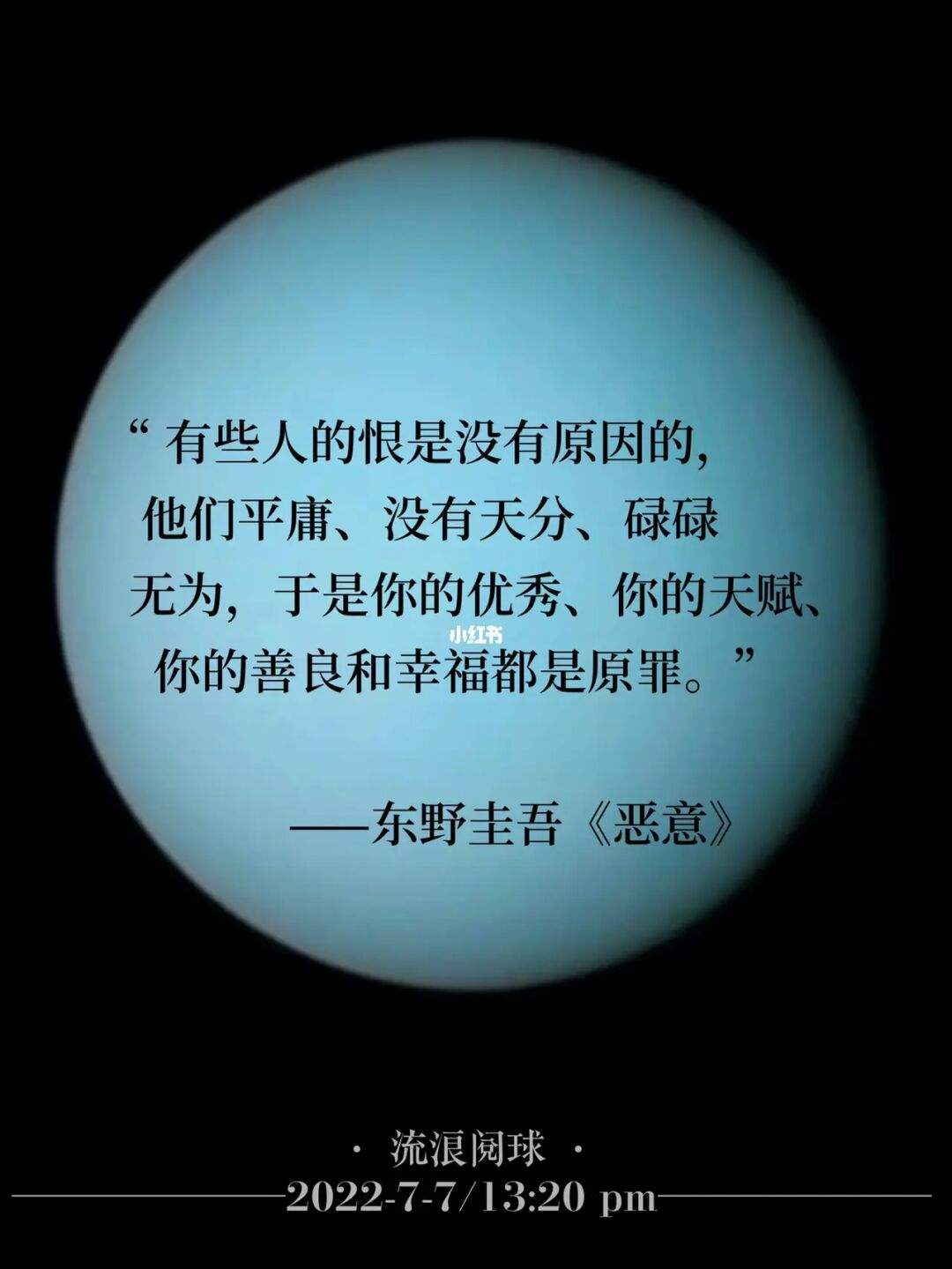
有人或許會問,The Banality of Evil遠比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簡潔直觀,為何譯者還是忽略了《惡的平庸性》這種顯而易見的譯法,而選擇了似是而非的《平庸之惡》?我認為根源還是在中文表達的習慣上。中文尤其是古文,相較於拼音文字而言,較為具象而缺乏形而上的本體論觀念。例如就構詞而言,中文以輕重表示weight,長短表示length,至於重量、長度這些詞都是現代文西化後的產物了。即便以輕重而言,輕與重也都是相對而言的概念,並沒有lightness這種類似於“輕性”之類本體論意義。原因也是顯而易見的,中文本身就不適合以ness、hood之類的詞綴來暗示一個詞從具像到抽象的變化。因此“惡的平庸性”雖然準確,但以中文的語感讀來總有些拗口,不如“平庸之惡”一般擲地有聲。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所謂白馬非馬。公孫龍的曾辯稱,假如他去買馬,那白馬、黑馬、黃馬都可以;但當他限定在白馬時,黃馬與黑馬就不能滿足要求了,可見白馬非馬。他的話術很容易用現代集合論的觀點反駁,即白馬屬於馬的範疇,白是馬的一種屬性。白馬縱然與馬不是等同的概念,也不能推出白馬不屬於馬這一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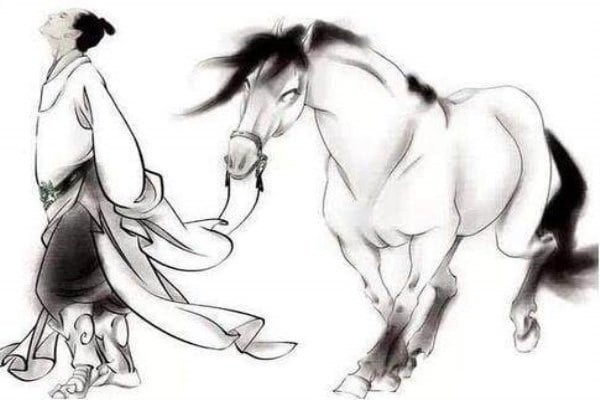
然而問題不在於如何駁倒這個幾千年前的詭辯,而在於思考為何這一辯術能在中文世界存在千年之久。我認為其核心還在於中文天然缺乏本體論的思維模式。如果就拼音文字而論,公孫龍或許根本不會產生白馬非馬的問題意識,因為他不會把horse與horsehood混同,即便他有心詭辯,觀眾也可以從語言層面指出這一顯而易見的區別。正是因為中文缺乏類似“馬性horsehood”這樣的本體論概念,白馬非馬才得以利用中文的多意性自圓其說。
同樣地,《平庸之惡》之所以成為流傳甚廣的誤譯,也是因為中文並不喜歡“平庸性”之類本體論式的表達。徜徉在中文之海,你我早已習慣平庸作為一種描述品性與行徑的形容詞,而難以思考“平庸性”的意義為何。這樣即便阿倫特探討的是惡的平庸性,大眾也難免把他從抽象層面拉入凡塵,理解為平庸的惡。這既是翻譯錯誤的教訓,也是一個深刻的例子,體現個人母語的文法特徵如何塑造其思維模式。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中文不能探討形而上與本體論問題,畢竟本文也是以中文寫就的;也不意味著在西方文化介入前,中國全無本體論的思考,如漢傳佛教、宋明理學都不乏相關探討。即便中文由於其書寫模式,不利於上述“平庸性”、“馬性”之類的思考,我也並不認為這是中文劣於其他語言的一種佐證。在我看來這些都是思維範式的差異,並無絕對的高下之分,語言的參差反而是人類思維多樣性的美妙所在。
不過,本文談的畢竟是翻譯,難免要在細微的區別間大費周章。昆德拉曾說,“歷史如同個人的生命一般不能承受地輕。輕若鴻毛、輕若飛揚的塵埃、輕若明日即將消散之物。” 翻譯某種意義上也輕地又如塵埃一般。完美的翻譯本就不可能,譯者尚需在不可能的空間中搭建一座搖搖欲墜的橋樑。更別說譯著最大的成就莫過於激發讀者閱讀原著的興趣,彷彿這座橋構建的目的就是為了其摧毀本身。
但這種自我否定的性質也正是翻譯的意義所在:好的翻譯把讀者渡向一個認知與思維迥異的彼岸,在讀者靠岸時應聲瓦解;平庸的翻譯則強化了讀者既有的認知,像一座堅固卻南轅北轍的路。如果能對外文著作中上述極易被中文表達所忽視或誤解的本體論層面加以仔細甄別,大概能夠避免這些翻譯的平庸之惡。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