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課筆記】David的〈馬拉之死〉:理性中的激情,政治宣傳的情緒渲染
本文寫於April 02, 2020,為台大歷史系花亦芬教授108–2開設之「藝術史與史學對話」課程筆記
“If art can make you happy, can it also make you good? If it can move you to ecstasy or tears, should it also move you to be a stand-up citizen? Can modern secular painting have the conversionary power of Christian masterpieces: the power to save souls, not from sin, but from selfishness? Ought the power of art lend itself to the art of power?” - The Power of Art, Simon Schama
“Ought the power of art lend itself to the art of power?”
生為台灣人,我們對於政治宣傳(propaganda)應該不那麼陌生。除了日治時期「警察」、「大東亞共榮圈」,小時候還在歷史課本上看了太多快樂農民圍著紅領巾的圖像,課文直白地告訴我們:這是共產黨的宣傳畫。有了警告,我看這些圖像時從未真的「被宣傳」,反而一直能抱著戒心辨識其中的符號。但是在藝術史課上,我第一次感覺到政治宣傳圖象的威力,其實非常強大。
那是在看法國新古典主義繪畫大家David的〈馬拉之死〉(The Death of Marat, 1793)的時候。我第一次看到〈馬拉之死〉還是在高中歷史課本上,講法國大革命的那章,在浴缸裡被暗殺的革命家。

我一直記得〈馬拉之死〉給我的第一印象:崇高、莊嚴、肅穆。那時候我對藝術還一竅不通,但從視覺得到的感動跟敬畏那麼直接,不需要理論多加闡述。馬拉的圖像旁邊,是課文對法國大革命的講解。我們(甚至是普世的一般看法)怎麼想像法國大革命?我覺得我們對它的印象還是比較正面的⋯⋯啟蒙、民主的精神,反抗封建下貴族的剝削,「自由平等博愛」。然後馬拉作為革命義士被呈現在那裡。
後來接觸了藝術史,從藝術風格而非歷史意義取徑,接近David這個畫家。上到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時,通常會把它跟啟蒙精神連接在一起。新古典主義出現之前,主導法國畫壇的繪畫風格是洛可可(Rococo)。社會組的高中歷史課本也有出現過Rococo代表作品 — — Fragonard的〈鞦韆〉。

Rococo畫作很好辨認,明快的氛圍、繁複裝飾、華麗衣裝、愉悅的人物、輕浮的動作(看〈鞦韆〉左下角偷看裙底的男子,就是這種)——基本上就是描繪貴族享樂。啟蒙精神提倡人權、理性,正是不滿當時放浪奢侈、道德放縱的貴族生活;而在繪畫方面,對洛可可的不滿最終成就了新古典主義。可以說,簡單樸實、要求美德的新古典主義,即為啟蒙思潮對18世紀法國社會所進行的全面批判中,批判繪畫(Rococo)的那一環。
新古典主義師法希臘羅馬時代的藝術品(希臘羅馬是「古典」,所以他們是「新古典」),背後更隱含對希臘/羅馬價值的高度讚揚。端正而均衡的姿態、崇高的道德、理性、勇氣,這些元素在David另一幅名畫〈荷拉提之誓〉(The Oath of the Horatii)裡一覽無遺。

〈荷拉提之誓〉背後的故事是這樣的:羅馬和異族打仗,雙方決定各派出三個勇士為代表決鬥。羅馬選出了Horatii家族的三兄弟(畫面左方並列的三名男子),和異族的Curiatii家族兄弟比試。比試的標準是戰到死為止,最後站著的是哪方的人,哪邊就贏了。然而這兩個家族其實是姻親 — — 畫作右邊哭泣的女人中,一個是嫁到Hortatii家的Curiatii女子,一個是即將嫁去Curiatii家的Horatii女兒;無論最後誰贏,她們不是失去兄弟就是失去丈夫。
在David筆下,Horatii家族的族長(父親)帶領三兄弟宣示付出性命戰鬥,他們身軀直立、表情堅定,體態健美強壯,和另一邊哭泣女人軟弱、蜷縮的姿勢產生極大的對比。兩邊沒有交集,男人和女人之間彷彿有一條界線。男性的勇敢捐軀代表愛國精神(again,這是羅馬德行的代表),女人則在角落為了家庭的破碎、為了「個人情感」哭泣。我們想起在啟蒙理論家的民主裡,公民資格依然是男性的特權,女人沒有足夠的理智/理性擔起好公民的職責(因為她們「困於私情罔顧大事」)。而這仍是從希臘時代流傳下來的規則(/常識/知識/⋯⋯myth?)。
然而,什麼是理性?理性是什麼?「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是理性嗎?或者「留得青山在」才是理性?為國家犧牲自我、犧牲家庭就是理性嗎?
當建立在理性上的啟蒙思想最終啟發了法國大革命時,驅動大革命的是什麼?是理性,還是激情?
而當大革命最後又變成雅各賓黨的恐怖統治時,人是被理性,還是被激情上了刑枷?斷頭台下的人頭是被理性決定所殺嗎?為了保護共和——「為了國家」——所有可疑的保守派、保皇派都得死。這是理性嗎?
其實死去的馬拉就是這樣一個殺人魔。他原本是記者,後來加入雅各賓黨,出版的報紙專門發布對保守派可疑人物的攻擊。他手握一長串可疑人物名單,一個個把他們送上斷頭台。David也是雅各賓黨人,甚至還是雅各賓黨的核心成員。David是簽名贊成處死路易十六的委員之一,儘管在不久前國王還是他的贊助者。在羅伯斯庇爾的統治之下,一些支持革命的舊貴族也難逃清算,接連被處決,其中不乏David過去親密的交往對象,但他對此毫不動搖。馬拉跟David這對好友是羅伯斯庇爾的左右手,每天致力於偵測共和的敵人,好把他們送上刑場。
死去的人越來越多,有人不免開始疑惑,革命走到這個樣子是正確的嗎?這是當初革命時想要實現的理想國家嗎?然而,對雅各賓黨統治的不滿,很容易就可以被解釋成包庇保守派,或者更糟:反革命。
某天,一個鄉下的貴族女孩Charlotte Corday終於受不了了。她支持革命,但不認為現在的革命還是她支持的那個革命。她藉口要提供馬拉一份可疑人士的名單,成功接近了在辦公的馬拉,然後刺殺了他——這就是「馬拉之死」。
所以,馬拉是烈士嗎?是革命的殉道者嗎?對雅各賓黨人來說,沒錯。他的死是顆震撼彈,因為對普遍法國大眾而言,馬拉也被看作共和國最可靠的守護者。Corday被大眾羞辱(an interesting point:他們試圖證明她不是處女,以作她道德淪喪的另一個證據),而馬拉的葬禮盛大舉行。哀痛的雅各賓黨人在聚會中要他們的同志、馬拉親密的朋友David畫一幅畫紀念國家的英雄,讓世人永遠記得他。
於是就有了〈馬拉之死〉。馬拉有嚴重的皮膚病,為了舒緩不適,一天要花很多時間泡在浴缸裡面。Corday刺殺他時,他也是在浴室裡辦公。在David畫作中,馬拉的形象是個完美的英雄,皮膚病不見蹤跡(西方藝術裡一向有理想化的傳統)。這幅場景向前來瞻仰英雄面容的民眾呼喊:「看,共和國最忠誠的公民馬拉,儘管在浴中都還在辦公(或者,儘管身體背負著病痛,也不眠不休地在為共和國的未來奮鬥) — — 而他就這樣死去了!他連死都是為了共和而死(畢竟,Corday正是以「共和國敵人的名單」為誘餌接近馬拉)。」
在這裡還要提一下畫作構圖的一些設計,馬拉被呈現的姿勢可以追溯到西方傳統宗教畫的一個主題「聖殤」(pietà),即耶穌之死。

浴室的裝潢被抹去,剩下一片黑暗,再次加強了非現實感,同時右上角一束光照下來⋯⋯基督教裡光跟神密可不分,例如教堂總是朝東等等。啟蒙之後,宗教被理性取代,但傳統符碼仍繼續留存。David用過去宗教的符碼,為新的宗教 — — 愛國主義?革命?共和? — — 畫出新的聖殤;在這裡,擔負了眾人之罪的是馬拉,救贖眾人的是馬拉。馬拉是聖人、不朽的共和之子。
這是不是一種政治宣傳呢?我覺得是(對了,David自己本身就擔任了雅各賓黨執政時「政宣部門」的首長)。David的政治宣傳至少對我很成功,因為在我知道這段歷史之前,我印象中的馬拉一直都是個為了革命犧牲的烈士——〈馬拉之死〉的圖像實在太動人。但現在我看到〈馬拉之死〉,會意識到自己的情緒反應是被刻意製造出來的。我意識到:我被圖像的崇高、莊嚴、肅穆感動了;我看到圖像,因而相信馬拉是個烈士;我把再現直接挪為現實。我被說服了,被宣傳了。
如果馬拉是烈士,那Corday是什麼?歷史要如何評價她、詮釋她?當馬拉的形象被David的畫作固定、流傳、成為不朽,Corday要如何為自己反駁?世界上多少人想到馬拉,會先想到David的畫作!David畫作的敘事當然不客觀,他作畫的動機就是要讓馬拉作為英雄永遠被人們傳頌。
(但是繪畫有客觀可言嗎?任何創作都好,裡面真的有客觀嗎?藝術能夠脫離現實存在嗎?能夠脫離政治存在嗎?藝術家在藝術家的身份之外,首先是活在這個世界裡的人。他的觀點,他的生活,決定了他如何選擇題材,重現題材。什麼被選中而什麼沒有,本身即已不公正。)
看看另一幅描繪馬拉刺殺事件的畫作。

這是Paul Baudry的版本(1861,我找不到統一的名字⋯⋯)。這幅畫裡,馬拉死亡的背景不再是神秘的虛空,而是人間的某個角落;牆上的書、翻倒的椅子,雜亂的樣貌和David畫中的井然有序正正相反。這次Corday才是主角:她站在法國地圖的前面 — — 為什麼?是代表她和法國人民站在一起?是全法國憤怒的化身?看這幅畫的人要如何詮釋它?這幅畫捕捉的瞬間,是兇手殺人後冷靜的樣貌,還是起身反抗暴政的勇者成功刺殺暴君?有趣的是,當女性被認為是軟弱的、無力勝任「公民」身份時,Corday不也是為了她的理想國甘願犧牲?她在出發刺殺馬拉前就寫好遺書,成功後也沒有逃跑,沒多久就被處決。這不就是〈荷拉提之誓〉讚頌的美德?
除此之外, Paul Baudry這幅畫還讓我想起聖經中寡婦Judith以美色誘惑入侵巴勒斯坦的亞述將軍Holofernes,並趁其酒醉將之斬首的典故。

自負、殺人無數的男人,誘惑的女人,血、死亡跟女人淡漠的面孔⋯⋯一切如此相似。善與惡、罪行與罪行交織在一起互為因果,我們看見了善還是惡?看見罪行還是義行?結果都是取決於故事怎麼說、誰來說。
寫了好長,最後想回到開頭引用的段落:
“If art can make you happy, can it also make you good? If it can move you to ecstasy or tears, should it also move you to be a stand-up citizen? Can modern secular painting have the conversionary power of Christian masterpieces: the power to save souls, not from sin, but from selfishness? Ought the power of art lend itself to the art of power?”
藝術能夠激起情緒,這點毋庸置疑。David的新古典主義繪畫,也許看上去是秩序、理性的,但他想激起的終歸還是激情 — — 〈荷拉提之誓〉要激起愛國心,為了國家,個人應不惜犧牲生命、犧牲小我的幸福生活;〈馬拉之死〉要激起悲憫、崇敬,要能在觀者心中建起馬拉的聖像。
但激情是危險的,群眾的激情尤其危險。政治宣傳正有這樣的力量,可以輕易的就種下民粹的種子。 “Can modern secular painting have the conversionary power of Christian masterpieces?” 若把政治理念化為聖訓,政治宣傳畫就像教堂裡的宗教畫一樣「教化」著我們,把我們變成信徒;告訴我們故事,但是以他們的敘事進行、以他們的版本為準。
那麼, “Ought the power of art lend itself to the art of power”?我反而好奇,藝術家真的有意識到自己正在 “lend the power of art to the art of power”嗎?如果他們真的都只是想use art to make you good 呢?只是一心的照自己所想畫出來呢?David或許真的相信Marat是個聖人、真的相信自己宣揚的價值⋯⋯所以說到底,這似乎不是應不應該,而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藝術家活在特定的意識形態裡,所以藝術(或者任何生產)總是在無意識中再製意識形態。
我們跳不出給定的框架,只能盡可能意識到這個框架而已⋯⋯而就不僅僅是藝術。倒不如說,這跟藝不藝術,就不是那麼有關了。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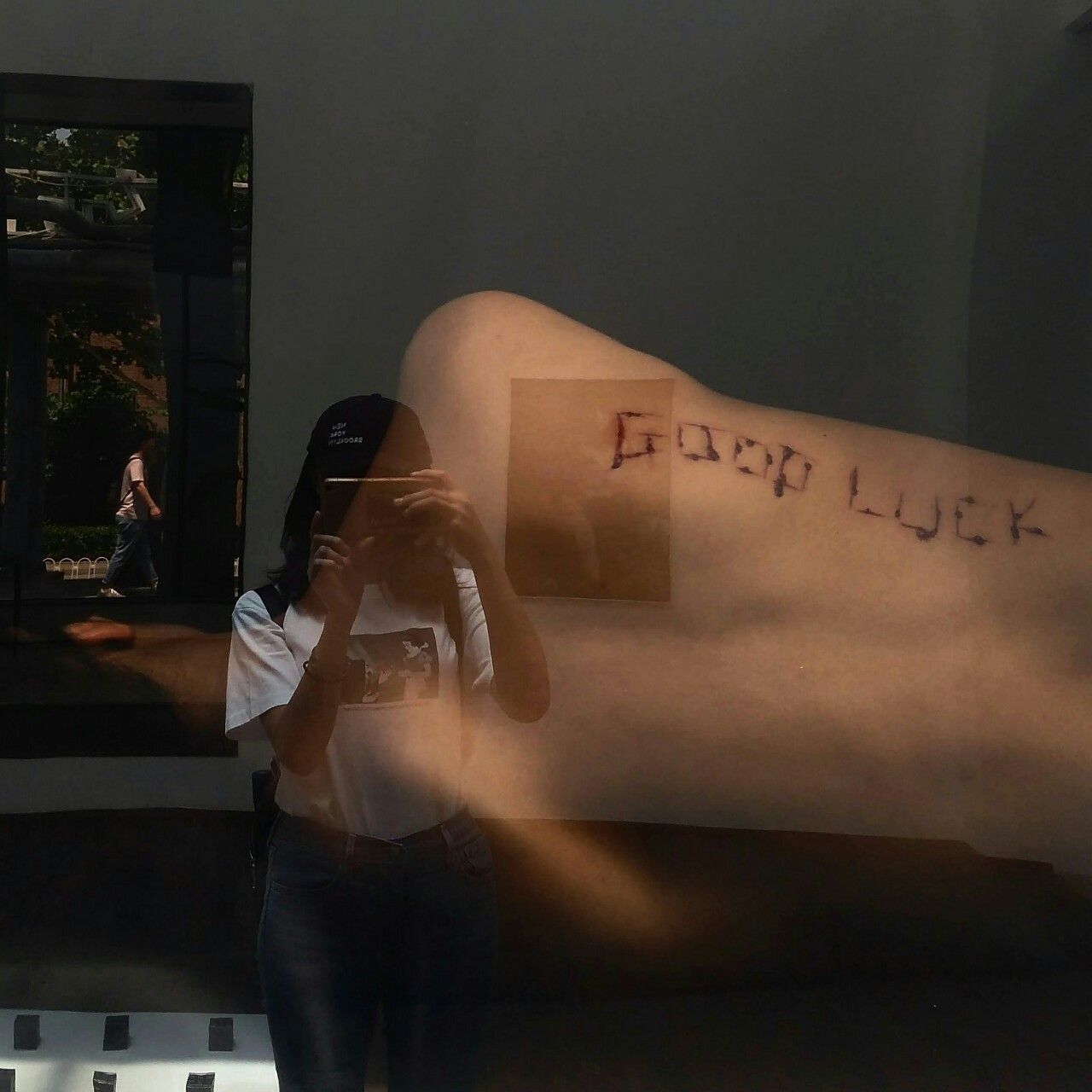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