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E 2024】救救孩子,要看見絕望以前的情緒警號——學童精神健康專題訪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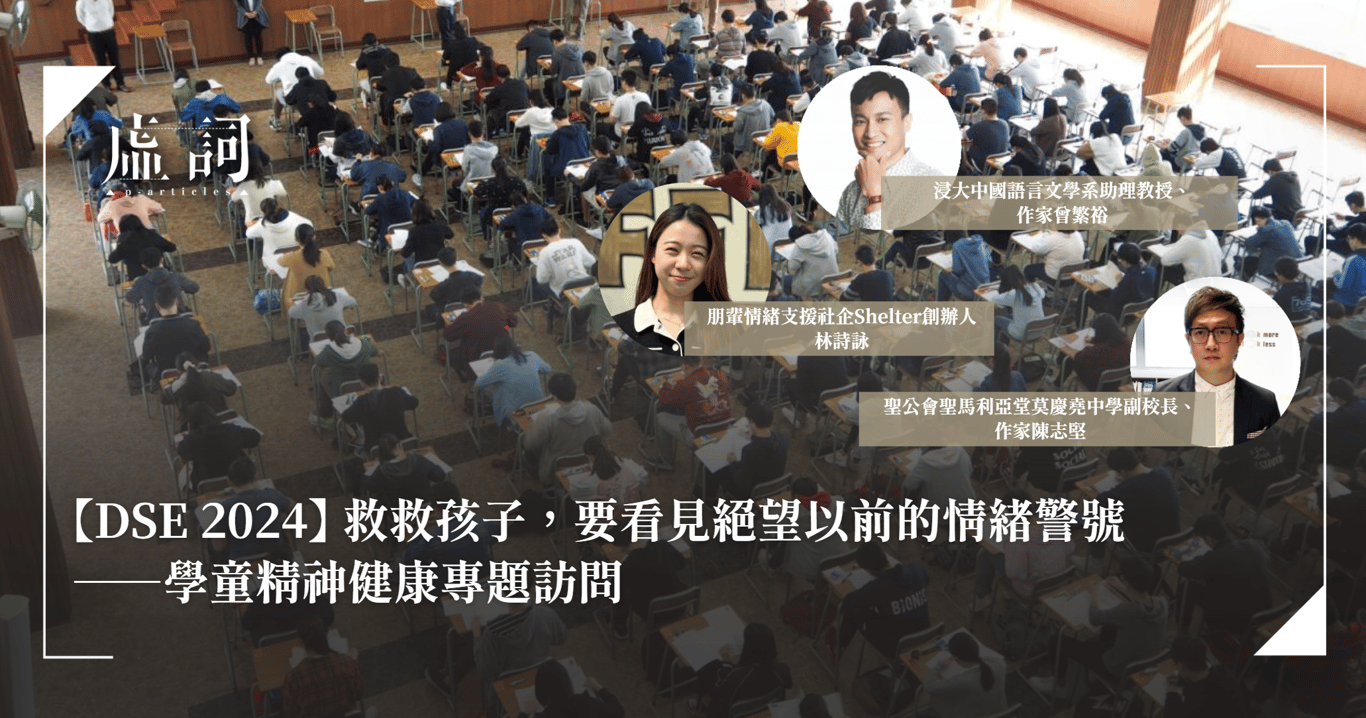
文|虛詞編輯部
去年電影《年少日記》,借學童自殺問題一再戳中社會的教育制度和精英主義,引起公眾關注學生情緒問題。遺憾的是,學童自殺輕生情況愈趨嚴峻,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於去年已錄得300宗以上企圖自殺及身亡個案學童輕生的呈報個案;根據中大醫學院有關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的調查發現,約四分之一學童在過去一年出現精神疾病,當中3.9%的學童過去一年曾有自殺念頭或行動;曾有區議員提及教育局並沒有備存學生懷疑自殺個案的病歷記錄,以及自殺成因的相關數據統計,可見教育局尚未予以適當的處理,對學童的心理狀況亦未有足夠研究。
毋庸置疑,學童壓力源頭之一是考試制度,為了大學學位、所謂的「理想人生」鬥個你死我活,因為無止境的試卷操練而叫苦連天,於是逐漸無力面對,甚或出現精神疾病警號,陷入情緒危機。適逢DSE開考在即,編輯部邀請到兩位教育界作家,分別為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副校長、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中國文學科目委員會前主席陳志堅,及浸大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曾繁裕,兩位以筆答形式,讓我們了解問題的普遍性,以至應對考試壓力的經驗和方法。
教育界以外,我們也訪問到朋輩情緒支援社企Shelter的創辦人林詩詠(細C),從社福界角度透視現時制度的缺口,以較近的距離認識學生的心理面向,藉此說起情緒健康的重要性。
在這個時代,新一代的成長至為關鍵,讓我們好好裝備自己,以同行者的姿態作陪伴,適時給予他人情緒支援,聆聽更多,讓學生表達自身,而不是說教、隨便拋下一句「加油」 作罷。在這吃人的教育制度下,救救孩子。
「生死戰」又如何?擁抱自我價值,探尋人生可能性——訪陳志堅副校長、曾繁裕老師
1. 在您與學生相處的經驗中,您認為學生受情緒困擾的情況是否普遍?您認為是甚麼原因造成這現象呢?

陳:中學生固然有中學生的煩惱,有中學生的難處,我們必須加以理解、聆聽心聲和給予更多的關懷,情緒人人皆有,無論是一般不開心或是受到情緒困擾,都要好好關懷學生的感受和需要。至於中學生面對的問題,無論學業、與人相處、家庭或個人志向是否能得到滿足,都是中學生所時常面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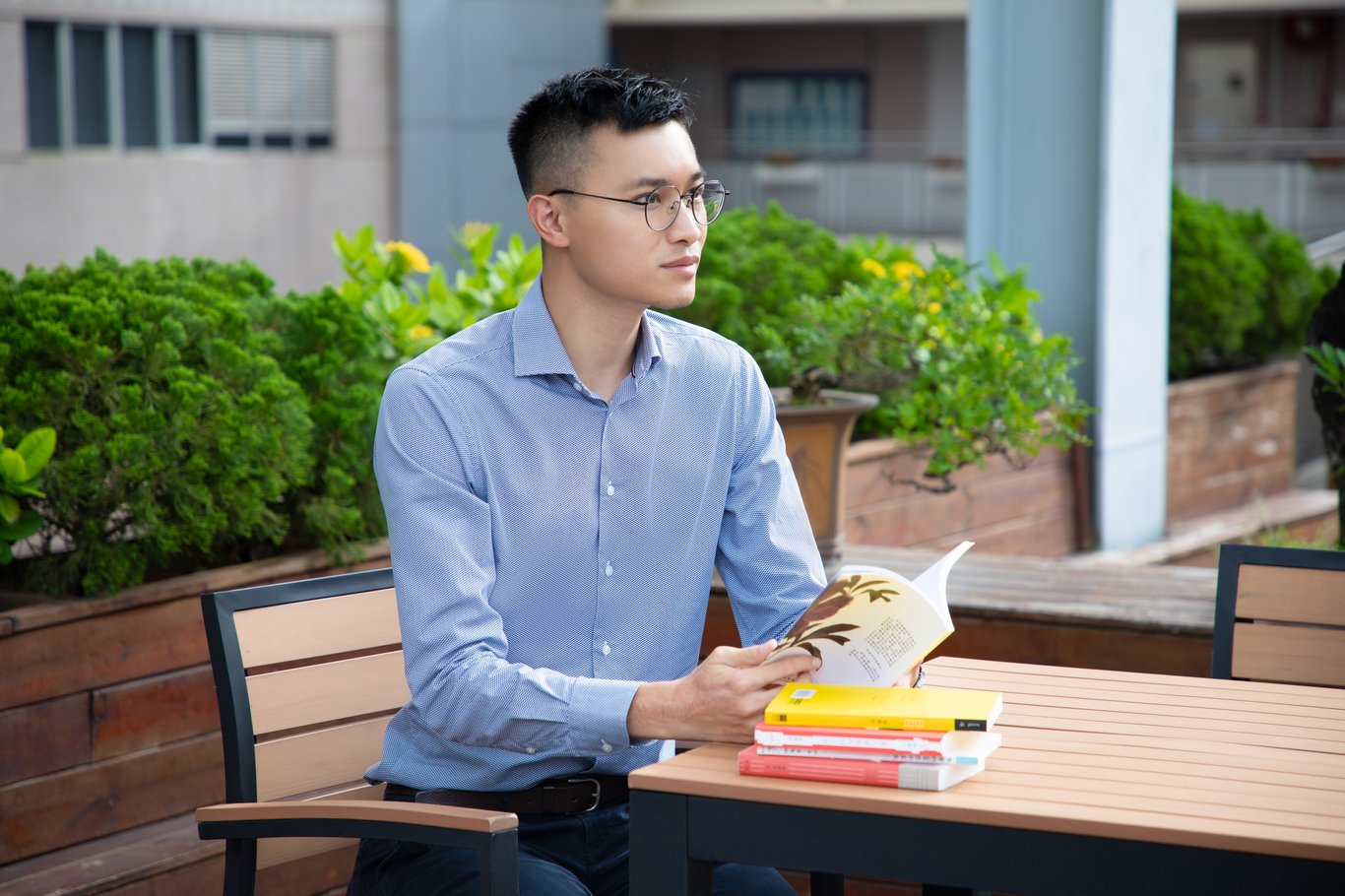
(曾繁裕在中學時期幾乎留班,會考成績唯中文科表現突出,令他發掘到自己的長處。如今既是作家,又是學者,更身兼教學與文學雜誌編輯工作,對香港教育大有反思。)
曾:學生受情緒困擾的情況很普遍,甚至常見抑鬱、焦慮等問題。原因有很多,可簡單分幾個方面:第一,父母關係不穩,以至子女在之間拉扯,即使穩定,教仔無牌考,往往過份催谷溺愛,或把責任外判給學校,子女難以適從;第二,手機霸權,既吸走父母的關愛,又讓學生難以專注,網絡世界外更冰冷,裡面則更易磨擦、衝突;第三,大眾文化使年輕一輩更重視自我和追夢,容易玻璃碎裂;第四,扣連主題,目標型社會使一切處於緊張的競爭狀態,學生無論升學、人際關係、將來求職乃至興趣,都彷如考試般面對重重功利計算,若未能成為少數的成功人士,就只能不斷內捲。
2. 有不少學生、家長認為DSE是一場「生死戰」,足可判定人生的成敗。作為教師,您如何理解考試的重要性?
陳:DSE是人生的其中一個階段,不是用來看判別整個人生的成敗。考試固然有重要性和意義,然而考試成績基於很多不同的因素,故此,不要將得失成敗看得過重。加上,現在很多升學途徑,一步步走來,將會發現有很多可能性。
曾:考試的重要性建基於快樂學習的反面,快樂學習重視無差別、興趣、共融和過程,若與他人比較學習進程和深度,只會適得其反,而考試則重視規範、評估、篩選和結果,倒模般迫使學生配置一式一樣的種種知識,再從中分別出能力出眾的人,享用有限的高階教育資源。考試制度一方面是資源限制以及專才社會下必需的,另一方面既代表社會對掌握必要知識的重視,又反映對學習動機的普遍不信。令人無奈的事實是,上流決定的社會不斷推舉「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而考試讓既得利益者更熱愛學習,讓中庸者努力到底,也讓被標籤為不合資格的人轉往其他領域,確實充分體現「效益」。
3. 對於應屆考生,您認為他們應以甚麼心態面對考試?您能否分享一些經驗或方法,鼓勵即將應考的同學呢?
陳: 一方面盡力而為,另方面以平常心面對。考試時遇有不懂作答的題目,可回憶關鍵概念作思考。如果真的不懂也要太擔心,因為DSE從來都不用取滿分,有些題目不懂是正常不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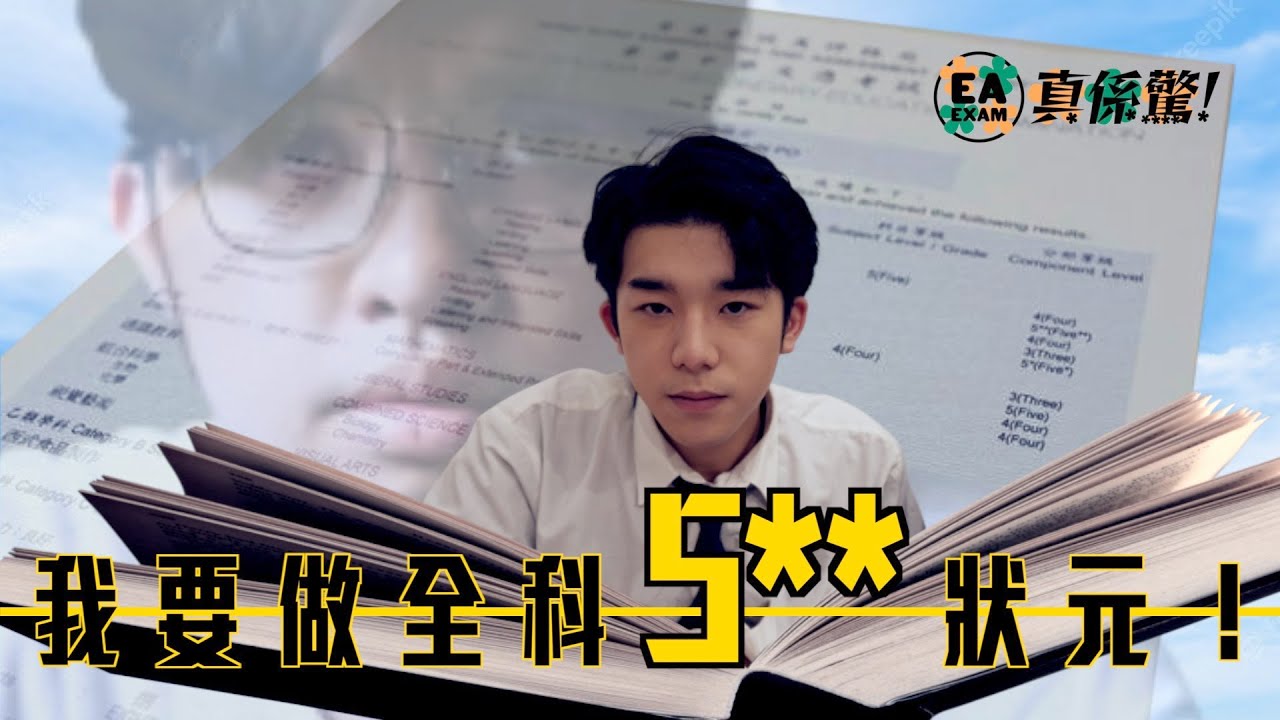
曾:心態千差萬別,結連許多複雜經驗和關係,難以一時三刻改變。簡而言之,緊張考試的人自會因為對自己的期望等各種原因緊張到底;不緊張的,除非像《試當真》替阿康拍真人show般賦予特殊動機,不然,也難改變。過來人的分享往往縮小現在,指將來回望的話,一定會覺得公開試只是件小事,但對於無法把眼光放遠的當局者而言,這沒有太大意義,因為此刻公開試就是擺在眼前最大的事,既然如此,倒不如擁抱自己的心態,不去否定和貶低這段人生經歷,好好珍惜,好好思考。抱歉有點灰,不過有時光機的話,我也會跟自己這樣說。
4. 作為作家,您在求學時期為甚麼會喜愛閱讀文學呢?有甚麼作品您會推薦學生閱讀,讓他們在學習或者準備考試之餘,同時可透過閱讀認識自我,獲取考試之外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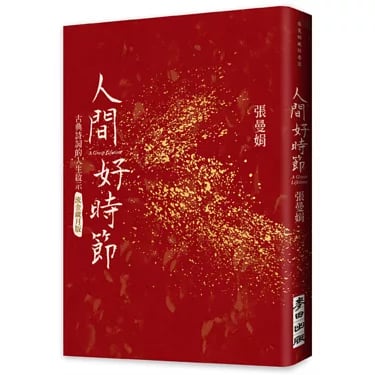
陳:喜歡文學,是因為文學可以抽離現有世界,作為情感出口,至回到真實世界,又發現世界原來有更多可能性。作品方面,推薦閱讀張曼娟《人間好時節》。無常是人生的本事,面對和處理生命種種固然是學問,其實世界本如是,某程度上只在乎我們的心態。張曼娟說﹕「發現自己的獨特,肯定存在的價值。」她又說﹕「不能預知的人生,是幸福的。」希望成為DSE考生的鼓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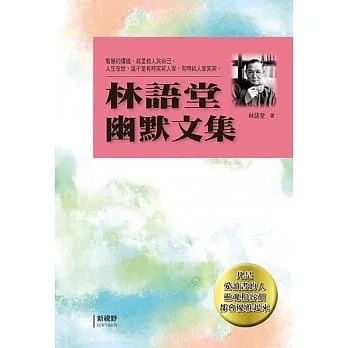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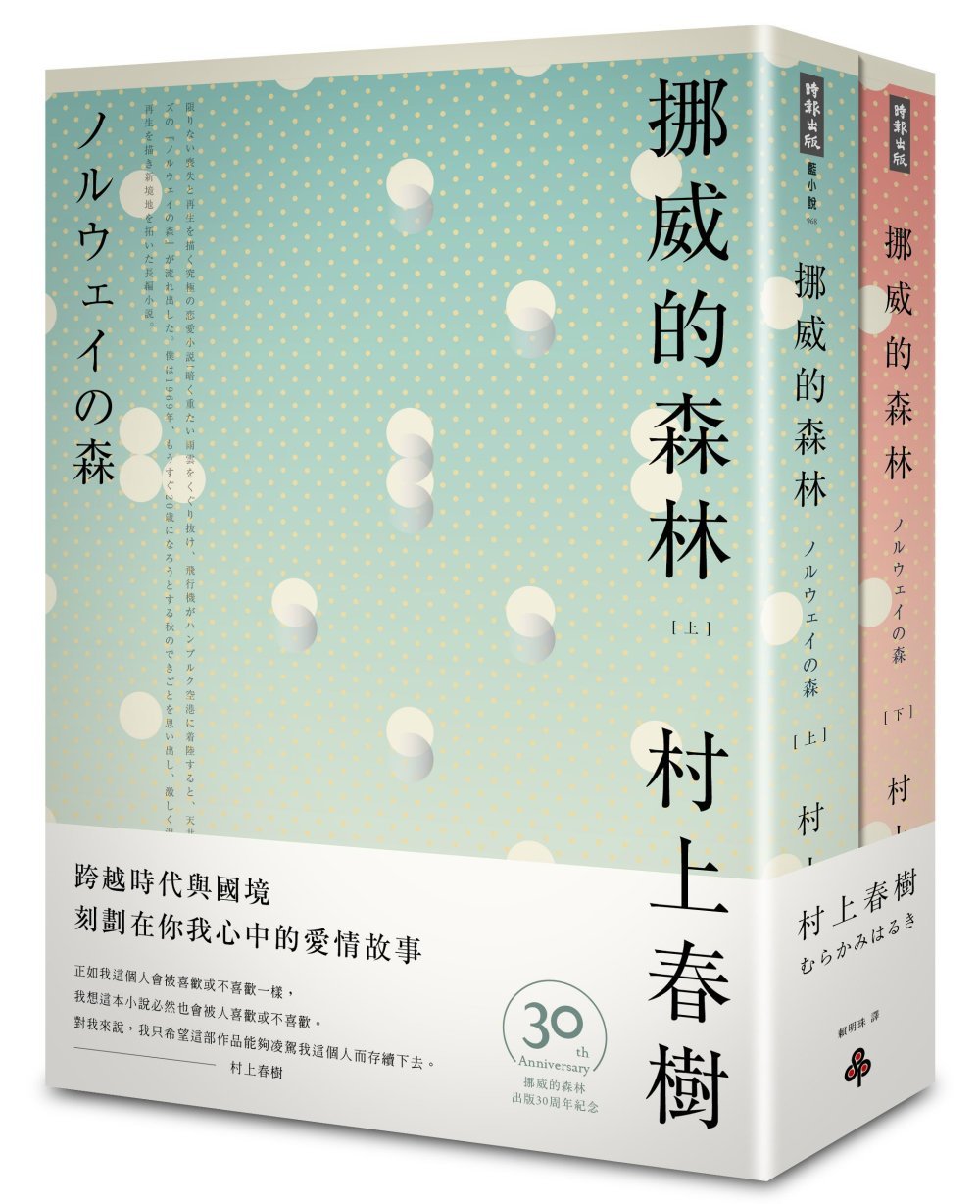
曾:求學時期之所以喜愛閱讀文學,除了因為文字世界本身的吸引力,也因為知識賦予的力量感。恐懼在於無法掌握,而閱讀文學能讓人摸清世界的肌膚和脈絡,心裡有數,繼而生活得更實在。當然文學有不同類型,有些使人看後鬱迫,需時消化,不利考試時的戰爭狀態。而選一些如林語堂的幽默小品、類型文學(愛情、推理、科幻之類)或語言難度較低的文學作品(如村上春樹和芥川龍之介的小說),則既不用過度燒腦,又可觸類旁通、想及人生。至於要對著屏幕的網絡文學,則暫時少看為妙。
去權威的同行者:情緒一井多源,豈能只救近火——訪朋輩情緒支援社企Shelter創辦人林詩詠

除了教育局的指引、社工、心理醫生以外,坊間可以如何幫助學童的精神健康?精神健康急救導師林詩詠(細C)兩年前創立了朋輩情緒支援社企Shelter,至今舉行四十場以上情緒健康分享會,細C甚至試過一個星期走八場,學校、社福機構、私人企業也會找他們分享經驗,一度證明情緒支援是整個社會迫切面對的問題。在學校講座裡,她分享自己躁鬱症的經歷,比權威性的社工來得更具說服力,達到去專業化的效果。到校講座以外,Shelter亦舉辦展覽、主題活動、工作坊,在社交媒體吸引學生和公眾一同參與。
說到學童壓力的源頭,細C認為有三:
一,大家向上流動的機會很少,或者前景不明朗,這些是由整個社會和政治環境構成。現在大家好像一潭死水,失去動力。
二,競爭太大,例如他運動很厲害想當運動員的話,先要條件是讀書好,變相很多責任和壓力不斷疊加上去。
三,科技發達令學生很早接觸到社會的真正面貌,這讓他們很難消化。就如出現老師的評價,甚至醜聞時,他們會驚覺以前認為有權威的人,如今已未必值得信任,繼而延伸至認為學校、網絡世界也不安全,遑論家境複雜的學生,就更無安身之處,失去傾訴的地方。
不要把我們的壓力全歸咎於考試
細C見證過不少應屆學生反覆入院,患上情緒病的學生更易出現惡性循環:踏入中六難以適應學校生活,於是發病而入住醫院。住院期間又難以集中應付學業,好像永遠追不上溫習進度,出院以後,要直面人生難題,壓力倍增而無法承受,結果是不斷入院,或經常出現自殺念頭。
中學的記憶其實並不遙遠,那時的她被認為是懂得自理的優秀學生,但躁鬱症已潛伏在內,「就算我經常哭,也沒有老師理我,到了大學的時候,才發現真的搞唔掂。」細C擔憂很多師長簡化了學生的壓力,DSE確是主因,但非唯一原因,「不能因為它的佔比較重,就能忽略家庭、人際關係、社會結構等問題。我很理解考試帶來的壓力,因為那是我們生命進程中的重大關口,是不容忽視的,所以我不能否定考試的重要性,但總不能單一簡化,說是壓力的唯一成因。我覺得現今社會只是不斷去處理DSE帶來的壓力,卻忽略長期因素。」由此,細C提出Shelter對付考試壓力的做法:若然考試佔了很大的生活比例,就盡量去擴大其他部分的比例,諸如家庭和朋友、讓他們開心的事,從而縮減考試的比例。
至於應試心態,細C表示難以界定,「每個人面對考試的心,都可以很不一樣,也沒有所謂應該不應該,而是我們要盡量讓他們感覺到,每人可以用不同的態度去面對難題,也讓他們意識到人生有很多可能性。」
補漏社會的情緒缺口 結構性問題有待解決
雖然Shelter竭力倡導情緒輔導,但細C終究認為Shelter的角色是被動的,說起來不免感到無力,「即使在講座看見有學生觸動落淚,我也沒有理由,沒有角色,沒有資源去接近他們。因為我們並非駐校,也不隸屬一間真正有專業輔導的機構,只有他們主動來找我們,我們才可以幫到手。」她再談他們的角色定位,「我們不能夠取締醫生和輔導員,但當你一個月只可以見到一次醫生或輔導員,其實剩餘的日子也需要支援,而我們就去補漏政府與專業機構之間的缺口。」
走訪多間學校後,細C發現嘗試情緒交流的學校為數不多,頂多就是有些社工來搞計劃,但有時只有經篩選的學生才能參加,像細C這些看似「妥當」的學生就接觸不到這些資源。反觀Shelter的功能,她指出安撫學生當下的情緒是他們的首要任務,「讓他們的壓力、不安、迷惘有地方抒發,但更根本的結構性問題始終非一朝一夕可以解決。」

Shelter最近籌備的「共學小組」正嘗試回應社會所忽略的長期因素,他們利用自身的社群優勢,集結熱心從事倡議工作、不同背景的成員,從不同角度討論和學習社會需要怎樣的精神健康服務,成員之間取長補短,可以多方位了解患者的真實面貌,例如發現精神健康與社會學、性別議題難以分割,去明白人如何成為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如此讓更多人裝備相關知識,逐漸增加情緒支援的供應。
我們要做幸福的薛西弗斯

關於推介書目,細C挑選了卡繆的《薛西弗斯的神話》,說是此書像埋下了種子,終有一日會發現世間有另一種看待事情的心態:「它很適合這個時代的年青人,這個世界好shit,但我們又要怎樣生存呢?怎樣消化這個世界荒謬的事?現在很常見到街頭塗鴉的字句,你會感到大家很頹,但頹得嚟又有樂觀,讀薛西弗斯也讓我有所同感。約莫那個年紀讀了之後,我開始意識到,我不能解決這個世界的荒謬——那麼,我不能夠改變客觀環境,唯有改變自己的主觀心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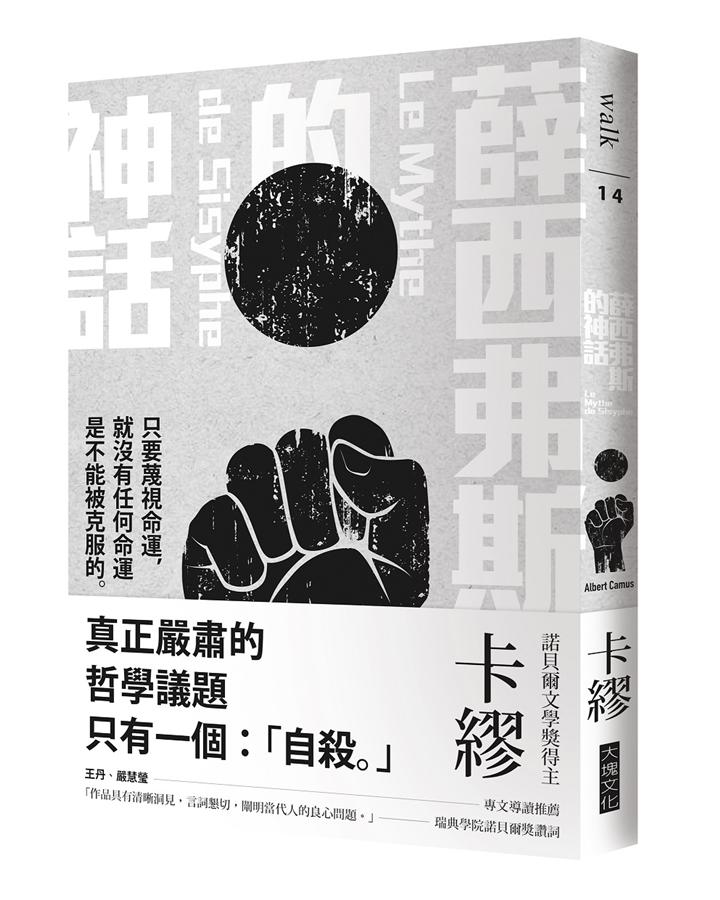
「我不想過於樂觀,但薛西弗斯帶給我一種悲觀中的樂觀。」倡議工作如是,她不希望採取正向心理學,「當我們想像自己是薛西弗斯,不斷推石頭上山的時候,我們要如何消化這個經歷?我患病的時候,不斷令自己相信它不是一個真正的苦難,嘗試超脫它,然後慢慢去轉化這些經歷。直到此刻,我發現原來過往的苦難,可以轉化成別人的燃料,幫助面對相同困難的青少年。 」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and clap, let me know that you are with me on the road of creation. Keep this enthusiasm toge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