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秘密結社、網路國家、火人祭、ZUZALU—對新政治社群的思考
秘密結社 、網路國家、火人祭、ZUZALU 等等:對新政治社群的思考
作者:Matt Prewitt 麥特.普利維特 CC-BY 4.0
August 22, 2023
Matt Prewitt 是激進改變基金會(RadicalxChange Foundation)的董事長,過去他曾是反壟斷和消費者集體訴訟律師,以及聯邦法庭的書記官,現在同時也是作家和區塊鏈產業顧問。本文經作者授權,以 CC-BY 4.0 形式翻譯釋出。
翻譯:豆泥 mashbean、Frank Hu、楊岱蓉 Tai-Jung Yang、Vivian Chen 、Liying Wang、鄧兆旻 Chao-Ming Teng、Beatrice Liao、Jiahe Lin 、Gimmy Chang
本翻譯群為 web3 for all 讀書會
社會學家喬治.齊美爾於1906年撰寫了一篇精彩的論文,名為《秘密與秘密結社的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Secrecy and Secret Societies)。這篇文章真的很難讀,句子冗長、且密度極高,該論文的英文翻譯版保留了古典學術德語的韻味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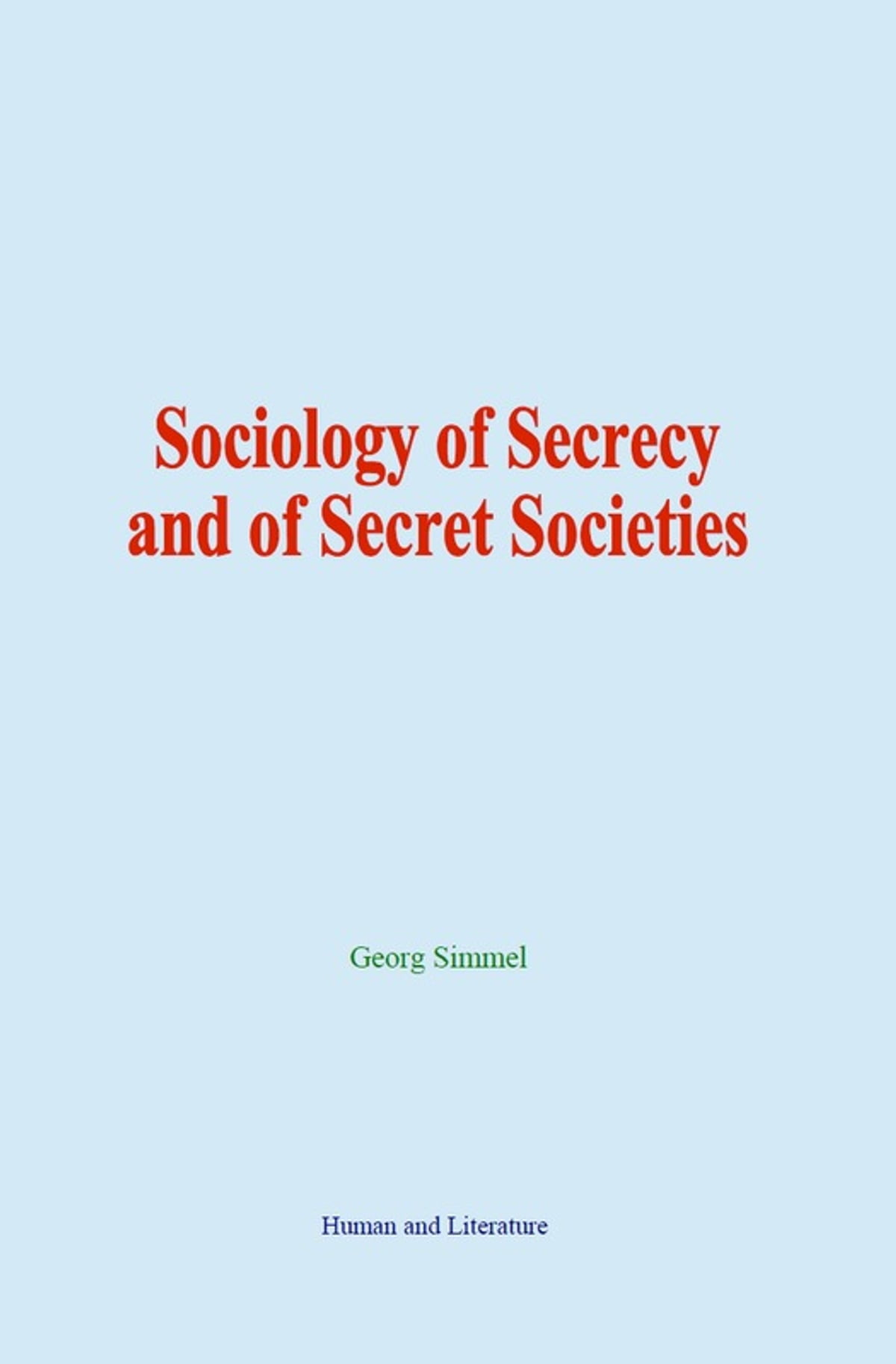
如果你仔細閱讀,你將加入一個小小群體,共享齊美爾對秘密在社會關係中的非凡洞察力,從友誼和婚姻到國家。齊美爾的讀者們大多互不相識,但這當中如果有任何人正在閱讀這篇文章,我邀請他們發電子郵件與我聯繫。一段有意義的關係可能於焉誕生,正如齊美爾所言,朋友之間共享的知識,雖非廣為人知,卻鞏固了許多最強烈的社會聯繫。
除了共享私有知識之外,強大的社群往往是命運共同體,彼此承諾或肩負共同的義務。承諾、義務和命數等等的,看起來令人覺得捉摸不定,難以量化,但它們確實可能是相關的,例如無擔保的信任和必須付出代價的分手。我們應更加重視此類指標,接著會討論更多。
最近,一股新的社群倡議浪潮正在蓬勃發展並且引起關注,如 Zuzalu、網路國家、Ezra Klein 的朋友們刻意建造的社群等。這些熱血的源頭可以追溯到火人祭還沒有出現之前的 20 世紀,如回歸自然運動(back-to-the-land),甚至更早以前 19 世紀的秘密教派和邪教。面對這些新嘗試我們應作如是觀?它們是否具備成功的條件?如果成功了,它們對世界是否有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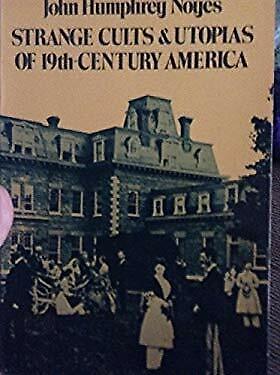
我們先從一些基本分類開始。大多數新運動,就像它們的前輩一樣,很難在政治上明確歸類。它們都是某種調整過的自由主義,但有些較為保守,其餘則極力於實踐進步自由主義。我發現可以大致將「新社群」倡議者分為三類,儘管他們經常混合出現,但可能並不總是認同彼此。
有共同價值觀的社群主義者(Affinity-communitarians)
在60年代和70年代,厭倦了主流社會某些方面(如資本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回歸自然者,希望生活在更小的社區中,與他們更相似的人一起生活。他們的後代今天仍然眾多。他們的背後的熱血與左派或右派無關:有共同價值觀的社群可以走向原始、傳統、部落、保守,也可以走向前衛、自由、進步。這很合理,因為與世隔絕可以促使人重回過去的傳統(不管這個傳統是真實或想像中的),當然也可以孕育新的進步或大膽踰矩的社會綜合體。這種社群都擁有具體的價值觀,並在主流社會以外蓬勃發展。
這可能會出什麼錯呢?
這種社群的計畫正當與否,完全取決於該群體相信的是什麼價值觀。他們很難維持團結,常常因內部政治而失敗:其中一個可能是變得教條主義和專制,另一種可能是分裂與不和諧。此外,當他們跟外界正式對抗的時候,往往容易被外界勢力直接壓垮。
個人主義的逃避者(Individualist-escapers)
這類人通常是自由放任主義者、無政府資本主義者和建造地下掩體的億萬富翁,他們希望斷絕依賴,超越社會義務。在這個類別中,我們看到人們試圖脫離社會主流,但並不一定創造出特別有條理或可定義的新社會。
這可能會出什麼錯呢?
只有原本的社會都已經不值得繼續生活,人們才有逃離現實的好理由。逃避現實的計劃往往悄悄地失敗,因為它們忽視了社群和社會的重要性,最後搞得事倍功半。然而,它們也可以偷偷地成功,因為它們看似不代表整個群體運動,所以一開始不會被注意到,最終在積極的情況下,緩和社群集體性的壓迫;或者在消極的情況下,削弱社會的規範牢籠,剪掉一條條宰制社會的文化束縛。
負責任的實驗者(Responsible Experimenters)
多年來,許多負責任的實驗者——例如那些務實的回歸自然者、(以色列的)吉布茲集體農場(kibbutzim)、托爾斯泰式農民(Tolstoyan farmers)等等——成功證明了新社會可以在適度的規模下形成。其中最好的一些還成功與外界建立了互利有效的相依關係。如今,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如何理解這種負責任的合作精神,並將其帶入數位時代。我們有理由抱有希望:因為 Zuzalu 聚集了一群多元的思想家,探討新的社會形式——當然不僅僅是天真的逃避者。此外,在知識界,即使是公開宣稱自己是自由主義者的人,最近也在主張一種有限度的、獨立於全球市場的的經濟模式。而 RadicalxChange 正在努力發展新的貨幣、財產和民主體系,以支援這些運動成功。
這可能會出什麼錯呢?
負責任的實驗總是一條狹窄的路,容易往兩邊撞牆。如何在全球單一文化中建立出口,而不陷入教條的、或不陷入排他的價值觀、或不陷入個人主義逃避的陷阱?要同時取得成功和做到好是很困難的。我認為,負責任需要承認這一點,並且優先選擇那些只取得小小成功,但高尚的計畫,而非那些取得巨大成功但錯得離譜的大作(參見:Facebook、德國另類選擇黨 AfD)。
在這篇短文中,我將探討新社群的概念。
首先:新社群如何與社會進步的概念相關聯?
第二點:有沒有可能像是建造橋樑和軟體一樣,有意地建立出新社群;或者它們只能在偶然的情況和/或歷史的長河中而湧現?如果是前者,該如何做到?它們要如何有效、有彈性地運作,並與世界其他地方保持負責任的關係?
接下來,我會提出幾則具體方案做結,這些方案是基於我的分析而提出的。
社會進步
「社會進步」(social progress)這個概念在知識文化中佔據了一個奇怪且稍微被邊緣化的位置。「社會的」這個形容詞就像一個提示,表示我們在這裡談論的不是統一的「進步」,也就是科學、技術或物質方面的進步。在衡量標準沒有共識的情況下,我們不知道怎麼樣才叫「社會進步」,所以在使用這個詞的時候保持謹慎是合理的。儘管我們對技術進步(或者色情)總能一望即知,我們卻未必能夠察覺到社會的進步。然而,這並不代表著社會進步不存在,只是很難達成共識,就像藝術或宗教一樣。但是,如果沒有社會進步,所有其他形式的進步最終都會失敗甚至退步。
哲學家與實踐倡議者丹尼爾.施馬赫滕伯格(Daniel Schmachtenberger)觀察到,當問及歷史上最早出現的「科技」時,大多數人會提到以下三項:石器、火和語言。這些重要的里程碑代表了人類早期便掌握了三種基本元素:物質、能量和資訊。但我們也許可以提出第四種最原始的,古希臘所說的「技藝」(techne),也就是人類文明早期就出現的敘事能力和智慧傳統,而這些當然與宗教和藝術有關。

這些技術對於人類合作的發展至關重要。也許光靠語言而沒有敘事,也能夠表達某些簡單的指令和基本實用的描述。但聆聽者與說話者,往往需要有共同的道德、法律或神聖感,才能夠理解真意和正確詮釋彼此。正是故事和藝術,以及它們融合成的智慧傳統和宗教,開創了擴展的社會凝聚力、共享價值觀且讓我們感受到更多不同可能性、合作的「我們」(註一)。
我岔開話題了,但主要觀點很簡單:社會凝聚力的驅動因素,如文化、治理、道德、法律、共享故事和共享價值觀,可以被視為「科技」。就像我們能操縱火、物質和資訊一樣,這些故事也維繫著我們彼此之間及我們和地球之間的關係。它們的狀態反映了我們的表現,文化的力量跟機械的力量一樣強。
事實上,任何特定科技領域(即人類操縱物質、能量或資訊的能力)的進步必須用另一種科技來衡量。例如,當我們敲擊燧石生火(能量)時,我們便能知道我們的石器(物質)是「有用的」。當我們看見引擎開始運轉以搬運重石(物質)時,我們便知道驅動它們的火源是有用的。當電腦的預測能夠幫助我們獲得更多物質或能量資源時,我們便知道我們的電腦(資訊)是有用的。
如果將文化、治理、法律、價值觀等視為科技,我們也能用它們來評估其他科技領域的進展。我們迫切需要這個額外的參考點來協助提升我們操控物質、能源和資訊的能力。
這個方式能幫助我們釐清創建新社群時所面臨的問題。我們應該要用同樣的熱情去欣賞並支持人們尋找新社群(也就是更明確且更好的故事)時所實踐的技術。如果我們在深化和擴展社群的技術方面沒有進展,所有其他技術進步將失去目標和方向,最終會陷入內外矛盾之中。更直白的說,我們將傷害自己和我們的環境。
在本文其餘的部分,我將分享一些重要的「模式」,我認為能幫助我們理解社群是否「有用」。無數個失敗的烏托邦因為誤解這些模式和其他事物而自取滅亡。這方面我們有很多可以向歷史學習。
一個關於連結社群的「模式語言」(Patten Language)
在1970年代,一群建築師寫了一本好書,名為《模式語言》(A Pattern Language)。此書描述了建築和城市的一些微小特徵,例如「門前的過渡空間」或「窗戶木工的圖案在某個時間點會在走廊上投下有趣的光影」。像這樣的想法幫助了許多建築師建造出美觀、溫暖、且具功能性的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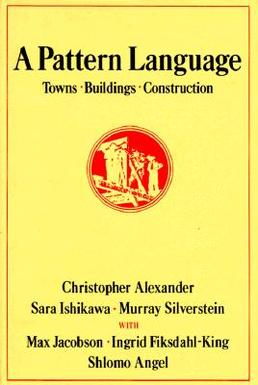
模式語言的概念幫助你描述一個過於複雜無法用任何全面性理論來描述的系統。你所能做的只是一些小小的觀察,希望其他人能夠有用地將它們拼湊在一起。本著這種精神,我來分享一些關於社群凝聚力和吸引力的觀察。
一、牽連的義務與共同命運 Associative Obligations and Shared Fate
社群的形成並非完全出於選擇。例如,我們並不能選擇我們的家庭,或者我們出生的環境,然而這些環境使我們成為特定社群的一部分。即使我們並未採取任何行動或是行使同意,這些社群通常也會歡迎我們,或者將我們視為其成員。有時即便我們並外主動要求,這些非自願的關聯性和未經要求的成員身份也會產生真正的道德義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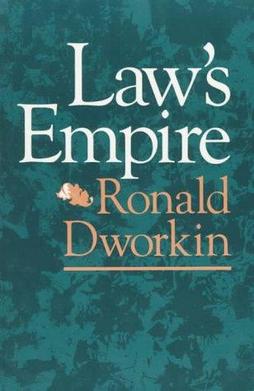
許多人對這些義務的概念持保留態度,至少在抽象層面上是可以理解的。某些被強制牽連的義務確實存在問題。例如,種族主義者可能僅僅因為某些人的外貌或祖籍,而單方面歡迎他們加入社群。這是否意味著這些人對種族主義者有某種忠誠或其他義務呢?絕對不是。許多其他具強制牽連義務的例子,雖然比上述的例子更無害,但卻是不連貫的:如果有人告訴你有一個社會全由和你同一天生日的人組成,然後聲稱你是其中的一員,這是否意味著你對這個群體有任何義務?同樣的,絕對沒有。你與那些碰巧和你共享生日的人沒有任何有意義的關聯性。
但這並不是因為義務必須總是遵循某種類似契約的「要約和承諾」(offer and acceptance)模式。更令人滿意的解釋是,一些社群,如「白人」或「12月15日出生的人」,根本無法構成有意義的社群。它們所組織的故事基本上是價值低劣的:邏輯上不一致,或道德上有問題,或兩者兼而有之。因此,它們無法為強制牽連的義務提供基礎。
但是許多其他牽連的群體並不完全無序或在道德上有問題:它們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是連貫的。如果我們否認所有強制牽連的義務的可能性,我們就否認了許多政治和社會群體的存在。
例如,假設有人對你好,因為你是他們的表親、鄰居、同事、同宗教信仰者、工會成員、隊友,甚至只是因為你也是人類。在相關的範疇內,並且在合理的程度上,你可能有義務回報這種特殊待遇,甚至可能要根據你被納入的類別來予以尊重。你的行為當然會極大地影響關係的深化或削弱,而這些行為也具有道德後果。但這種聯繫在某種程度上是在你沒有簽署任何合約或做出任何肯定的情況下開始的。
當人們彼此給予特殊待遇時,社群關係會更加深化。當這種特殊待遇是基於一個好的故事,或許是在邏輯上有意義,且道德上被牽連在一起時,回報這種待遇成為社交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並不是一個機械式的契約過程。我們並不能完全控制我們社群成員的身份,這是可以接受的。
二、杜威式的公眾 Deweyan Publics
約翰.杜威(John Dewey)認為「公眾」或政治社群是為回應共同問題而形成的事物。例如,如果一個城鎮中的一家工廠開始污染環境,為了共同管理污染,將使人集結成一個「公眾」來應對這個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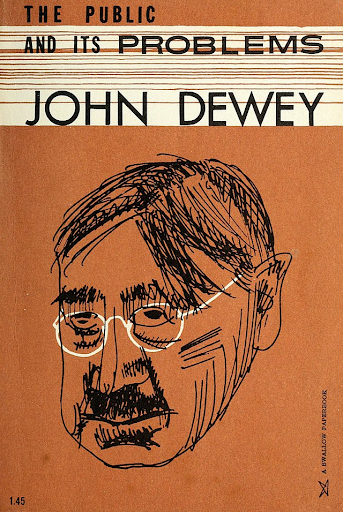
他明白在現代社會中,由工業化帶來的超複雜問題使得政治社群很難辨識自己。其所面對的問題通常太過分散或抽象,使人難以輕易組織起來與之對抗。然而,打造民主社會的工作即是傳播足夠的資訊和教育,讓公眾能夠自我辨識。因此,關於公眾問題的資訊必須廣泛可得,而在組織一個社會去對抗問題的過程中,在地的面對面互動至關重要。
三、保密和信任 Secrecy and Trust
社群常常圍繞著「共享的秘密」形成,或者換句話說:「特殊的知識」。這些知識可以是文化、語言、科學、宗教或其他任何事物。社群通過使用和保護這些知識來定義自己。
一個社群的特殊知識可能是一種秘密語言,讓其成員能夠在內部有效且具體地溝通。或者它可能是一種宗教教義,就像德魯伊(Druid)入門者必須花費多年時間記憶的神聖詩歌。甚至可能是相互勒索:犯罪集團的成員根本是被彼此綁架,任何一個人都可以透過揭露他們所知的來毀滅其他人。
當一個社群的特殊知識被外部揭露,或者被記錄在一些公開物件中(例如文本)中時,這將稀釋社群的凝聚力或對彼此的仰賴程度。齊美爾舉例說,德魯伊人被禁止將神聖詩歌寫下來,因為如果這些神聖詩歌歌曲被紀載在公開的文本中,較年輕的新成員要理解教義,就不再需要依賴長者的教誨,從而削弱了智慧傳統中固有的親密社會性。著名人類學家泰德.斯特雷洛(Ted Strehlow)因為曾經公開了某些原本應該以文化機密來保護的(澳洲)原住民歌曲和資料而一直受到爭議。如今,維基百科和 ChatGPT 使師生之間的連結變得薄弱:老師不再享有對資訊的特殊獨佔優勢,甚至喪失傳遞資訊的能力,從而對學生來說不像個老師,反而更像個監工。
在最強烈且最親密的私人關係中,通常假定互相具有保密義務,並且往往以無需附加擔保的信任基礎來進行協議。相比之下,在公共生活中,很少假定負有保密義務,並且通常要求具體保證。公眾要求透明,其實反映了公眾預設掌權者總是圖謀不軌:透明是為了打破掌權者彼此交換祕密的「密室」,防止這些掌權者形成「小圈圈」,然後作出背離整個群體的決策。
某程度來說,社群與其週遭環境之間的資訊障礙強度,指涉該社群在多大意義上真正構成了一個有凝聚力的社群,而與其週遭環境有所區別。甚至在個體層次上也能看到這個模式:一個可以被完全摸透在想什麼的人,也因此完全能夠被操縱,從而可能缺乏自主性和對自身行為的責任感。
這個模式對社群建立與加密技術(包括公共區塊鏈、零知識證明(ZKP)和其他強化隱私技術、以及指定驗證者簽名(designated verifier signatures))二者之間的相互影響具有重要意涵。
四、退出成本 Exit Costs
正如我上面所說的,具有關聯性的義務有時可能是單方面或非自願產生的。但事實上,它們只有在人們長期互相相濡以沫,建立深交、並產生重大的道德義務關係時,才能充分展現出來。
假設你要跟一個熟識的人建立更親密的關係,你跟他什麼時候建立起「友誼」的呢?是第二次回電話,還是一起度過第五個年頭的家庭假期?答案肯定是介於中間某處,但並沒有明確的界線,每一個友善的行為只會加深關係。隨著關係的加深,人們逐漸意識到因關係而產生的義務。而這就是關鍵:如果「放棄」這段關係的「代價」更高,人們更有可能吞下這些義務。
因此,最深厚的關係和最強大的社群往往是患難見真情。相較於承平時期,如果兩個村民在饑荒中沒有選擇,只能緊密合作以求生存,他們之間很可能會發展出深厚的友誼,如國家民意在戰爭中變得同仇敵愾等等。
商業環境也有類似的結果,當邊界完全開放,且資本能夠通行無阻,建立信任的可能性就較低。人們在商言商時,就比較沒有理由去投資這些人情世故。
低的「退出成本」使社群更難深化和成熟。
五、相互示弱 Mutual Vulnerability
因此可以說,上述所有模式都指向一個主題:相互示弱。藉由有意義的關係、分享秘密、面對共同問題和親密連結,人們變得容易受到彼此的傷害。
脆弱讓社會凝聚力成為一把雙刃劍。如果我們試圖將相互示弱當作社會組織中的一個變量,並且「充分利用」或擴大它,我們可能確實增加了凝聚力,但同時也可能增加了脆弱性或風險。
區分不同的相互示弱模式可能是有用的。例如,脆弱性可以是對稱的或非對稱的;一對多、全對全或部分對部分。甚至可能是循環的,例如,A對B脆弱,B對C脆弱,C對A脆弱。
所有這些模式都值得進一步研究。相互示弱在凝聚群體中的作用似乎非常重要。例如,當每個人都清楚地理解,任何人對規範的不尊重,都會對每個人造成災難時,就可能會形成一個願意尊重共同規範的文化。。
實驗:以無擔保的信任,種下關係
以上這些模式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資訊科技進展會削弱社群。開放的金錢和資訊網絡降低了地方組織的重要性,破壞了保密性,減弱了相互示弱的依賴,並且讓退出社群變得容易。這就是包括齊美爾在內的社會學家自工業革命以來一直研究的原子化現象。問題並未減少,反而加劇,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種趨勢會停止。
我對此感到擔心,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新社群的倡議很有趣且重要。它們不能重蹈覆轍,它們應該像科技專家一樣,吸取過去失敗的教訓,根據過去的成功基礎建立新事物。
前述的模式暗示了一些「負責任的實驗者」在改善社群建設技巧方面,可能會採取的方向。本著這種精神,以下是兩個具體的實驗,我認為它們是合理且有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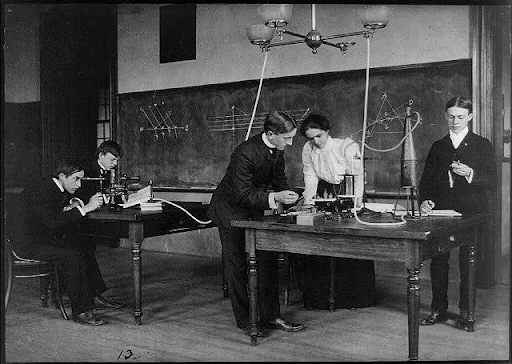
無擔保的信任網絡(Unsecured trust networks)
區塊鏈承諾藉由「去信任」來擴大合作。但有沒有可能這完全搞錯了呢?反而我們要問的是,我們是否有辦法設計一些方式鼓勵更深層次的信任,並利用它呢?來、想像一個建立在信任和財務上相互示弱的社會,大致如下。幾個人將一筆錢存入共同帳戶。他們每個人都有能力親自提取並聲稱整筆錢是自己的。如果有人拿走錢,沒有任何措施會阻止他,事後也不會對他採取法律行動。然而,所有人都清楚這麼做將嚴重背叛彼此的信任。
這個社群可以共同管理財富,例如投資股票、房地產等,並分享收益。(就連共享的非現金資產也可以輕易被社群中的任何個體拿走;例如,任何成員都可以合法聲明這個社群的投資為其個人財產。)
此外,社群可以發行一種內部貨幣(internal currency),該貨幣對應每位成員為該群體所貢獻的傳統貨幣或資產的數量。
由於這個系統相互示弱,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地欺騙其他人,內部經濟很可能會意外地高效且產生合作。我懷疑不會有參與者會去討價還價或在日常交易中作弊。如果他們真的想做這些事情,他們大可以直接帶走整個社群的資產。此外,彼此欺騙會增加他們帶走群體資產的可能性。社群貨幣和內部經濟創造的剩餘價值將由社群的互信而增強(甚至可能是超線性增長)。
這樣的系統創造財富的方式,跟銀行採取的部分準備金貸款很類似,但更值得採用。畢竟,銀行貸款也是透過信任或「信用」創造新的貨幣,但這是仰賴銀行的擔保進行獨立的交易。然而社群不需要靠銀行,而是可以選擇根據自己共享的資產發行額外的社群貨幣,同時保持這些資產有益投資。社群因此可以創造新財富,其價值有多高,端看社群內部的信任、尊重和合作程度有多高。認真履行義務,對內部經濟做出貢獻的社群,將會看到他們特殊貨幣的價值能兌換更多法幣。
這些社群的規模可以逐漸且謹慎地增加。它們可能從一些相互熟悉的人開始,逐一審慎地接納新成員。此外,或者可以設定每位成員能夠「偷取」共享資金的「上限」,從而有另一種途徑可以擴大規模。例如,可能讓每位成員能夠拿走的額度,是他們投入的2倍、5倍或10倍,但再多就不行了。這樣一來便可以建立更大的團體,而不需要每個人都對最薄弱的連結投以過度的信任。這樣更大團體可以透過謹慎增加成員能夠「偷取」的金額來「深化」,這反映的是更深層次的信任,而非更廣泛的信任。
這留下了許多問題。以這種方式建立的社群不會自動展現我前述的所有相關模式。這個社群要蓬勃發展,不能只靠彼此在財務上相互示弱,還需要在文化上建立共同的基礎。還有一些重要問題,例如如何處理「對財庫擠兌」(runs on the treasury),這在任何金融系統中都會時常發生。然而,這種有意識地將利益交織在一起的方式,可能會開啟深化社群和增加社會及財務安全性的新可能。
另一個也很有趣的事情是,一般而言我們會認為,在沒有保證的情況下,有錢人比窮人更沒有意願彼此信任。但我懷疑有錢人無法彼此信任的真正原因,其實是因為擁有的財富太多,無法對彼此示弱。因此,這些系統可能有望讓社群達成某種平衡,因為貧困的社群比富裕的社群更能夠利用彼此的脆弱性。
另一個稍微不太確定的實驗性想法。(我猜已經有類似的東西存在,請幫助我瞭解更多):
猜拳式權威結構(Circular Formal Authority Structures):這種模式尚未被充分探索,但可能可以幫助已經磨耗嚴重的非正式規範,在文化背景中重新建立典範。
假設有一個「A→B→C→A」形式的權威結構。這與「制衡」概念有關,但更具體來說:我們在這裡談論的不是全盤影響或多方否決,而是一個系統,其中每個行動者可以被另一個人在迴圈中獎勵或譴責。想像一個由三個成員組成的團隊,坐在一張桌子周圍,一起做一份工作,但每個成員決定他們左邊那位的薪水。
它有點像一座「紙牌屋」,循環權威結構的效力明顯取決於成員之間的非正式規範。因此,非正式規範可能有非常好的機會來獲得力量。系統中的所有參與者可能會一起努力發展合理的規範,並認真對待它們。
這對我來說很有趣,因非正式規範通常只在具有深厚共同歷史或強烈威權的體制中,才具有真正的力量。然而非正式的規範非常重要,但民主社會中許多機構似乎對此視而不見。這就是為什麼對於在缺乏(a)或(b)的情況下,建構循環權威結構進行實驗似乎是一種有趣的方式。
結論
建立新社群是困難的。而且要以對參與者和整個社會負責任、誠實且有生產力的方式建立新社群是更加困難。
但我不覺得有辦法繞過這些事情。相對於我們操控物質、能源和資訊操控的技術,我們在建構社會凝聚力方面的技術嚴重落後。因此,要麼我們摧毀機器(不太可能),要麼機器將會破壞社會(恐怕真的會實現),不然就是我們需要更有意識地讓社會更強健。
我提出了一些我認為值得實驗的想法。如果你同意,請聯絡我,我們來一起努力實踐。
非常感謝 Paula Berman、Jack Henderson、Angela Corpus、Alex Randaccio 和 Christopher Kulendran Thomas 對這篇文章的建議、討論和貢獻的想法。
註解
如果這三種東西對應到三個古典元素——土、火和風——那第四個元素是什麼呢?請容我想像為「水」。這是一個生成般的隱喻:水帶來連貫和再生,並維持生命。它保護著大地,大地連結並支撐我們的身體,我們同時對其負有責任,水也讓我們免受太陽的攻擊。它改變自己的相態來緩衝過度的能量。直覺上,水在能量增加時會自發形成有序的結構,但其實正好相反。當水蒸氣冷卻時,首先凝結成液體,然後結晶成冰。如此一來水可以隨時準備好發揮它的保護作用。水讓其他元素保持和諧。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and clap, let me know that you are with me on the road of creation. Keep this enthusiasm toge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