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學與女性經驗:讀 Hope Jahren 的 Lab Gir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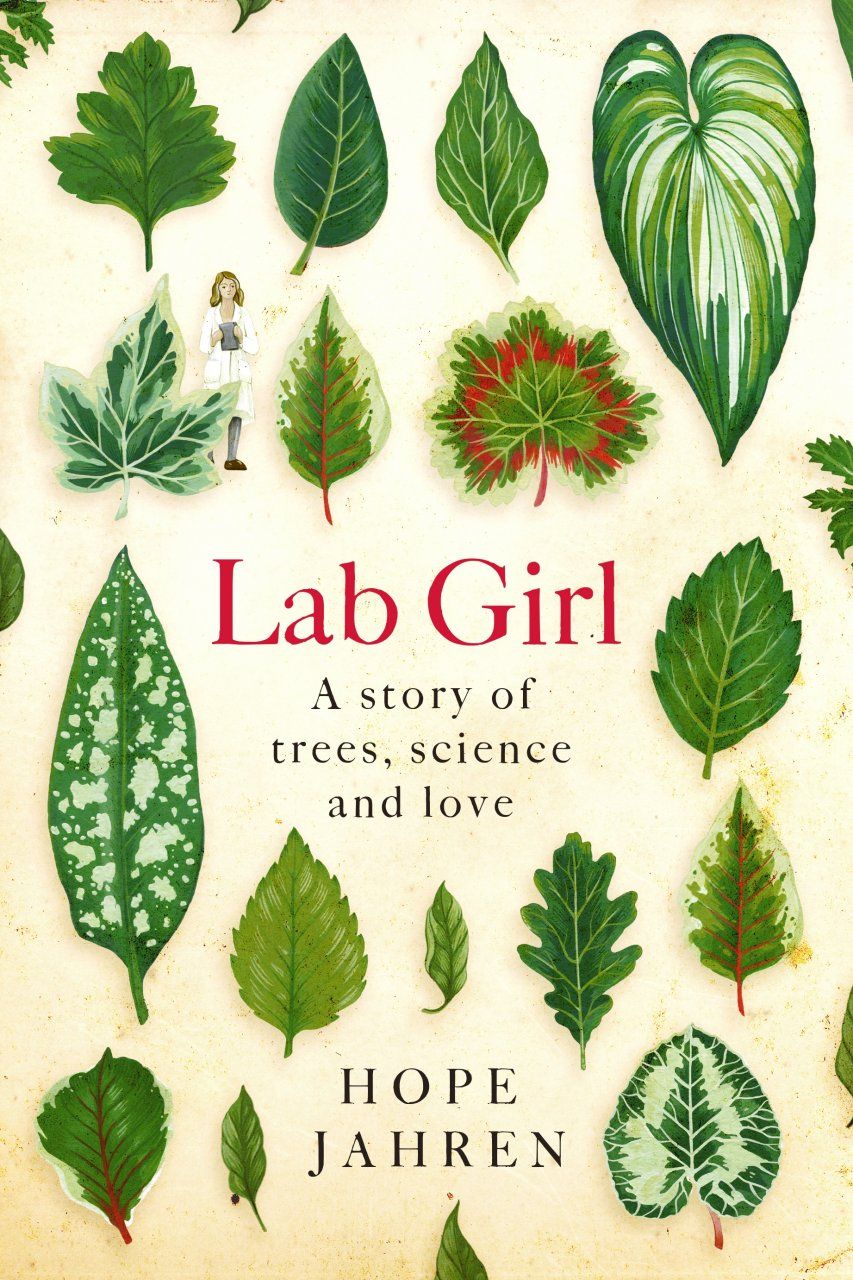
我是一個讀書、寫書評,也從書籍出發去談社會現象的人。很高興我發現了 Matters 這個寫作平台。作為開篇貼文,我想分享一篇我三年前寫的關於 Lab Girl 的書評。
原文書訊:Jareh Hope. 2016. Lab Girl: A story of trees, science and lov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中文書訊:荷普.潔倫。2017。樹,記得自己的童年:一位女科學家勇敢追尋生命真理的故事。台北:商業周刊。駱香潔譯。
────
故事是這樣的:一個爸爸開車載兒子上學,路上發生嚴重車禍。爸爸只受了輕傷,但是兒子大量出血,緊急送往附近的醫院。值班的外科醫師趕來一看,大呼:「天啊!他是我兒子!」
──請問故事中的外科醫師和小孩是什麼關係?
作為一個開放式的問題,答案當然可以各式各樣。例如小孩是外科醫師的義子,或者外科醫師和開車的爸爸是一對 gay couple,小孩是他們共同扶養的兒子。
這些答案當然都對,然而許多人,特別是男人,似乎都忘記了還有一個更簡單的答案:外科醫師是他媽媽。
作為一個「性別意識」的簡易測試,這道題目早已行之有年。國中的我在公民課本上看到這道題,也當真困惑了許久,直到我偷看了後面的解答。那時的我腦海中真沒有任何一個外科醫師是女的。這段經驗我一直銘記,直到我成為一個處處在意「政治正確」的女性主義支持者。
美國植物學家荷普.潔倫(Hope Jahren)在她的回憶錄 Lab Girl 裡,寫出了這道題目的真實變奏。潔倫的父親在社區大學教科學,從小她就在父親的實驗室長大。潔倫熱愛實驗室裡的所有儀器,夢想著有一天能夠擁有它們。然而每個值得追求的夢想,必然都會碰到阻礙。潔倫碰到的第一個阻礙就是性別問題──她沒看過有任何一個科學家是女的。
潔倫急切想知道女生到底能不能當科學家,但是在寡言成性的北歐裔家庭裡(潔倫自嘲),這個問題無論如何問不出口。在三位哥哥陸續上大學念自然科學之後,潔倫仍然試圖在極其有限的管道中,搜索任何一個女性科學家的身影。
在植物學路上磕絆的過程中,也總是有人不把她當作一個認真的科學家同行,而把她看成是隨同採集隊出勤的「小女生」助理──縱使她和他們一樣努力構想理論,一樣努力挖掘、收集、標記,一樣努力寫作發表,如果不是更加努力的話。
人們把男科學家視作理所當然,以至於系所主管從未想過同仁懷孕時該怎麼辦。看到潔倫挺著大肚子在系館前喘氣,系主任的反應竟然不是上前察看,而是請潔倫的數學家丈夫勸她懷孕時不要到學校來。丈夫將壞消息告知潔倫後,潔倫的反應首先是:「實驗室是我建立的,實驗室才是我的家!」繼而是:「為什麼他要透過你來告訴我,他不會直接跟我講嗎?」
Lab Girl 之所以叫 Lab Girl,顯然多少是因為在科學領域,女科學家的經驗如此不被「預設」(且不說在美國,植物學已是性別最平等的自然科學領域之一了)。
不過我們也別因此以為這是一部典型的女性主義控訴之作。事實上這本書花了更多力氣談科學本身,以及科學家這個身分給潔倫帶來的慰藉和成長。
有一個幾乎已成套路的女性主義問題意識是這樣的,亦即現代婦科的診療設計是如何地以男性治療者為中心,如何置孕婦的生產體驗於不顧。然而就在潔倫寫到她分娩那一晚時,劇情來了個大逆轉(plot-twist):當醫生和護理人員用各種跳動嘈雜的醫學儀器將她包圍時,她內在的 Lab Girl 忽然又跑出來了。她頓時感到安心無比,因為她覺得自己已經被科學儀器背後的萬萬千千科學知識溫柔承接。
無論如何,若僅僅只把 Lab Girl 讀成一部性別政治的張本,就太低估了潔倫說故事的能力。
身為一位學者,潔倫如此隱喻她生涯之初,決心來到喬治亞理工學院,從無到有建立一個「潔倫實驗室」的心情:
「種子擅長等待。大部分的種子至少等了一年才開始生長,櫻桃種子等上一百年也沒有問題。種子到底在等待什麼,只有它自己知道。唯有在獨一無二的溫度∕濕度∕光線組合,加上許多條件同時出現時,種子才會勇敢冒險,把握今生唯一的一次生長機會。⋯⋯每棵強壯的樹最初都是一顆等待的種子。」
身為一位同事,潔倫這樣隱喻她和學術上的手足∕伴侶∕同志∕同梯∕共犯比爾(Bill)之間的關係:
「只有非常少數的真菌與植物建立起深刻持久的和平關係,菌絲網包覆、穿透樹根,與樹木共同分擔把水抽進樹幹的責任。真菌也會開採土壤裡的稀有金屬,例如錳、銅跟磷,然後把這些金屬當成東方三博士的珍貴禮物送給植物⋯⋯真菌在哪裡幾乎都可以活得很好,但它放棄了更輕鬆也更獨立的生活,選擇跟樹緊密結合。」
但請別誤會──這本書縱然處處穿插植物學隱喻,它從未成為媚俗的「植物版心靈雞湯」。它從未告訴我們「植物如同人生」,它並不鼓吹「向植物學習」。相反地,潔倫處處提醒我們「植物和人類何其不同」,唯有承認植物和人類之間的深刻差異,我們才能真正認識植物,以及,幸運的話,我們自己。
潔倫生涯第一篇重要研究,是有關植物的蒸散作用。一個人跑了四分之一個美國,搜集黑莓樹一年間的蒸散量,潔倫大惑不解地發現:一年中最潮濕最熱的夏季高峰,黑莓樹的蒸散作用卻驟然陡降。這就像一個人在乾燥涼爽時猛流汗,潮濕悶熱時卻不流汗了。這怎麼可能呢?
關鍵就在黑莓樹不是人類。作為大型落葉植物,蒸不蒸散考慮的不能只是外界環境的溫濕變化,而要通盤規劃「在一年中的什麼時候要開始脫落葉子?」對黑莓樹來說,靠蒸散作用調節溫度只是其次,更重要的是,蒸散作用會讓葉子維持常綠,生長不息。為了趕在入冬之前就讓葉子脫落殆盡,黑莓樹只有在溽暑時分就降低蒸散量。
在顯而易見的層次上,植物不像人類,它們不會僅僅為了調節體溫而流汗。只有在付出努力深刻了解之後,人和植物才能找到彼此的共通點:我們都必須為了活下去而預做準備,並且犧牲忍耐。
初出茅廬的潔倫由此學到了秉持一生的植物學家精神:植物學的目的不是要把那些我們過去不知道、不熟悉的植物現象納入我們熟悉的世界;而是首先要承認人跟植物之間有著巨大的鴻溝,然後看看自己可以離開熟悉的原點有多遠,離陌生的植物有多近。
這,對我輩學習人文社會知識的人來說,何嘗不是一則意味深長的植物學隱喻。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