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我說」專欄2022年回顧

我們從2022年初開始邀請新二代書寫尋找自我認同的經驗,作者們大多是大學生或社會新鮮人,從自身成長經驗出發,反思身份、多元、文化差異等重要面向。透過這篇回顧,我們希望能更用心地回覆作者們的創作,並且提供簡單的索引,讓讀者們能夠從文章連結到自身關注的議題。
|新二代「聽我說」專欄的誕生|
我們從2022年初開始邀請新二代撰寫自身的成長經驗與身份認同,至今陸續累積十餘篇。從自己的經驗出發,聽我說專欄作者們不斷回應二十多年來台灣社會對外來者的偏見,尤其打破片面與單調的刻畫,不管是過去對於新住民家庭的弱勢想像,或是新南向政策下對新二代的期待與要求,每一篇都展現尋找身份認同的複雜性。
首先在面對身份認同時,作者們都傳遞一件重要訊息:身份認同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與他人互動過程中,被迫需要面對自己的成長背景、親緣關係,有時甚至是外貌長相,進而反思這些特質為何與人不同(關於認同的形成,Yen Le Espiritu剖析亞裔美國人經驗可以提供許多啟發)。劉曉星十分具體地點出求學階段如何被迫面對自己和同學的差異,因為2000年代對於新住民家庭教育的焦慮,教育政策直接在二代貼上弱勢的標籤,而各式各樣的檢測量表都不斷提醒新住民家庭如何與別人不同。然而被移民政策或他人貼上標籤是一回事,回應標籤的方式有千百種,如同Rita提到不斷想要證明,證明自己的成就與能耐,拆解刻板印象。
正因為身份源自於血緣、家庭、家鄉,因此尋找認同也意味著梳理自己與其他人、其他地方之間的關係。在探索新二代身份時,Lý Xì Dầu與李宣如都強調認同不是一座孤島,而是牽動著自己與母親、家族之間的經歷。雖然新二代已經逐漸能夠以母親的東南亞家鄉為傲,然而異鄉人的身份卻曾經為母親帶來異樣的眼光。從Xì Dầu與宣如的筆下可以發現,明明是相似的身份特質,卻會因為時空背景、世代差異而有全然不同的感受,也就是說認同會因為每個人的經歷、擁有資源多寡而呈現不同的樣貌。此外,認同不是單純從過去經歷中尋找自我,而是不同生命歷程階段的對話,像是寓羢不斷學習Tagalog,甚至和母親開啟關於異文化的對話,使得兩人的關係更為靠近。
換句話說,認同是流動的,既沒有絕對,也沒有唯一。Yky提到,以前覺得自己是越南人,但隨著台灣時間久,也更加坦然面對自己的不同背景。有趣的是,Yky用了混種這個概念來形容自己,而其他專欄作者們也在尋找認同中拾起不同的詞彙,像是混血、兩個文化。這其實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混」意味著橋接兩個不同元素,難道台灣的爸爸與東南亞的媽媽留著不同的血液,屬於不同的種族,有著截然不同的文化嗎?偉翔的文章談到媽媽來自越南華人家庭,,大歷史下離散難以用國族血脈解釋。這題其實隱藏著幾個敏感而複雜的議題,一方面種族或族群等概念都沒有絕對的分類標準,往往是政策、政治、經濟等因素合理化不同分類方式(有興趣讀者可以進一步參考社會學家Omi與Winant有關種族形成的研究),尤其是台灣自90年代以來不斷區別待遇來自東南亞的移民工,進而加深台灣人與東南亞移民工之間的分野;另一方面,台灣至今缺乏機會好好檢視主流社會與移民社群之間的關係,以至於混血和混種雖然合理化我者與他者之間的分野,卻也是新二代訴說自身經歷的重要表達方式。然而在血緣和親屬關係以外,也有其他因素影響認同的形成,甚至影響能否取得他人的認可。Nhi提到小時候被外婆當成台灣人,沒有當成自己人,因而下定決心學好越南語,獲得阿姨的肯定,讓Nhi更有信心說出自己同時是台灣人也是越南人。比起單純的血緣或親屬關係,語言掌握對於許多新二代認同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當今強調多元包容的脈絡下,面對這些身份認同時,究竟該看見差異,還是強調我們之間沒有什麼不同呢?像是婕容覺得新二代的普通又正常,而慧君卻在成長過程中被他人以異樣眼光對待,覺得自己和別人不太一樣。如同前述,同一個身份標籤在每一個人身上承載著不同的經歷與情緒,而說出這些經驗既是希望能夠得到肯定與重視,但同時也能夠以平常心相互理解。到底一樣還是不一樣的焦慮其實也烘托出目前多元論述的一大問題:他者的差異往往都還是服膺於主流社會的規則,不管是新南向將新二代所具備的語言文化特質當成行動招牌,或是強調新住民的異鄉人身份以彰顯台灣的多元文化,這些論述方式都不斷將文化差異給塞進同一模板,甚至當作商品來販賣(關於差異性如何商品化,必須大力推薦bell hooks的系列作品),進而忽略差異所伴隨的權力關係。正因為主流社會賦予差異性不同的價值,有些差異受到推崇,有些則難以獲得認可,像是依靜提到,相比於東南亞的新二代而言,擁有中國背景的新二代更難陳述自身的認同,因為這觸碰到了敏感的國族問題,已經超越當今台灣多元文化論述所能接受的範疇。
到底該如何影響主流論述也超越了本篇回顧文章的能力,但比起遠大的目標而言,這一系列的文章提供更簡單而深刻的反思:我們能否更直接面對身份認同的討論,而不是習慣性地陷入回覆套路,打開更多對話的可能。
----------------------------------------------
|想不到回覆的時候,也可以花更長的時間反思|
夏末的時候,我參加了一場新二代留聲機的聚會。那天開場時大家圍坐在一起,以一個年份回想當時的點點滴滴,拼湊和遷移有關的記憶。當時間軸來到2000年代時,參與活動的新二代憶起上幼稚園、上小學的經驗,怎麼回應學校老師和同學對於母親東南亞身份的疑惑,一到暑假便開始籌備回外公外婆家的長途旅行。
作為一個台灣人,頓時覺得自己2000年代的經驗不足掛齒,不外乎就是學校和家裡兩點一線的奔波,煩惱著未來要做什麼,卻從未對自己到底是哪國人感到困惑。聚會當下有些慌張地說自己想不起來,負責主持的夏曉鵑老師輕聲說沒關係,讓我得以暫時放下內心的惶恐,卻也不斷思索如何面對這種無處安放的感受。
事後我想起研究所同學Amy,在一次有關族群與種族的討論課堂上,許多非裔與拉丁美洲裔的同學們剖析自己在美國生活的經驗,而作為一個亞洲來的國際學生,我聽了相當有共鳴,對於不公平的待遇也義憤填膺。Amy是我在所上的好朋友,她來自德拉瓦州的白人家庭,那天討論課Amy異常的安靜,下課後她告訴我不知道該用什麼方式回應同學們的經驗,倒不是她不了解種族主義或族群階層化的脈絡,而是任何回應都顯得不太妥當,因為她終究帶著白人的特權在社會走跳。我當下感到有些詫異,討論內容怎麼會給Amy帶來如此強烈的自我審查?
在新二代聚會上,我突然理解Amy的困窘,那種說什麼話都不對的侷促感。我回想那天和Amy對話的當下,的確比起她跳進討論中開始高談自己的觀點,我更感謝她花時間好好一起聆聽。之所以串連起這兩個經驗,不是為了類比新二代和美國一觸即發的族群議題,而是想要以自身經驗為出發點,好好面對聆聽他者經驗時的困惑、無所是從的感受。不管是新二代述說成長經歷,還是族群或性別少數提供自身觀點,過程中都必須與主流價值角力,甚至挑戰生活中的常規,這勢必會讓主流價值下的既得利益者感到不安適。
與其急著給予回應或是消除內心的不快,或許更需要梳理困惑,甚至花時間和自己的偏見相處,當然這不是特別容易的事情。這與既得利益者的「特權」息息相關:特權不單是擁有多少金錢或權力,更是包括生活中不需要面對的障礙,像是不會因為外貌、膚色、打扮方式被貼上標籤,不需要思考母親的異鄉身份,更不會因為母親的身份在學校與職場被質疑。在聆聽他人的身份認同與經驗時,意識到自身的特權也是重要的一步,包括自身的家庭、社經背景、性別等因素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特權不是絕對的,而是根據所處的環境而發生變化,像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到了異國他鄉,勢必也需要面對自身與他人的不同。意識到特權不是為了盤點自己有多少特權,更不是和他人較勁,而是了解自己從何而來,不再一味地要求別人和自己都一樣。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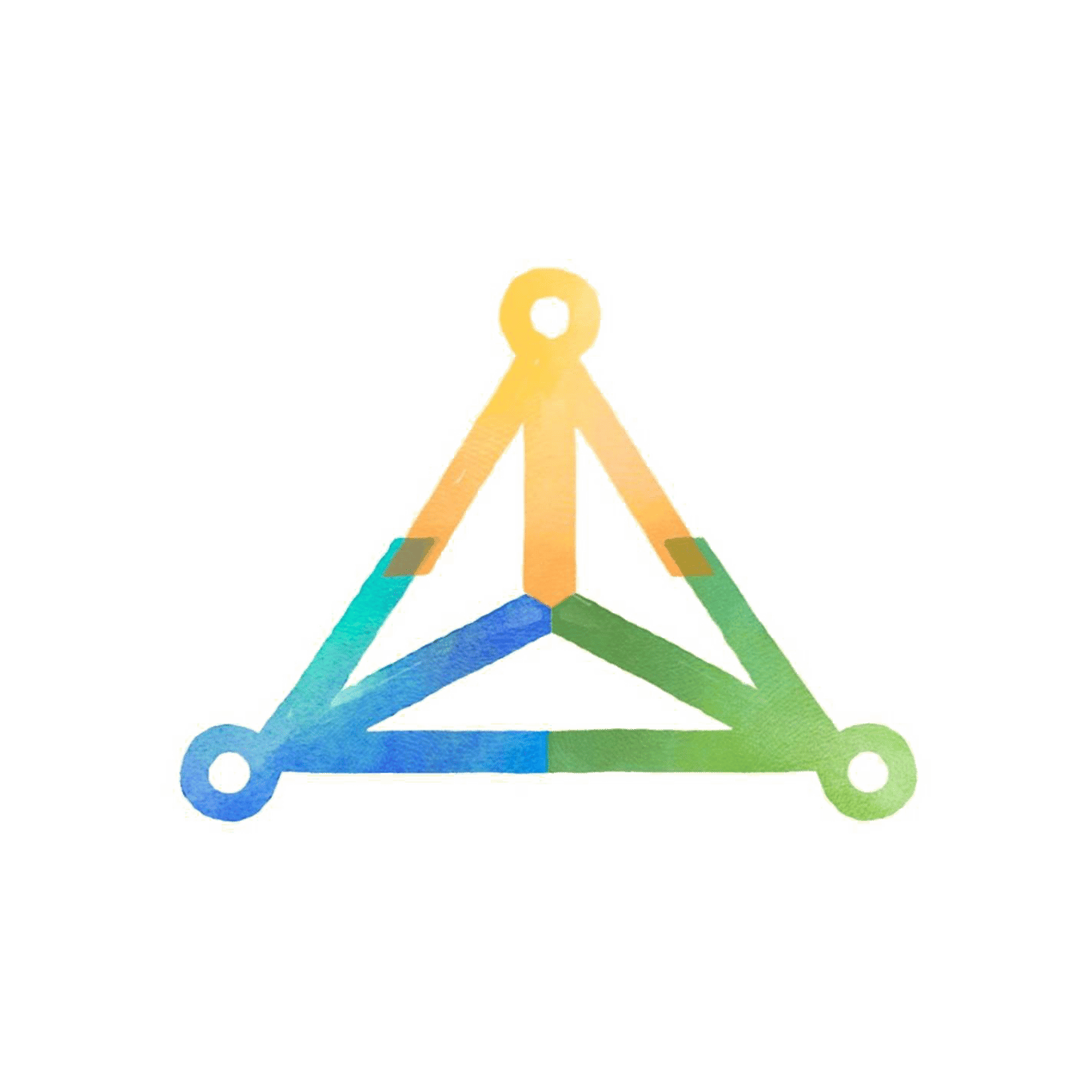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