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乱乱想(一):宗教与国家——缘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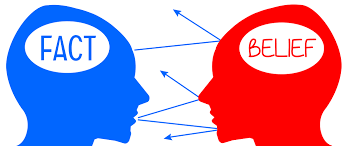
“病毒没有信仰。”
这是我不知从哪里看来的一句,细品,很有意思。
2020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的一大特点,是以高度传播性不分种族、年龄和性别地精准打击感染人群。其中,两组带有明显身份标签的群体性确诊案例引人注目,一是韩国新天地教会的聚集性疫情,另一个则是香港北角佛堂的接连感染事件。毫无疑问,尽管中国内地封门闭户人人自危,这两地的人们踏出家门去虔诚追求信仰的决心似乎并没受到多少影响。无论是信耶稣基督,还是信如来佛祖,可以想象:所求之愿,大概率是包括但不限于“平安健康”云云。然而毫不留情面的新冠病毒,以铁铮铮的强硬姿态空降教堂佛舍,似乎丝毫不为几乎贯穿人类历史的两大信仰所动。由此引发了我的两种忧虑与思考:
1. 大病初愈后的信徒们,该如何自处于无处安放的信仰?
2. 信仰到底因何而来?
“相信”是一门玄学。有位新闻从业人士曾总结“后真相时代”的切面是“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这大概指的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传统新闻媒体的权威性受到威胁,越来越多的人判断信息真实度的路径,开始转换成“意见胜于事实,立场决定是非”模式。
假设“后真相”说法成立,那么自然地会产生一延伸疑问:“前真相”存在过吗?
首先,这里说的真相,需要区别于类似“一片叶子掉了下来”的简单现象。我们经常说人要有“求真精神”,话里话外藏着两个弦外之音:“真”是复杂现象,需要厘清脉络,并非唾手可得之物;正因此事至关重要,所以要费尽力气,查明原由。“前真相”时代的权威新闻工作者,好比信息生产环节的“局内人”,而读者又好比信息消费端的“局外人”。早期的局内人,往往受雇于特定组织,因而信息生产的驱动力带有机构属性。他们一般经过长期专业训练,以“专业主义”之姿恪守行业操作准则。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以机构公信力为担保的信用体系,大概率上是值得信赖的。但这就直接等同于一张让人丢枪缴械,无条件相信的万能通行证吗?
针对这一问题,学界也存在迷思。传播学学者李金铨把它用“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来解释。无论局内人是身在此山中,亦或是在此山外,庐山的真面目皆因天气,温度或看山人所处海拔等的变化而变化。即使我们运用卫星技术从高空窥见全貌,也无从将某一瞬间的定格就称为庐山的真面目。因为万物灵动,而静止,也仅仅只是运动的一种状态而已,并不能以一概全。但更难办的是,“局外人”角色的两种可能性也宣告了“真相探知”的破产:一方面,局外人可能因没有触及到下棋者的实际利益考虑,因此能够超脱于棋局之外,更能看清真相。即“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正是因为没有想下棋者之所想,局外人也会囿于表面,无法深度换位思考。
当然,如果有心,我们甚至还能更进一步提出质疑:谁有权力定义“真相”?前文已经提到:早期的信息生产行为,往往带有机构性质的驱动力,同时机构也会为信息真实度背书。那么往前追溯,机构自身的驱动力从何而来?这个问句几乎贯穿传播政治经济学长达70多年的历史:传播机构的维持,必然脱离不了经济来源,钱从哪里来,权力往哪里去。但难道要说,谁更有钱,谁就能有权定义真相吗?又或者说,庐山的真面目,只有世界首富才能最终定义吗?由此可见,尽管有机构公信力背书,咱们也不能一股脑儿全将信任托付。正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
那么,再回到我们起点:“前真相”存在吗?“一切坚固的”,真的坚固吗?
我不禁开始对此存疑。
按照学者李金铨的说法,真相是局内人和局外人观点的互相渗透。用我的理解,所谓的“真”,是个伪概念,它是局部或片面真实在人心上的一种认知投射。既然客观上的“绝对真相”无从得知,那么主观上对信息的认知判定,几乎决定了人们选择“要信什么”和“不要信什么”。换言之,虽然我们至今,也无从得知这个世界上是否有神的存在,但也不妨碍人们主观上愿意将自己的信任,交付给并无实体的象征或符号,进而起源并绵延了宗教的存在。既如此,我们基于以上论述,我几乎要认为:“相信”是一种非理性行为,而“信仰”大概是一种更为极端的非理性行为吧。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