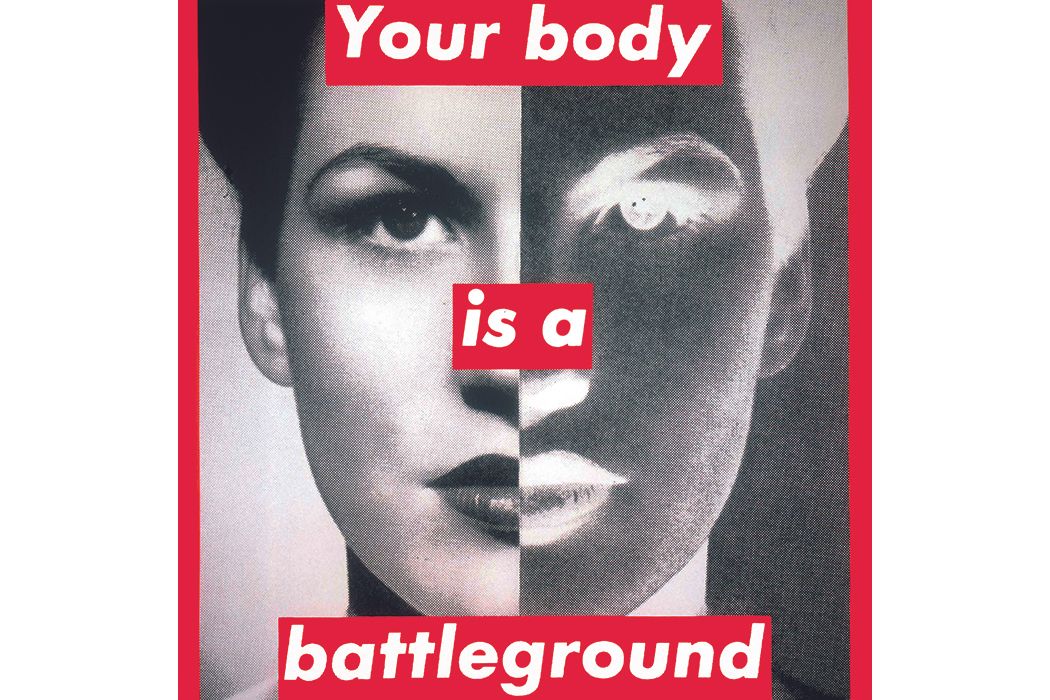我们的失去必须是无可挽回的 | 纪念李文亮
上星期天我和朋友去了在纽约中央公园举办的李文亮医生的悼念会。我们迟到了一小会,前来参加的人比我想象得多很多,远远地便看见草地旁聚集了一大片黑色的人群,沿路上也遇到不少身穿黑衣、带着鲜花来的中国人。
我们快步走近人群,隐约听到主持人的声音的时候,我和朋友不约而同地拿出了包里的口罩戴上了,这让我们迅速融入了这个戴口罩的人群。
这竟然是我半个多月以来第一次戴上口罩,在半个多月淹没在疫情的狂潮里之后,那一刻却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从不在场,可我也从未离开。
组织者准备得很用心,旁边草地的铁围栏上贴着给李文亮医生的悼词,黑白相间,这是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人们为这场悼念活动写下的留言,悼词下面摆满了鲜花和标语。





我想摘抄一些记录在这里:
“李先生,天堂也会有炸鸡,火锅和你最爱的日本料理吧!我想天堂一定不会有高墙,一定不会逼你说‘明白’,一定充满了爱与自由。谢谢你——匿名”
“没有愤怒的哀悼无意义,我明白了。——陕西,乔”
“李医生,您做了您应该做的事。——匿名”
“长夜将至,我从今开始守望,至死方休。——羞愧者们”
“李医生,愿在天堂一切安好,往后之日,我辈将继续发声,真诚地面的现实,延续您的光亮。死亡不是您的终结,您在我们心中,憧憬光明,则不惧黑暗。——湖北随州,李晨曦”
“再见了李文亮医生,未来的人生里,我会用每一段真话告慰你。——Chen Yi”
“一路走好,您是勇士,是义人,但其实您更愿意做个普通医生吧?我被您发出的光所照亮,也未自己的沉默感到羞愧,但我将尽我所能去记住这一切。——中国上海,小何”
“李医生只是一个讲真话的普通人,为什么普通人会遭遇这种事情,凭什么!3W+的确诊患者为什么要遭遇这些!有些人会被钉在耻辱柱上,人民会记住它们,历史会记住它们。——北京,孙圣佼”
“对不起,是我们所有人的忍气吞声迫使你成为英雄。——中国深圳,王亚伟”
“国士无双,一路走好。您是中国最好的眼科医生,擦亮了人民的眼睛。——浙江宁波&纽约,Veronica”
“英雄走好,哨音已被大家听见。——Singapore,Barney”
“表达自由,人权之本,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天总会亮的。——Nanjing,Ivy MA”
“讲真话的历史,血泪斑斑。即使明天重新开始,也绝对不能原谅昨天,李文亮是普通人,是你我他。李文亮千古!——武汉,非非”
“天道无情匹夫补,我们会为您上街的。——江苏南京,陈子润”
“这一次,我也想勇敢一点。——福建,朱慧玲”
“李医生一路走好,谢谢您的善良和勇敢,我们不会忘记,愿日后可以在光明的地方相见。——Shanghai,Sara Yang”
“我如此哀恸,不是因为他是吹哨人,他普通地有良知,有着普通的善良,见到危机也只敢小声提醒。我们连这样小声提醒的人都保不住,都失去了,到底还有谁来振臂高呼。那个死去而又不能死的人,是我的同胞,更是我的同类,我在哀恸我自己。——云南,十一”
悼念会的后半段,是在场的参加者排队拿麦克风自由发言,很多人上去了,他们之中有些是留学生,也有在纽约定居、做生意的移民。有坐了六个小时的车从外州赶来的女孩,有担心回国后被清算却仍然选择不戴口罩发言的留学生,有六四时期推着婴儿车上过街的阿姨,还有从小生活在国外,却努力用中文讲出:“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的ABC。
他抗议变本加厉的审查制度,微信、微博的频繁删帖封号;她呼吁海外华人寻求国际社会的关注,调查中国疫情;她建议中国年轻人传承父母的记忆,莫让历史被遗忘;她提到要发展个体意识,拒绝和集体绑定;他指出维稳手段为何反而导致社会动荡;还有更多的人强调了言论自由、公民权利、体制改革。他们每个人说完,周围的人都热烈鼓掌,人群里不断有人喊:“说得好!”
只有一个人招来了反对,他戴着墨镜和口罩,遮住了整张脸,拿起麦克风后说到:“如果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那我也要发一点不同声音。大家想一想,李文亮的死和他说不说真话有关系吗?他染上了病那是不幸,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我们要抗议的不是言论不自由,而是疫情,大家不要把矛头转向……”
我旁边有个男生立刻喊到:“可是我们的声音在国内根本发不出来!”又有人喊:“疫情哪儿来的?怎么散播开的?”、“那他为什么被训诫?”,另一边有人连喊了两次:“你自己去微博上说啊!”
嘘声越来越多,导致他没法顺利说下去。他有点急了,反问了人们一句:“你知道真相吗?这里有人是李医生的朋友吗?有人认识李医生吗?”
这句话挑衅到了更多人,人群吵杂起来,有人要求他摘下墨镜和口罩,有个高个子的中年男子高喊:“我是武汉人!”
但同时也有几个女生在呼吁:“让他说完!”、“他有说话的权利!”“我们不是在开批斗大会!”。
结果,他还是没能把后面的话说完,发言时间就到了,主持人让他再排下一轮发言,他便也没再出现。
会后我在人群中几乎见到了纽约各个圈子的朋友,大家聚在一起聊了起来,好几个人问起我最近微信被炸号的事。是的,我也在4、5号那波炸号风暴里牺牲了,我那个用了八年多,加了近五千个人的大号就这么没了,说是一次性抹掉了我半个人生都不为过。但几天来反复回应了不同人一遍遍“怎么炸号的?”的关心之后,情绪早已平复下来,进入了接受现实的阶段。
那个周末阳光很好,虽然成排的树枝都光秃秃的,但湛蓝的天空仍让人心旷神怡。离开会场之后,我和朋友一边聊天一边穿过中央公园,打算去另一侧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到了之后才发现他们在换展,于是就近去了大都会,一直逛到它关门。
朋友不久前刚从国内逃难般回到美国,赶在美国的边境禁令生效之前。原本回国过年的她每天都在帮忙协调物资,最紧张的时候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她说,这其实是她这大半个多月以来第一次出门走这么多路。
我也是。1月下旬从台湾回来之后,我其实就没怎么出过门了,赶着写完了观选记录时,国内的疫情已开始全面曝光,一天甚于一天的信息过载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我除了在楼下街区的范围里去超市买点东西、吃个便饭外,连地铁都没搭过两回,仿佛和国内同步过起了隔离生活。
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关闭了微信一整天,可只维持了一天。因为工作需求,必须每天都盯着国内的最新消息,只能继续刷个天昏地暗。我的作息严重混乱,经常通宵不睡,偶尔又一睡不醒,连续好多天每天只吃一顿饭。
由于全身心围着国内的疫情打转,也没法和当地的人hang out了,难以忍受局外人置身事外的轻松和深表同情(实则并不在乎)的姿态,难以忍受人类的悲欢竟无法相通的事实。即便理智上知道,别人也有自己的生活要过。
在这段混沌的日子里,我一直处于失语状态。连续被一出夸张过一出的魔幻现实轰炸,被时而暴躁时而抑郁的极端情绪捕获,没能留下多少思考和表达的心力。另外,也是觉得自己既然身不在场,应该把公共空间留给更急需发声的人们,毕竟与他们的切身遭遇比起来,我实在没有资格造作呻吟。
周末外出舒展了下筋骨后,压在我心里的重负也解下来许多,同时也清楚地感觉到,此刻身在国外是个多么大的特权,我还能像往常一样在街上散步,去喜欢的公园和博物馆,在餐厅里和朋友吃饭聊天——纽约确实什么都没有发生。
就像每次公共事件,都会导致你的圈子再一次割席,这次当然不会例外。我在朋友圈互相拉黑了三个人,他们认为我不该指责政府,对方甚至没有尝试讲理,而是骂到:“你躲在国外逼逼啥啊?”
这让我哭笑不得。我三十一岁才离开中国,也曾计划回国却不得,这一路上所付出的代价,其中既有心甘情愿也有迫不得已,虽然我都欣然接受,却也不算占了什么便宜,顶多算是等价交换吧?我不曾自视甚高,可凭什么被你们挟持成罪人呢?
早在疫情爆发之前,我和周围很多人已苦于国内变本加厉的言论管控,和傲慢低能的官僚体制太久了,那些勇敢发声和行动的人都已经被“应收尽收”了,所以不那么勇敢的我才会稍微显露出来。我们的公共空间一溃千里,最后连一个小声在自己群里提醒身边人的李文亮,都逃不过公权力的侵犯。
毕竟早就不是第一次了,我也累了。这个年龄的我还在愤怒,不是因为心浮气躁;我还在批评,不是因为口无遮拦,而是非如此不可,遭遇了这个时代的我们自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如果可以,我不想写这篇文章,我想让最近过得一团糟的自己放松一下。我已身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应该自由地生活,我前几天甚至差点飞到夏威夷去,为了逃避纽约漫长压抑的冬天。
就像我曾经旅行时遇到的一个朋友,她一直在中国体制内工作,后来嫁给了一个加拿大人,前段时间刚在美国生了孩子,经常在朋友圈晒一家人的吃喝玩乐,我也时不时会点个赞。
直到疫情爆发的时候,她正在欧洲度假,我看到她发朋友圈轻描淡写地说:“国内的大环境是没法改变的,好好改变自己吧。”
这样的话总是把我一耳光抽醒,提醒我配不上这个精致的世界。
毛姆在《刀锋》里写过一句话:“自己忍受恶报比较容易,只要硬着头皮就行,教人不能忍受的是看别人受苦,毕竟看起来通常不是罪有应得。”
这次疫情所带来的全面公共危机,虽然我不会乐观到认为它能直接导致结构性的改变,但也不可小觑它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冲击。过去只有小部分弱势群体和离弱势群体较近的人承受体制问题带来的大部分压力,其他人尚还可以装作岁月静好,不闻不问就算了,但这次灾难已经把大众给裹挟进来了。
过去我会对大多数人的无动于衷齿冷:一个人要多无耻才会轻视他人的痛苦?现在我想,人们也并非冷漠,也许他们只是在极有限的空间里找到了一个出口,以逃离自己无能为力的心情吧。
我曾经有一个被炸掉的微博号,还活着的时候颇有一些号召力,被炸掉是因为在18年3月份的时候,国内最大的民间女权媒体平台“女权之声”遭到全网封杀,我写了一篇倡议文章,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向新浪申诉要回账号,那篇文章一夜之间被转发了五千多次,然后号就没了。
其实当时我很清楚,只要发出这篇文章多半会被炸号,但我也很清楚,我们不能失去“女权之声”。我想,如果连这个时候都不站出来,那留着这个号有何用呢?要我何用呢?
这一次也是类似的心情。多年以来,我都喜欢把靠谱的公共信息分享到朋友圈,慢慢地也积累起一定的公信力。我的朋友圈里有差不多五千人,所以已经算是一个小型公共平台了,其中大部分人生活在国内,也很少翻墙,所以总有人对我说,我是他们看到外面世界的一个窗口。
在疫情期间,社交媒体上信息大爆炸,但良莠不齐真假难辨,有个朋友留言建议我建一个微信群发文章和各路消息,方便大家查看。我想毕竟筛选信息也是我擅长的事,不如尽这点能力服务一下身边的人,别的也不知道做什么更好了。
所以我拉了个群,没想到立刻就加满了五百人上限。我自己一个人发不过来,又怕遗漏重要信息,就又找了我几个信赖的朋友,组了一个八人的评审团,一起筛选质量过关的内容发到群里。
我们分享了很多文章和社交媒体的帖子,包括外网的,很难确定到底是哪篇踩了雷。但后来我们倾向于认为是许章润的那篇《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因为听说这篇文引炸了很多群。我们在群里翻来覆去发过好几遍,网页版、图片版、pdf版、印象笔记版,生怕大家没读到。结果当天晚上群就炸了,顺带炸了作为群主的我和评审团里一个发文最活跃的朋友。
被炸的理由是“传播恶性谣言等违法违规内容。”是的,其实就在广大群众群情激愤为李文亮平反的时候,微信和微博也没有一刻停止以此为罪名的疯狂删帖封号。
发现炸号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该来的还是来了,”并且故作轻松地跟朋友说,我已经有了这个心理准备。
如果真是因为许章润那篇文章而炸,给他陪葬我觉得很荣幸。作为一个身在墙内的知识分子,写出这样的檄文已是奋不顾身了,难道我们连转发的损失都不愿承担吗?
有人说,他写了又有什么用,转眼就被删掉了;还有人说,太难读,没法普及给广大群众。我只知道,他说出了我积郁已久的愤怒,我也相信这震动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内心。
我想我们冥冥之中还有着同样的觉悟,在眼睁睁目睹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命运之后——
那个坐在阳台上敲锣鸣病的人。
那个深夜追着殡葬车凄厉地喊着“妈妈”的人。
那个在一千人共用一个卫生间的隔离所看《政治秩序的起源》的人。
那个开着货车在高速路上流离失所没有归处的人。
那个坐着死去被家人抱住头等待殡葬车的人。
那个隔离在家中被饿死的人。
那个花了20万最终因无力承担而被放弃治疗的人。
那个怕传染给家人而给自己挖好坟偷偷上吊的人。
那个无处就医又怕传染妻小从桥上一跃而下自我了断的人。
那个90岁高龄为60多岁儿子排到一张床位而在医院守了五天五夜的人。
那个在求医院床位的微博下评论:“我家人刚过世了,空出一个床位,希望能帮到你”的人。
那个先是骂着求助者的嚎丧影响心情随后又只能以同样的方式呼救的人。
那个为求助而临时学会用微博发了一句“你好”的人。
那个被盘查时用围巾捂住嘴,因买不到口罩而羞愧哭泣的人。
那个用橘子皮当口罩的人。
那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家都死了只好孤身一人去民政局报道的人。
那个把抵工钱的口罩全部捐出去的人。
那个写下“安心赴死”、“是时候奉献出自己”的人。
那个写下“能、明白”并印上红手印的死了两次的人。
我实在不忍再看到同胞们承受这样的苦难了,不希望中国人继续深陷在这数千年的王朝更迭中苦苦挣扎。如果这么多的死亡和眼泪都无法推动国家的进步,如果仍带着侥幸心理纵容这个落后的体制和反动的执政者苟延残喘,下一次再走到这历史的关口,又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那天夜深人静之后,我还是大哭了一场,一直到清晨。微信是我重要的国内信息平台,没了势必会影响工作,但幸好我没有居住在国内,生活不会被它绑架。但损失又何止如此呢?我想到在我八年多的人生路上一个个遇见的人,我再也不可能把他们都找回来了;我想到我和朋友、家人的共处时光,我们曾一起旅行过千山万水,我再也不可能重走一遍了。
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叫“微信封号”的超话,里面有近四百个帖子,全是那两天遭到封号的用户的申诉,很多人在竭力地自证清白。有一个人是抑郁症患者,被永久封号后,丢失了和女朋友生活的点滴,又错失了工作上的大客户,精神崩溃,说自己下辈子不想来了。
然而没过多久,整个超话都被微博删除了,只留下空空如也的页面。
后来我又申请了两个新的微信号,第一个存活了一个晚上,第二个存活了不到二十分钟。
我拒绝了昏庸,最后却逃离不开虚无。沉重的虚无感的阴翳几度遮蔽了我所有感官,但突然在某个时刻我明白了,和之前那些无法触碰时的疏离和伴随着的困惑不同,我突然和更多人的痛苦有了连接。尽管不可相提并论,可我想到在2020年刚开始时那些失去了父母的人,失去了半个人生的人,失去了希望和安全感的人。所有人都失去了什么,而仿佛我只能通过永远失去自己的一部分,才能和他们有片刻的同在。
我们的失去必须是无可挽回的。如果你再也无法整全,那我也不可能恢复原状;如果你一天没有自由,我也将一天没有名字、没有住所、没有回忆。否则浮沉都将是可耻的,我从未身处战场的愧疚和遗憾,都将无从被赦免。
所以我对你将永远说不出那句:“一切都会过去的。”
我的朋友,这是昏庸和虚无的两难中唯一的真实,而我们已抓住了这真实的片刻。因为这彻底的失去,我们再也不至于两手空空了,我们握住了一点武器,它是坚固的,提醒我们将要为什么而战。
那天纽约的李文亮悼念会结束之后,晚上我在一个WhatsApp群里看见组织者在和参与者们交流悼念会上的经验,他们讨论起了那个问“李文亮的死和他说不说真话有关系吗?”的“异议者”,很多人都对自己当时的反应做出了反思,觉得应该让他说完,应该平等地交流。
但也有朋友认为不用太在意,“这样的话微博上有很多,无非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团结起来抵抗疫情,现在抨击政府言论不自由对疫情没有任何帮助,应该等到疫情结束后再说。”
是的。其实当时他刚说出第一句话,我就知道他后面要说什么,然后发现果不其然。类似的话语,我从疫情爆发第一天起听到现在,由不同的人前来重复同样的逻辑,让我疑惑,这到底是发自真实经验的共鸣,还是集体无意识地拿来了某种宣传呢?
后来,我又看到一个关系很近的朋友说:“感觉现在批评都不是时候了,刚刚看了数据之后觉得疫情真是非常难,湖北两万七千多人确诊,武汉将近一万五千多确诊,还有疑似的肯定至少好几万,官方在观察的密切接触者全国至少有十八万多。我有一个认识的微信好友在武汉,看了她发的所有文章,对照官方数据,突然就觉得目前最重要的不是批评,是需要更有建设性的意见。”
在我提出“批评和提建设性意见不矛盾”后,她强调说,并不是觉得批评没有意义,而是目前比起单纯的情绪化的批评,提出积极的建设性方案更有用。
我回复:“我现在看到的有效的行动是两种,一种是直接救助受害者,帮助其寻找各种资源,一种就是坚持不懈地推动舆论追责权力,有些人着眼当下,有些人想得更远,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资源和能力选择能做的吧。但是说到底,这么久以来的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是必须想清楚的。如果这样的灾难还没能让人起来批评当局的错误,下一次也是重蹈覆撤(实际上这次已经是重蹈覆撤)。我不同意用“提建设性方案”来否定和消解所谓的“情绪化”,就让人们愤怒吧,为什么不愤怒?情绪有什么问题?我们要看到造成这种情绪的机制,而不是本末倒置,苛责这种情绪没有更好地建设机制,因为我们本质上并不掌握建设这个机制的权力。”
但是她和其他人最后都会问一句:“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我无言以对,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每个人身处于这场并非一日之寒的天灾人祸里,都是无力的,无力让我们急需找到确定的答案,也急需回到有掌控感的常态里。
可是,我宁愿承认自己是无力的,承认自己是失语的,承认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承认自己无路可走,也不要虚伪的思想和行动作为出口。
我拒绝解脱。我身边还有很多西西弗斯,他们日复一日地把即将功亏一篑的巨石重新推到山上,却从未得见山顶的风景。我怕弃他们而去,我怕被他们放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记住李文亮。因为他是具体的人,有着具体的故事,他直观地讲述了他在这个盛世华章里是如何失败的。这个华章的任何一个情节都不是新的,一字一句都是陈词滥调,让人疲惫不堪、头昏脑涨、浑浑噩噩。但李文亮的面孔是新鲜的,他陪我们度过了新年,给了我们一个记忆上的锚点,让我们回想起这场灾难时,不至于将它粉饰成另一场胜利,而强权将悔之不及自己竟然造出了一个平民英雄。
疫情期间,我和很多朋友一样,开始读加缪的《鼠疫》。鼠疫是荒诞的象征,在这个荒诞的世界里,魔显形,恶显相,而尚有人性的人们将如何自处?
我知道其中被摘抄得最多的一句是里厄医生的话:“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的问题。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但这还不足以表达其中的真意。
塔鲁最终觉悟到,即使抱着良好的愿望,即使好人也难免杀人,“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种逻辑中”,一举一动都可能致人死亡。他学会了谦虚,明白了要“心甘情愿原原本本做人。”
“我只想说,大地上还有灾难和受害者,一定得尽可能拒绝,不要跟灾难同流合污……我听到过那么多高谈阔论,脑袋几乎给弄晕乎了,那些高谈阔论也足以使其他一些人晕头转向,结果同意去杀人了,从而也使我明白了,人的不幸缘于他们没有使用一种清晰的语言。于是我决定讲话和行动都要明明白白,以便走在正道上。”
写完这篇文章时,刚好是李文亮的头七,微博上依然有人因为纪念他而被警察惩戒,但愿被他唤醒的对真实、自由表达的追求不会停止。让我们把每一句话都清晰、明白地说出来吧,为了那些不再说话的人,为了每一个真实的字词都不再被替换、不再被模糊、不再被缩写、不再被指代的那天。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