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清明,和無數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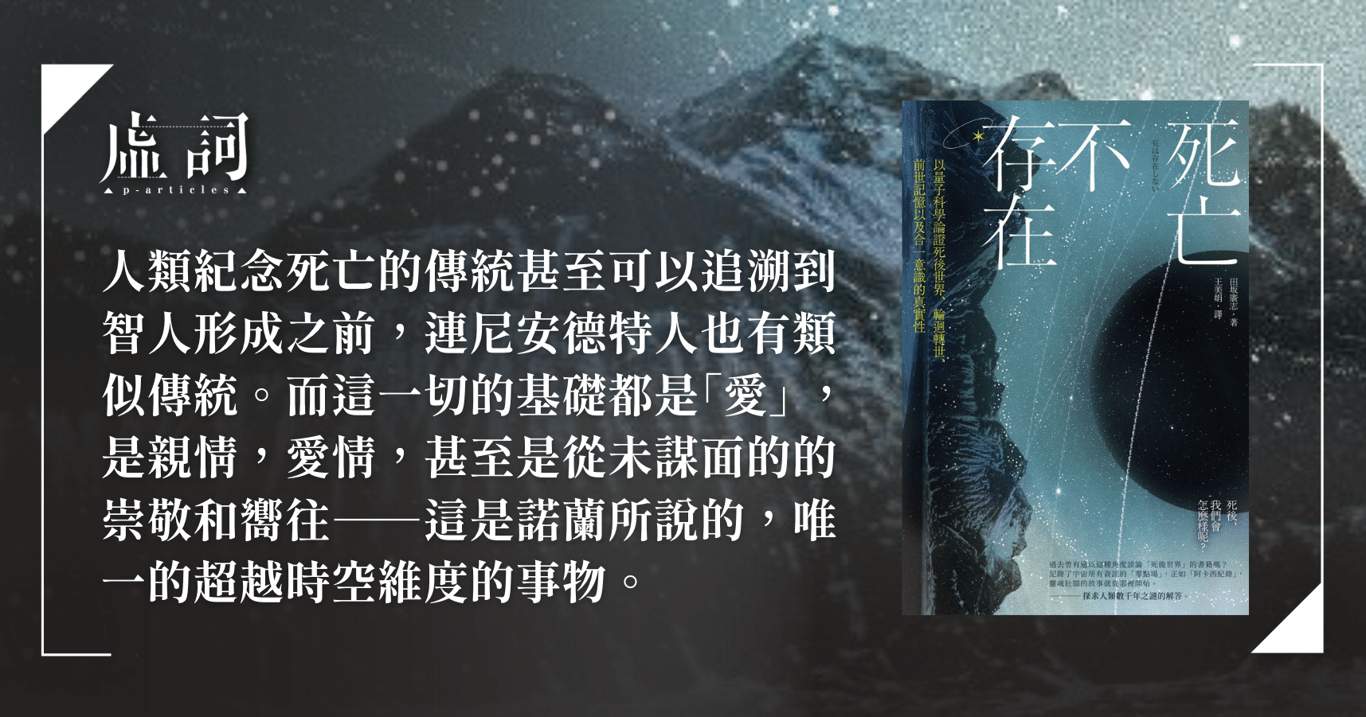
文|王崢
清明節並不是新加坡的法定節日,但這並不影響街上的悼念活動,像某種可控的火災一般,點亮了以秩序和整潔著稱的獅城,在海霧中醞釀著一股不知飄向何處的憂愁。在每個排樓組屋的街口,政府都設有一個巨大鐵桶,不知是鏽跡還是油漆,在夜色中閃著暗暗的紅色。從晚飯開始,這些本用來收納垃圾的容器,如今被賦予更神聖的功能:等待那些在熟食中心,辦公樓,和地鐵站陸續走出的人群,以新的身份重聚為鐵桶前的悼念者,開始燃燒生者世界的兩大特產——冥府的新加坡幣以及新加坡護照。不知在那裡,這些是否還是硬通貨呢?似乎在亞洲文化中,悼念是我們談論死亡的唯一方式。我們無法真正了解死者的想法,所以只能猜測;而正因為猜測,悼念更像是我們對於自身的慰藉。在每年的清明節,新加坡的武吉布朗,世界上最大的華人公墓,一群致力於保護其不被政府拆除的現代「守墓人」都會邀請全真派道士為一群無名的死者舉辦一場集體的悼念。這位名為皮特的道士說:「我們就是他們;我們太關注未來,有時忘了過去,所以清明節是一個禮物」。
在田坂広志的暢銷書《死亡不存在(死は存在しない)》中,這位曾經的醫師從量子力學的角度解釋了「死亡」並不是終點,而是一個通往下一個階段的過渡。但這本書並不能完全消解人類對於死亡,首先是他人,然後是自我死亡的一切情感和歷史。科學和藝術彷彿都是為了解釋同一件事情:如果死亡是終點,和更多看起來永恆的事物相比,我們短暫的生命意義在何?當然如果按照田坂的解釋,死後世界、輪迴轉世、前世記憶以及合一意識均存在,那麼悼念將不僅僅是一種遺憾,而帶著某種慶祝的心情—祝福死者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足以將讓「欲斷魂」的悲哀轉化成一種「踏歌聲」的祝願,即所謂「喜喪」。人類紀念死亡的傳統甚至可以追溯到智人形成之前,連尼安德特人也有類似傳統。而這一切的基礎都是「愛」,是親情,愛情,甚至是從未謀面的的崇敬和嚮往——這是諾蘭所說的,唯一的超越時空維度的事物。清明節,作為一種文化儀式,將以物質和非物質的形式,不斷提醒著這種超維度的力量,如何將一個在白日裡不苟言笑的城市,在夜晚變成一個情斷絲連的劇場。但當我走近他們,卻也無法再保持一個外來者的矜持。我想起了童年時的清明節,外祖父曾在一個陌生的墳頭一邊掃墓,一邊對著我說:「有一天你也會來這麼看我」。
於是我久違地和外祖母打去電話,發現家裡長輩都回去了,這是春節後再一次難得的重聚。隔著一整個南海,我也只能以電子掃墓的形式參與其中。現在掃墓甚至可以掃碼了,但是相比於物理運動,也許電磁波可以更好的地傳遞感情,如同田坂書中所述。總之是給我外祖父的一點悼念。由於童年時父母忙於工作,我和外祖父的時間遠大於和父母的時間。作為書畫家,外祖父總是精神矍鑠,對於一切含有文字和圖像的事物都樂此不疲—我常常是他的觀眾和讀者。在病榻上仍堅持寫作,也許代表了某種東亞文人的理想形象;但他從未對我多言他因政治動亂而傷殘的左腿,直至離世。之前因為他罹患的胃癌甚至想過要學習醫學,但實在缺乏這方面的天賦,在美國大學時就已放棄。但後來在藝術中彷彿又找回童年時候那段和外祖父在桂林附近四處臨摹和旅行的日子。他有些不穩地騎著自行車,彷彿又出現在悼念的人群中,如海市蜃樓。人生是多麼奇妙的輪迴,上週向香港一家英文雜誌解釋七年前寫的第一首英文詩「瑤族葬禮(An Iu-Mien Funeral)」,寫的便是外祖父作為民國時代的左派知識分子,卻選擇一個極具民族和宗教意涵的葬禮形式。當時我無法理解,但從新加坡回想美國和中國的一切,突然覺得可以明白,人面對死亡時的感受。
外祖父臨終前的最後一句話是:「讓他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無論怎樣總是可以活下去的」。想到這裡時,新加坡已入深夜。滿街的煙火在鐵桶中次第熄滅,只剩下了一簇火星,和無數團霧氣,還在樹梢遊蕩著。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and clap, let me know that you are with me on the road of creation. Keep this enthusiasm toge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