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 从丁真到拉姆:直播时代的少数民族旅游开发
从拉姆到丁真,流量的逻辑重来都只带来经验的断裂。从丁真到拉姆,本文发掘了一段少数民族旅游开发的历史,并以此追问直播时代不同的人群如何被锁在自己的流动性/不流动性里,从而孕育了一种特殊的内部东方主义。与丁真们有限的流动性对应的是后隔离时代复苏的旅行流动性;而二者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是少数民族地区自1990年代以来的旅游开发与当下网红直播业的发达。两个因素的结合虽然得以让丁真们待在家乡就能不断地与粉丝互动,邀请他们来家乡玩,从而完成旅游kpi,但这一基于内部东方主义的财富流动并非永远奏效。直播并非只意味着舒适的旅游,也意味着劳累和危险,正如同样在康巴藏区直播的拉姆所遭遇到的。
作者 / 曾毓坤
01.
远方与隔离
30天引发60多个热搜,“甜野”男孩丁真持续爆红,已经证明他并非昙花一现。丁真也并未走向典型的网红之路——没有像羌族“天仙妹妹”等初代少数民族网红那样外出巡演、走穴带货;更没有像蒲巴甲等康巴前辈正式出道演艺圈。丁真留在理塘,进入体制,签约了国企理塘县文旅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为理塘形象大使。在直播日益成熟的今天,丁真已经不需要离开理塘也可以保持自己的热度。
与此前的少数民族网红一样,旅游经济下的丁真得以爆红,背后是当代中国内部东方主义话语下对少数民族的他者化消费。集中体现丁真形象的短视频《丁真的世界》呈现的缓慢、放松、单纯的远方:
在我们村庄,每天推开门,就能看见格聂雪山。大部分时间,我就和弟弟一起放牛,时间过得好慢,好慢,躺在草地上,也能躺上一整天。最开心的是和兄弟们赛马,我骑马很厉害的,村里比赛经常拿第一,他们都叫我赛马王子。很多人问我,我的梦想是什么,我没有太想过这个问题,就想骑着我的小马,翻山越岭。这就是我的世界:雪山、草原、冰川、寺庙、白塔、我的朋友们、还有唱不完的情歌。
在电脑荧幕前观看这一远方的近景是内地打工人忙碌的格子间生活。无论是对梦想问题轻盈的回应,还是罗列“雪山、草原、冰川、寺庙、白塔、我的朋友们、还有唱不完的情歌”,毫不奇怪的是所有这些语法和词汇都取自典型的“内部东方主义”词典,构成对国内另一个世界的想象和消费。值得注意的是,丁真的独白以自己和家乡的连接结束:“但我还是最爱我的家乡,我想就这样呆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我想留在理塘,为家乡做一些事情。”骑马的丁真并非没有流动性,但只在雪山下和草原上翻山越岭,他从未也不会离开他的家乡理塘,丁真的流动性只是把远方拉得更远。

但这种远并不足以阻止人们“朝拜”丁真的步伐。相较历史上通过异闻和奇珍异宝对他者进行幻想的“东方主义”,“内部东方主义”的特点是距离的相对浓缩,加上基建和交通工具的发展,”朝圣”式的旅游是对远方向往后的下一步行动。“朝圣”的另一面是疫情稍缓时人们出门的渴望。十一长假期间,经中国旅游研究院测算,国内游客达6.37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恢复79.0%。虽然丁真走红的时节已逐步接近疾控专家担心的第二波疫情可能爆发的窗口期,粉丝们的热情被视频和直播中丁真的笑容彻底燃放。《人物》等媒体的多篇报道已经展现了络绎不绝的丁真“朝圣”潮。粉丝们往往身着汉服或者藏装,见到丁真后给他礼物,向他问候祝福,丁真回之以标志性的微笑,然后就是拍照、合影,短暂的相聚融合了一连串交换,以最夸张的方式放大了远方的他者与殷勤的来客之间的差异。
02.
变迁的少数民族旅游业
值得一提的是,“内部东方主义”并非新中国多民族图景的必然结果。建国初年的民族团结政策曾着力建立平等、互助且互相了解的跨民族关系。丁真的家乡理塘民国时名为理化县,带有明显他者化色彩的“涵化”、“教化”之意。解放后,1951年5月,经政务院批准,将带有歧视民族性质、妨碍民族团结的县名“理化”改名为理塘县。
据人类学家路易莎(Louisa Schein)的研究,“(内部)东方主义”借由旅游大规模在中国出现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文革时代,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的恢复和发扬被包含在文化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另一方面,中国朝向世界,自我呈现中显著的元素之一就是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繁荣”,这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和1993年人民代表大会等节庆活动中少数民族身穿多彩民族服装的游行可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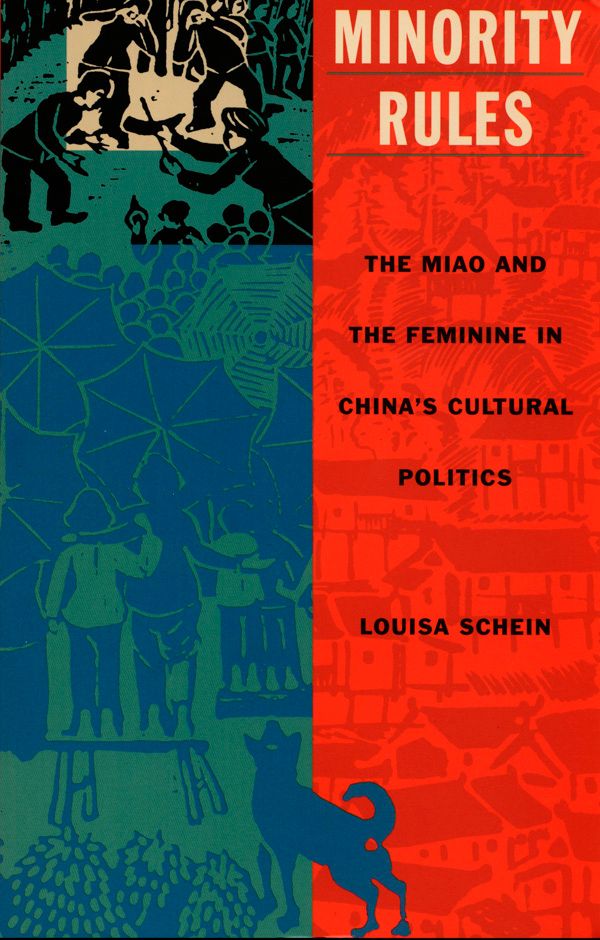
1980年开始的中国旅游热也因此首先接受的是国际旅游市场的凝视与塑造。但很快,以西南地区为代表的地方政府以民族特色旅游积极响应国家的经济政策。1990年代开始,各地的大小民族村开始兴起,吸引的是国内大小城市的汉族居民。2005年的“十一五规划”则进一步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上议程,旅游开发被视作将城市财富导向农村、进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思路。这一背景下,对少数民族居住的边陲地区各地政府而言,旅游开发看起来能够把最落后、最需要解决问题的人群转变为最奇异、最能带来经济效益的资源——两者恰巧都是东方主义的必要元素。传统国际秩序中的东方主义也因此转换为常态化国内旅游所鼓励的内部东方主义。
相较民族村模式,近年来的少数民族旅游开发则牵涉到一地的整体规划。旅游往往与当地政府的城市开发规划高度相关。2018年刊登在《甘孜日报》上的《理塘县做强县城纪实》如实记录了理塘县2014年县第十三届人大代表会以来的城市发展。该报道提到:
理塘县以“康南区域中心城市”作为城市定位,立足高起点、高标准、大战略,按照旅游全域化理念和“一张蓝图绘到底”的规划原则,完成了县城总规、详规和景观规划。几年下来,理塘县城改造的拆除面积达25846.62平方米,整改面积达32229.39平方米,新的楼房整齐地按照“一纵三横”的城市规划进行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本地民生的考量,《纪实》一文多次使用“世人”一词,强调这些工程的服务对象在于外界的潜在游客:
曾几何时,这座美丽的“天空之城”不再光鲜亮丽,留给世人的,满眼是破败景象。城市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城市管理瘫痪,房屋建筑乱搭乱建,店招店牌杂乱无章,占道经营比比皆是。
工程的意义即在于让“被世人称为‘雪域圣地’、‘草原明珠’、‘天空之城’的理塘‘重归于世’”。一系列带有“自我东方主义”色彩的旅游规划也就不难理解:主城区建筑通过3000万元的投资进行了藏文化装饰。佛眼林卡、白塔林卡、幢嘎林卡、扎邦林卡4大林卡和仁康古屋中心、勒通古镇、千户藏寨等旅游景区也陆续建立。曾书写理塘的仓央嘉措被塑造为本地旅游符号。包含丁真签约的理塘文旅公司在内的一批旅游公司也陆续成立。
然而,规模化的投入并不总在旅游开发中奏效。一地迎合内部东方主义的旅游开发的关键一点在于与相似、相近的景区拉出区别,如何在旅游资源相近、开发政策类似的少数民族区域里冒头。同样在今年爆红的贵州独山县水司楼就证明了这一规划冒头逻辑可能带来的恶性竞争。独山县已负债400亿,而2亿打造的百米水司楼的旅游开发思路是将水族建筑元素奇观化,从而得以冠名“天下第一水司楼”。“天下第一水司楼”背后的建筑师李宏进以怪奇少数民族景区建筑设计闻名。从1998年开始,他先在张家界设计荣登吉尼斯的“九重天世袭堂”,此后作品包括恩施土司城的百米“九进堂”、湘西龙山县的世界最长土家风雨桥等,直到17年经济犯罪落马,留下没能完成的独山水司楼。出生于湖南湘西,李宏进的职业生涯史是一部少数民族景区“自我东方主义”旅游规划建设的浓缩史。

而理塘的旅游规划遇到的竞争比独山更加艰巨。邻县稻城亚丁早已是川藏县上成熟的“香格里拉”。理塘如何能够找到自己区隔点?比独山县幸运的理塘没有卷入恶性的举债开发。当丁真爆红并决定留守家乡时,他“甜野”的个人符号成为理塘独一无二的底色。而对旅游效应而言,将丁真捧红的直播产业则是比李宏进式奇观建筑更加无形而有效的基础设施。
03.
在地的网红,走丢的明星
直播技术一方面可以无限拉近粉丝与明星的距离,另一方面,屏幕的隔绝仍然没有办法取代来到理塘与丁真一对一合影,到远方旅行依旧是必要的。而这一比“天下第一水司楼”更管用的旅游磁铁背后的必要条件是丁真在理塘驻守,而非如前一代少数民族网红蒲巴甲等人一般成为跨地转场的明星。
上一代康巴男神蒲巴甲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在全国性选秀节目《加油,好男儿》夺冠后被吸纳进中国娱乐产业的中心,也因此逐渐迷失为不再在地的他者。这从他历年演绎的电影角色中可见一斑:既包括《喜马拉雅王子》《新康定情歌》中的藏族角色,《唐三藏传奇》里的胡人,还有大量如海归精英、剿匪英雄、晋国太子申生等本身无任何民族特点的角色。随着中产白领的生活和叙事成为影视题材主流,明星身上已经不大容得下诸如少数民族的符号,比如吕良伟的越南船民身份几乎从不被提及。而选秀阶段作为网红到明星的过渡,正好是民族性对人气能够叠加的阶段。蒲巴甲在《好男儿》时期的走红和之后影视生涯的不顺都不令人意外。介于蒲巴甲和丁真之间的是天仙妹妹尔玛依娜,2005年因为偶遇旅客摄影师,照片被发在网上后爆红,鱼贯而来的签约和商演最终引导她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进入科班的她戏路没有更宽,也和蒲巴甲一样在无民族的主流明星和少数民族网红的二元框架里无所适从,最终过气。

正如诸多分析尝试预测和众多网友所担心的,娱乐界对丁真而言是一条危险的旅途。对他和其他少数民族网红,娱乐产业中能够施展的空间并不比进藏的国道更加广阔。只有待在家乡才是安全的。与之相比,朝拜丁真的粉丝虽然要克服山路和海拔,但因为旅行而得到满足的心灵却十分辽阔,难怪有不少讨论都围绕着是否要在理塘住一年。
但这种分析所遮蔽的是少数民族地区在结构层面上相对有限的流动性。在汉语和经济能力绑定的当下社会,丁真除了眷恋家乡,不太会说汉语的他即使进城打工也寸步难行。而本文最后意图指出的是,与丁真们有限的流动性对应的是后隔离时代复苏的旅行流动性;而二者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是少数民族地区自1990年代以来的旅游开发与当下网红直播业的发达。两个因素的结合虽然得以让丁真们待在家乡就能不断地与粉丝互动,邀请他们来家乡玩,从而完成旅游kpi,但这一基于内部东方主义的财富流动并非永远奏效。直播并非只意味着舒适的旅游,也意味着劳累和危险,正如同样在康巴藏区直播的拉姆所遭遇到的。
04.
直播的两面:舒适(Leisure)与劳痛(Labor)
人类学者Jenny Chio曾经犀利地在她研究贵州苗族农家乐的著作《A Landscape of Travel》中指出,旅游产业途径中内含着两种流动性,一方面是游客出行,在旅行的目的地尽情享受平时生活之外舒适而悠闲的时光;另一方面则是劳累和苦痛,除了描写在地接待工作的具体劳动之外,她发现,许多苗族居民并不那么“在地”,在回到家乡进入苗寨的旅游产业之前都曾常年在外打工。她反问到,为什么这些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走过的路远多于游客的苗族劳工不会把自己之前的走南闯北称之为旅游?答案自然在于舒适(leisure)和劳痛(labor)两种流动性的区别。事实上,Chio所研究的苗族农家乐正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下的产物,她看到的苗族流动工人则是“三农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嬗变的版本。两种流动性前后折射出的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窘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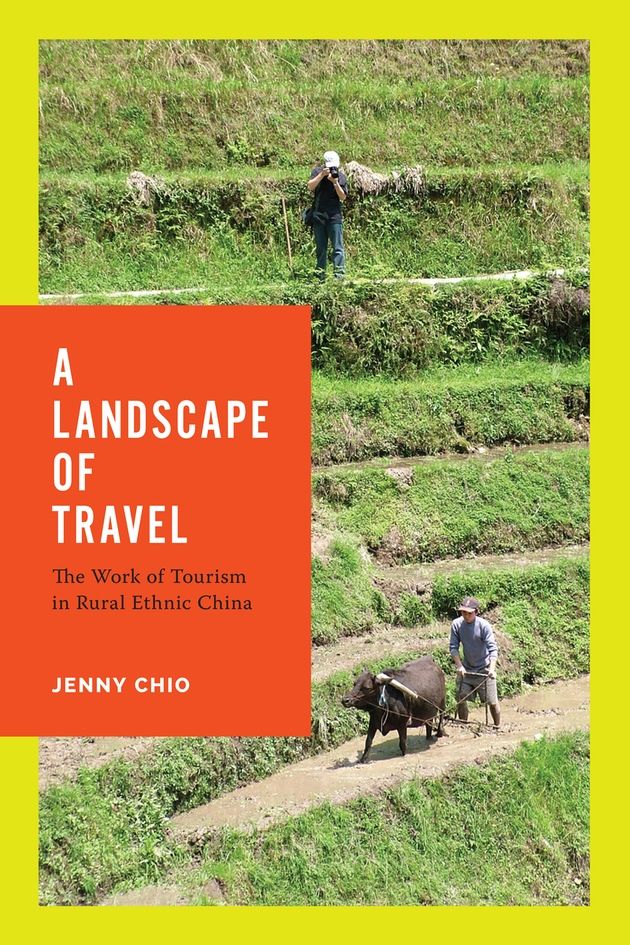
直播时代的康巴藏区不同于Chio笔下的贵州苗族——丁真在格聂雪山下纵马,拉姆在观音桥的山腰采药,二者都没有表现出足以越出家乡的流动性,与Chio遇到的返乡苗族劳工形成鲜明对比。为什么不外出?比少年丁真所言对家乡的热爱更无奈的是拉姆在平台个人简介上所写的话:“我不是不喜欢大城市的生活,但是为了陪在爸爸身边,所以我就靠山挣钱,我想把山上的宝贝分享给更多的人!”
缺乏内地直播打造网红的一整套赢利模式,直播对拉姆而言,从来就不是能带来足够经济收入的工具,无法使她积累足够财富,以要回孩子抚养权,保障对父亲的照顾,进而远离给她带来无尽伤害的前夫。事实上,更加流量化的网红直播已经完全走向了内部东方主义的高级形式——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挪用和消费,比如近日走红、模仿藏族黑肤和高原红的藏妆。藏族主体在藏妆中只是模仿和挪用的“资源”。
而拉姆的直播既不是藏妆这样去在地化的流量风暴,也不像丁真被摄影机发现后意外走红,再成为旅游资源。正如《三联生活周刊》调查报道《被夺去生命的拉姆》一文指出,不带货的拉姆,“网络既不是她的交友方式,也不是赚钱渠道,只是让自己被外界看到的工具”。反过来说,与丁真类似,直播只能把拉姆和观音镇绑得更紧。拉姆得以成为直播网红的是她深嵌在地生活的直播内容,上山、采药、在大山上穿戴好藏族头饰和长裙起舞。
拉姆的直播很好地在展现异域风光、异族生活和自己阳光个性上达到了平衡。但通过她的直播,还是可以瞥见采药生活的劳痛。不同于丁真展现的舒适,这种劳痛甚少能吸引游客来观音桥镇,上山寻觅采药的拉姆并与她合影。而据《被夺去生命的拉姆》报道,对保守的观音桥镇而言,直播这一面向外界的方式甚至成为当地人批评拉姆,并合理化其前夫暴行的依据:“你们外面的人看着挖药好像很稀奇、很辛苦,在我们这里很平常的。我们山里人都会去挖药的,比她小很多的小孩子都会去挖药。”
这种见怪不怪的态度背后一方面是本地保守的性别观,另一方面则是在地视角对自我东方主义的反弹。丁真岁月静好的故事里,他的弟弟和舅舅,乃至邻村的白发干部都因直播获得了人气,而在理塘,没有被直播到的是当地人谋生的劳痛。采摘是横跨藏区重要的生计项目,据《澎湃新闻》报道,今年4月理塘的虫草季,理塘有3万多名牧民进山进行虫草采挖,这对全县人口仅七万多的理塘而言是十分夸张的数字。忙碌劳累的虫草采摘构筑的时空迥异于丁真放牛时所感知的“时间过的好慢,好慢”。丁真是否是其中的一员?明年的4月又是否还将是其中的一员?千里迢迢而来与丁真合影的粉丝又将如何与采摘时劳碌的丁真相遇?或者丁真是否还留在仓央书房从而与采摘的时空隔绝?他或将走出理塘?而走出直播,直面藏区的粉丝们还能否想起曾经直播采摘的拉姆?
相较推断、祝福或诅咒丁真何时会过气,这些未知数是网络直播时代少数民族旅游开发中易被遮蔽的褶皱。看到这些,需要的不是欣赏丁真的眼睛和跨域千山万水的腿脚,而是抵制各色东方主义的视角和对少数民族发展困局的共情。
参考文献:
吴淑斌(2020).被夺去生命的拉姆.三联生活周刊, 2020年第43期
Schein, L. (1997). Gender and internal orientalism in China. Modern China, 23(1), 69-98.
Chio, J. T. (2014). A landscape of travel: The work of tourism in rural ethnic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欢迎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
独立网站:tyingknots.net
微信公众号ID:tying_knots
【倾情推荐】订阅 Newsletter
成为小结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
我们来信、投稿与合作的联系地址是:tyingknots2020@gmail.com

目次(持续更新)
- About us | 一起来结绳吧!
- 进口、洄游与误归:三文鱼的驯养经济与后新冠时代的多物种认识论
- 口罩为何引起热议
- 结绳系疫 | 错过新冠革命:后见之明与民族志知识
- 结绳系疫 | 后疫情时代的后见之明与具体研究
- Corona读书会第23期 | 医疗基建 Medical Infrastructure
- 新冠疫情会长久地改变洗手习惯吗?
- Corona读书会第6期 | 动物、病毒与人类世
- 非男即女?:生物学家有话说
- Graeber | 中文里的格雷伯
- David Graeber | 萨林斯悼念格雷伯
- David Graeber | 论飞行汽车和利润下降
- Graeber+Piketty | 劫富:关于资本,债务和未来的交流
- David Graeber | 傻屌:解开“领带悖论”
- David Graeber | 过于关怀是工人阶级的诅咒
- Graeber | 互助也是一种激进:恢复“冲突与和平之真正比例”
- 国际聋人周的礼物:一份人类学书单
- 「修车大水,就是我想要的生活」——自我去稳定化(self-precaritizing)的「三和大神」
- 算法文化与劳动分工:启蒙运动中的计算
- Graeber | (反)全球化运动与新新左派
- 书讯 | 英文人类学新著 | 2020年9-10月
- 欧洲以东,亚洲以西:后冷战世界下的中亚(上)
- 欧洲以东,亚洲以西:后冷战世界下的中亚(下)
- Corona读书会第30期 | 把XX作为XX:方法、地方与有机知识分子
- Graeber | 如何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至少是已经发生的那部分)
- Graeber | 大学死了吗?人类学与职业管理阶层的兴起
- 马克思、韦伯、格雷伯:学术与政治的三种面向
- Corona读书会第7期 | 全球公卫中的跨国人道主义 Transnational Humanitarianism
- 书讯 | 英文人类学新著 | 2020年夏季
- Corona读书会第28期 | 大坝与水利政治
- 特朗普人类学(一):手、谎言、#魔法抵抗
- Graeber丨格雷伯与科层中国:从《规则的乌托邦》说起
- 黑色海娜:对苯二胺、孔雀与不存在的身体
- Corona读书会第32期 | 松茸的时日
- 编辑手记 | 《末日松茸》:一本没有参考文献的民族志
- 影视造梦:横店“路人甲”们的生活群像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2019年全球社运的人类学实验课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伊拉克抗争:为每个人而革命,也为“小丑”
- 哀恸的哲学:“孩子带来了冰河时代的那种焦虑”
- 书讯 | 英文人类学新著 | 2020年11-12月
- 从丁真到拉姆:直播时代的少数民族旅游开发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