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自我,我們都是時代建構下的個體(上)
法國學者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的回憶錄《回歸故里》在今年7月引進了中文版,作為一名從法國底層工人階級出身的學者(哲學、社會學)來說,他幸運地跨過了埋藏在法國戰後社會階級的鴻溝,並在其獲得社會地位後,以自己父親的去世為契機,在重返家鄉後反思跨越在兩個不同社會等級時空中的自我。在這一過程中,從家庭、社會與政治的視角出發,也對當下我們的生活有更多的啓發與共鳴。

這裡所說的啓發與共鳴,我想具體有兩個層次上的內涵,其一是在更宏觀的社會和我們的共同體角度上來說,迪迪埃以自己的人生經歷觀照出了範圍更廣的社會現實,剝去遮蔽在我們眼前的現實迷霧,以期從政治、社會和文化的角度帶領讀者認識到當下社會現實的本質問題。
而另一方面,是作者在透過對整個現實社會的洞察,以理論為鏡反觀自己的過去,在那段令人羞恥不堪的經歷中以其重新整合自我。透過這樣的回顧,他體察到了整體社會命運與他自身命運之間內在的關係,並在對自身經歷的回顧中映射出身處於這個世界中大多數社會個體的命運與生活狀態,從而在個體的層面給予我們面對現實,我們應該如何在一場「改變自己的勞作」中如何與自我相處的啓示。
因此對於這本書的討論,我將分為兩部分介紹,第一部分主要探討作者是如何著眼於宏觀社會的體察,指出當今現實問題的本質的;第二部分著重談談作者是如何深入地以自我生活合理性為視角追溯過去,調整當下(一場又一場「改變自己的勞作」)和面對未來的。本文是關於這兩個視角分享的第一篇。
迪迪埃用回憶錄的形式,坦誠地將他自己的成長經歷作為基底,勾勒出了一整個現代乃至後現代社會的深刻問題——階級差異及差異是如何透過社會與文化被人為建構起來的,這一比同性戀還讓人羞於啓齒和承認的核心問題,瀰漫在所有人的生活方式當中。用描述法國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態來穿插著社會現象的反思,有著比直接用理論為索引,生硬地解釋生活、社會現象的方法更高明也更符合我們當下的視角所需。

正如許多人所說的,新冠疫情後的世界早已是另一個世界了,但如果從迪迪埃的經歷來看,其折射出世界早已是另一個世界了。

當代社會觀念中最大的錯覺就是生活與高屋建瓴的政治無關,可事實上,政治主題永遠是瀰漫在生活中所有面向的本源,個體、群體、社區…大眾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都會以政治主題的制度化順延展開,只不過在西方社會中,這種展開的過程在民主投票程序中看起來相對更為清晰。
各種理論、主義,在不同階級人群不同生活階段、不同的互動情境中被選擇,同時也在不斷的客體化和主體化的交互過程中塑造著不同人的世界觀,最終落實在他們的人生大大小小的選擇與生活方式之中。被建構的並不僅是理論或觀念本身,而是不同人的實際生活。

不論是歐美政府在應對疫情衝擊下的乏力,還是BLM平權運動在美國等西方社會的風起雲湧,還有國內近期以來頗受關注的「被困在算法里的外賣員」事件。從國外到國內,似乎都有著一股相同卻難以明狀的力量在主導著這些現象的出現,而就從英國脫歐、民粹主義運動到今年BLM運動的歷程中來看,迪迪埃精准地指出了西方社會背後,乃至整個現當代社會背後這股力量的來源。
在以「左」、「右」的嚴格政治傾向為區隔和鬥爭的語境里,恰恰蘊含著導致今天犬儒主義、身份政治和頗具破壞力的社會運動之根源所在,因為在迪迪埃的觀察中,以法國政壇為縮影,「左」和「右」往往是相互轉化,甚至是一體兩面的,左派為獲得被精英階層拋棄了的底層民眾選票而提出空洞的理想和承諾,在獲得政治利益後對底層選民的背叛,這往往也將原本中下階層的大眾導向了以虛假形式主義為口號的極右翼政黨,這看似是底層選民們矛盾性的行為實則有著內在的邏輯——他們需要一種暫時性的發聲和對背叛者的報復。
作者以自己父親和家庭的政治信念作為出發點,花了不少的篇幅擴展論述了深藏在法國民主社會背後的種種背叛與不公。這就讓今天諸如性別、種族平等,理性祛魅、剝削、異化、技術操控、媒介等等視角的解釋,都顯得只是作為現代性的種種側面現象被一一羅列出來,都沒有整體把握住導致這些問題背後共同的政治經濟原因。在翻轉電台的一期專題分享中,我認為李厚辰老師所歸納出來的「個人主義與平民社會」主題就在某種程度上與迪迪埃不謀而合。
當今以西方社會為典型的政治語境中,習慣性地用種族衝突,黑與白的對立、移民與本土公民的衝突等話題為二元視角,替代原本就沒有解決的由政治經濟共同形成的階級不公與固化問題,從而,新建立起來的話語體系又難以觸及問題的根本,導致人們總是在一種不穩定的情緒中左右搖擺:「政治話語的變化改變了人們對於社會的認知,同時也就改變了社會本身,因為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思想的範疇所建構的,這思想便是人們對社會的看待方式。」舊的問題還未解決,新的問題卻在不斷地為掩蓋舊有的問題的過程中被製造出來。
在平民主義平等訴求的基礎上新建構起來的「自由個體」概念,由權力集團和公共知識領域向下注入大眾社會,這徹底將原本就擁有緊密共識的社會團體衝擊得支離破碎,從而某種程度上形成我們今天的原子化社會。在這樣的環境下,個體只有在文化領域和理念上是遵循著「自由主義」的,而在現實生活中,人的工作、人的行為準則、人的社會關係都是早就被塑造好的體系,人可以自由施展其中的影響力是極度有限的,甚至連個體自己的生活方式個體都難以把控。在原有的社會共識中,因某種信念和價值組成的團體不僅僅是形式上、數量絕對值上支持某種共識,而是「共產黨既表達著他們,也塑造著他們,通過共產黨表達出來的集體觀點不反映選民們那些零散的、不一致的觀點」,他們內部是相互塑造,有基於生活經驗提和理性反思、討論而提出的價值主張的,換句話說,黨派團體與選民之間是有著經驗層面和實際生活方式上的互動溝通和實踐的,其價值主張也是經過這長期的互動所形成的。而當下西方民主社會極化的一面就體現在:「選民擁有相同的意見,但這種意見是外界強加的,它不是建立在共同思考出的利益訴求或者在實踐指導下產生的意見之上的,它更多地涉及一種充滿敵意的世界觀(反對外國人)而不是一種政治理念(對抗統治階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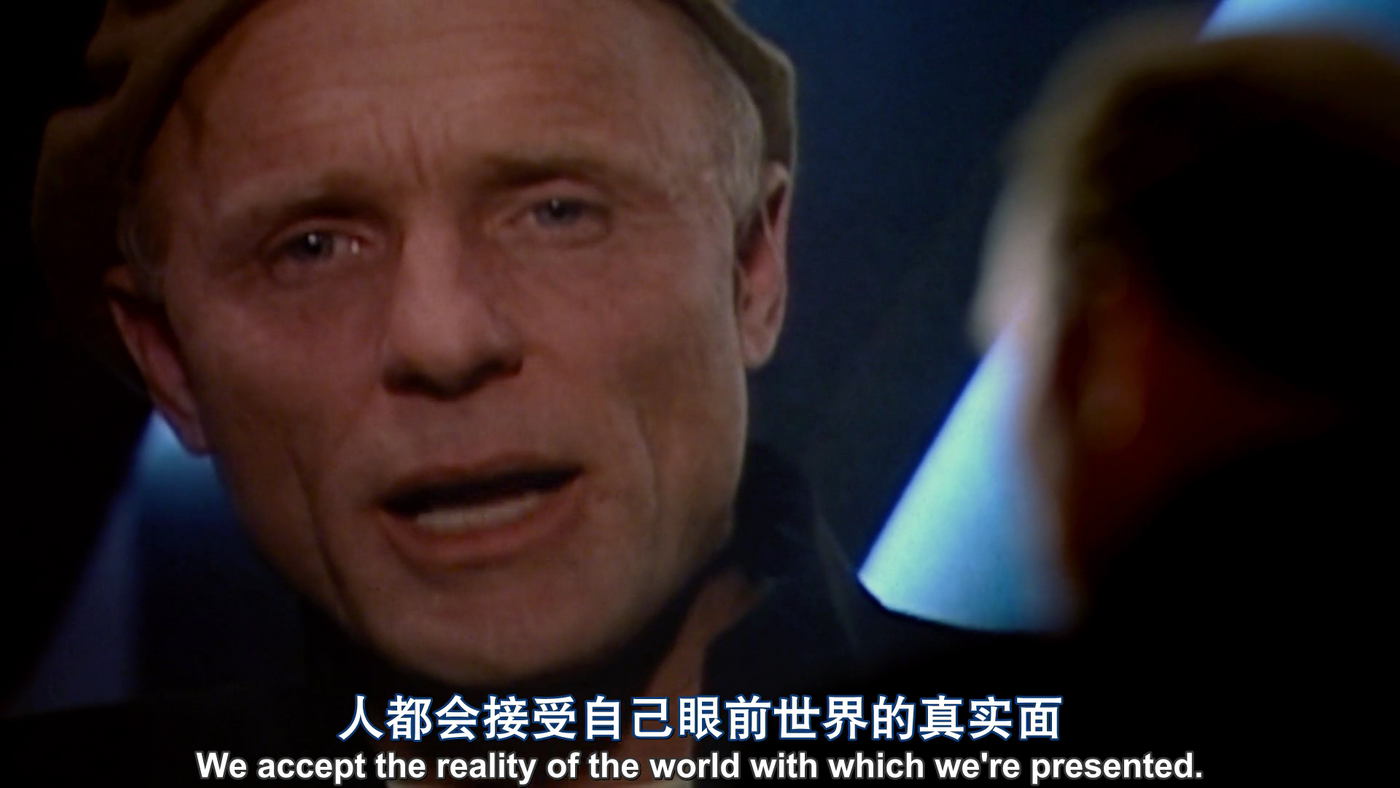
原有的個體被自由主義原子化地消解在了群體中,而群體的意志也在個體的無能中瓦解。
在此,正如李厚辰老師在其專題中提到的,「個人主義」與「平民社會」在現代的合流,共同塑造了現代社會種種的負面問題。
在被自由主義消解的傳統平民社會,社會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他/她的工作之間、個體與自己的生活,其中理解的意義和價值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分工社會、科層制底下的「有機團結」社會。個體在這樣的平民社會中像是無頭蒼蠅般追逐著所謂的「自由」,一方面這所謂的「自由」也讓個體的價值追求與社會的客觀現實之間無法相容的茫然;另一方面在「自由」無法落實在現實中的無奈與失落轉而會墮入各類主張「決定論」的「歷史集團」當中,無能的個體需要在不確定性的一潭死水中竭力抓住那麼一點確定性,而極端政治主張、身份政治領域,便成為許多個體安置不確定性恐懼的臨時舞台。
因此,極端主張的擴散、各類陰謀論、本能性情緒的蔓延就不難理解了。而當今的虛無主義、以單純形式主義來進行的各種社會運動也隨之一波又一波地被催生出來,但其行為背後,是空洞與無能的本質,激情燃燒、批判與宣洩過後,什麼也未被改變或是建構起來,理論與個體的生活實踐之間仍是橫跨著巨大的鴻溝。
也正如最近Netflix繼19年《隱私大盜》後的又一部揭露互聯網技術侵蝕公民社會的電影《監視資本主義:智能陷阱》一樣,它僅僅描述技術現象背後的隱私問題和操縱機制問題和相應的現象,而沒有觸及到更深層的問題,這就讓影片最後幾位受訪者提出的解決方案在現實面前顯得極其的無力。
而在《監視資本主義》中採訪到的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教授的觀點更值得我們注意。衛報早在2019年初就她的新書《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監視資本主義時代)進行了採訪,其中在談到新的資本主義變體是否在新技術形態下得以可能的問題,她談到:「監視資本主義並不是一種技術,數字技術可以是許多種形式並產生許多的影響,但社會和經濟的運行邏輯共同決定了技術是如何塑造我們的生活的。監視資本主義依賴算法和各類傳感器,機器智能和其他平台,但這並不代表它就等同於這些技術」。因此技術的背後,有著更根本的社會機制和經濟生產形態在共同發揮著底層的作用。

而當代由各類社會話題如:各種社會運動、身份政治、貿易摩擦與移民、種族問題,都是在試圖用一套新的被建構起來的社會幻象蓋過對原有的社會階級問題的討論,用另一種話題的熱議遮蓋根本問題所在,用另一種形式主義的二元對立取代原本實質性社會議題的溝通討論。
所以,迪迪埃用自己的視野為當代人提供的並不是對階級不平等的簡單批判或是政治鬥爭背後虛偽的揭露,更多的是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以去除當下我們看待自身社會問題的那層遮蔽,重新找回和自身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意識。因為,導致當下現實的源泉,並不是技術、也不是各類文化形式主義、身份政治問題,而是繼工業革命後,在互聯網和全球化背景下新的政治、經濟結構用新的話語體系重新包裝自己,延續著那個自韋伯和馬克思時代就已然存在的問題,直到今天,我們終於可以一窺它壯大成樹的整體樣貌。只是,問題還是那個問題,人已不再是那時的人。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