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給予你最憐憫的感化,也置你於最深刻的痛苦之中
自人類歷史緣起以來,人們對懲罰的形式便是多種多樣,各類酷刑、壓迫、奴役、羞辱、剝奪生命等等,每一種懲罰讓現代觀者看上去都是那麼具有恐怖的震懾力,特別是通過各種物理形式摧殘人的肉體,宛如地獄一般的酷刑和羞辱,受罰者透過肉體為媒介來感知這種痛苦,刑場本身帶有戲劇般的展示與傳播作用,由此向公眾散髮震懾力。這可以說是舊有懲罰最為嚴厲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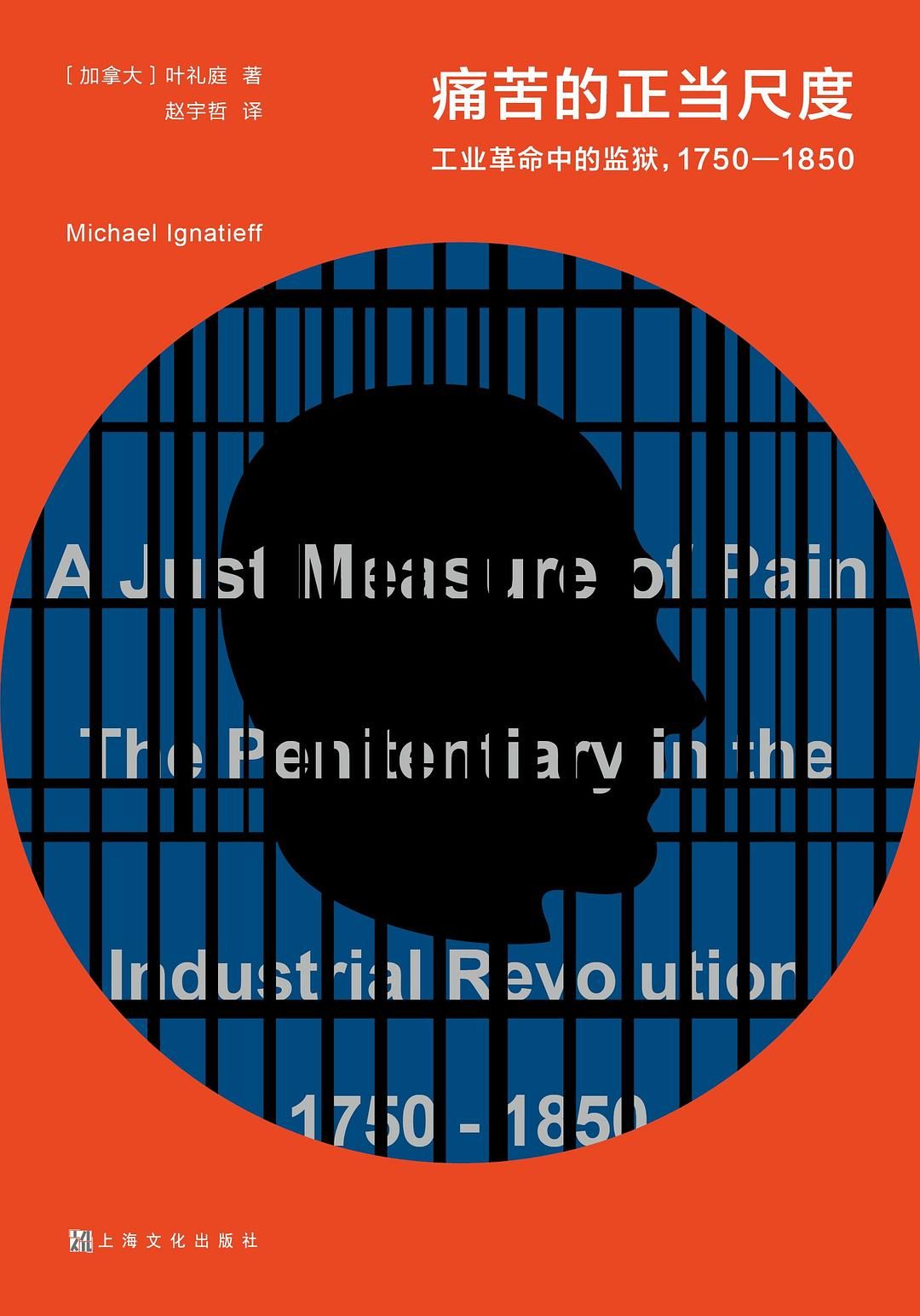
筆者一直以來都抱持一種觀點,即人類發明瞭監獄體系是一種文明的進步,告別了形式野蠻血腥的懲罰方式,以更為溫和的監禁管教替代了舊時代的黑暗傳統。但從葉禮庭工業革命時期的監獄史視角來看,人類懲罰的形式本質上陷入了另一種維度的痛苦之中,其雖沒有表面上那血漿噴湧,身首異處般的慘象,但卻是植根於心靈世界的深度摧殘,這當中值得令我們更為關注的便是,自監禁體系的思想誕生後,這一幽靈就不會一直存在於封閉的監禁機構內部,就類似工業革命後的新技術誕生一樣,即是一種思想,會隨著社會文化和需求進行傳播,無形中越過高牆,滲透進公眾社會生活的許多部分當中。監禁不是一種僅屬於懲罰和改造罪犯的文化,而是要逐步成為一種現代社會對人的全新管控方式。高牆的內與外,成為了這種秩序感、管教文化的一體兩面,當今不同的社會組織,其形態、架構都或多或少有著與監獄組織架構相同的形式,社會彷彿被同一套秩序籠罩起來,整齊劃一來運行。
作者透過18-19世紀工業革命時期懲罰形式的變遷史,並將眼光聚焦於當時英國的宗教、社會和經濟場景,探究了監禁文化在英國,特別是英格蘭地區的起源,從中可以看出——作為現代社會懲罰的最普遍形式——監禁,其背後最為直接的文化來源便是非國教思想,或者也可以簡單理解為基督新教道德倫理;該思想體系中對於理性的極度內化、高度自律性與追求極致的秩序感共同成為了監禁文化的初始來源,並逐步隨著社會變遷衍生為更加細緻的現代監禁措施,而這套體系在與工業革命的生產需求和民主政黨們的政治利益下顯得是那麼地契合,以至於監禁體系在發展的過程中還吸收了工廠管理的某些方法,兩者的發展水乳交融,既不斷完善著高牆內的管控體系,高牆外的社會管理更是越發地有序,即便在實行監禁後期出現的種種反人道現象的出現和明顯證據反映監禁對於犯罪率的控制沒有明顯的作用的時候,新資本階層群體仍保有著對監禁系統的高度信心,對於監禁和道德改造的思想越發的根深蒂固,這對於新教文化中自稱理性的部分簡直就是一種最根本的諷刺。而擴散至全社會那秩序、「理性」的管制文化則成為與我們每一位普通人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正如作者在前言所提到的——「出現在高牆內的新權威形式一定與高牆外的階級關係和社會策略的變化有聯繫。」這根本就是新階級(資本主義)轉型對社會秩序的重構,新教道德觀結合了資本主義經濟生產的利益需求,共同在銘刻於道德制高點上的十誡條款顯得是那麼溫和但卻又處處散髮著冷酷的氣質,瀰漫進整個社會。
作者在結論部分的提煉中最富有啓示性的觀點莫過於其清晰地抓取出邊沁和托克維爾當時期關於民主的建設和思想,即民主參與在全社會中的擴展讓大眾的實體政治權利更為普及,而另一面卻對社會的越軌行為更加缺乏容忍,懲罰的形式也更加社會化和強調道德、心靈層面的規訓;民主社會如果從這一層含義來看待的話,沒有所謂的自由與更寬廣的包容,有的只是一套現成價值體系不假思索地普及和對邊緣群體極端缺乏的容忍態度,整齊劃一和高度秩序感不是獨裁政體所特有的,這在民主社會中更為普遍,並且這種對既有道德範式的匡扶、維護,是根植於內心而很少來自於外部。
到這裡不禁想起發條橙的作者,安東尼·伯吉斯為何在《發條橙》中對於善與惡的自主選擇權那麼執著地強調,以至於說出:
「有些罪行更加惡劣,其中罪大惡極的莫過於剝奪人性,殺死靈魂—也就是能夠選擇善與惡的自在之心。「 ——「寧願要一個人們自己甘願作惡的社會,惡行出自他們的自由意志,也不願意要一個被硬擰成良善,無害的社會。」
這本書可以說是對福柯的《規訓與懲罰》的歷史學補充,但我個人更願意將其看作是關於現代性的社會隱憂,而這一切的擔心再往前追溯,都是馬克思·韋伯那對於新教倫理悲傷的注腳。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