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有长(zhǎnɡ)毛自由吗?

选题源于炎炎夏日。我激动地穿上吊带并作大鹏展翅状拍照发给老妈,她秒回“好看是好看,就是胳肢窝得清爽些,露出腋毛有点羞耻”。
而这,成功激起了我(身为女儿)的第一反应“你怎么能关注腋毛甚于关注我!”,和(身为建构主义者的)第二反应——“为啥胳肢窝就得清爽?腋毛怎么就羞耻了?”
01
(脱)腋毛小史:腋毛怎么就(被)羞耻了?
哈,不出建构主义者所料。尽管考古发现人类在石器时代便开始脱毛,但那时不脱腋毛只脱头发,且脱头发也无关美学,只关乎生存——光头可以防止自己在战争中被敌人一把揪住。
羞耻则源于文明古国。在古埃及,体毛是不文明的象征,不卫生的体现。埃及艳后剃光了她所有的体毛(含头发),以显示她尊贵的社会阶层。贵族男人们也喜欢剃光胡须(再戴上假胡须),因为仆人和奴隶普遍留着胡须。作为上层符号的脱毛亦出现于古希腊、古罗马,富裕的男女使用剃刀、镊子、浮石、脱毛膏来满足自己。此时腋毛于男女的双标已初现端倪,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均以光洁身体示人(除头发外),男性雕塑却能看到毛发;古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如是说,“妇女应剃腋毛,以免让粗鲁的山羊在你的腋下找到自己的路”。

不过,上层符号终究只是上层符号,远未飞入寻常百姓家。直到18世纪末,男士剃须刀已然发明的时期,仍没有严格标准来规定女性如何处理自己的体毛。而今日的腋毛羞耻往往溯源至1915年的一场商业阴谋。那时,美国吉利公司首度推出女性专用刮毛刀,并在时尚杂志做了推广。广告中,模特身着低胸无袖晚礼服,高举手臂,露出无毛的腋窝,配文:“一个时尚女性说,腋下应同脸蛋般光洁。”两年内,它家的刮毛刀便卖出了一百万支。接着,各类公司喷涌而出,广告商很快通过杂志和电影中的图像来塑造女性的美丽标准,腋毛是粗俗的、恶心的、男性化的——腋毛正式被羞耻了。

然而,西方腋毛被嫌弃的一生怎么影响到了东方的老妈?我继续艰难地搜集资料,发现,除了“挽面”(女子婚前清除掉脸上的杂毛),古代东方人秉持“身体发肤,授之父母”的教诲,基本不脱毛。鲁迅1925年作《从胡须说到牙齿》,说“譬如腋下和胯间的毫毛,向来不很肇祸,所以也没有人引为题目”——那时自然是不脱腋毛的。李安拍《色戒》要求汤唯养腋毛,以呈现30年代中国女性的美,并说“连我妈60、70年代的人也没有刮,中国人没有那么多气味,对我来说,腋毛很性感,刮掉很可惜,我很乐意秀出来”。我还找到了80年代林芳兵和巩俐没刮腋毛的挂历照——直到80年代,不刮腋毛也是可的。是二十世纪末期“文化殖民”的深入,才让东方女性的腋毛也羞耻了起来。我的搜索结果显示,2010年前后,“女明星露腋毛”开始搭配“尴尬!”成为吸睛标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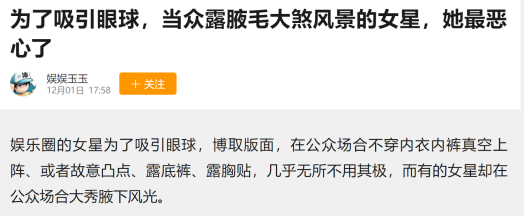
好在,腋毛羞耻有衰微之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者开始挑战僵化的女性美丽标准,在美国小姐大赛外的游行中,她们扔掉自己的剃刀和镊子(还有胸罩和高跟鞋)。2014年,本·霍珀的一系列摄影作品《Natural Beauty》让女性高抬手臂展现腋毛之美。2015年,许多美国女孩给自己的腋毛染了色,来反抗舆论和主流审美对女性的束缚。一项英国的调查表明,从2013年到2016年,剃腋毛的女性比例从95%降到了77%。

而在东方,女权主义者肖美丽于2015年发起“腋毛选美大赛”,挑战人们对女性腋毛的厌恶,她说:“我不是要所有人去保留腋毛,我只想说如果有人不想刮腋毛,其他人不应觉得这是恶心、不卫生、不文明或是不够女性化。”2020年,日本一家美容刀具公司推出一支女模特高抬手臂露出腋毛的广告,标语上写着大大的四个字“脱毛自由”——与1915年的商业阴谋形成绝妙互文。

02
腋毛,你怎么承受了这么多!
从纯科学的角度,腋毛是性腺分泌雌雄激素的结果,能减少细菌滋生、减缓摩擦以保护肌肤(谁说腋毛不卫生来着)。
但腋毛从来就不只是腋毛。如前所述,文明古国将脱毛视为上等人的象征,有钱有闲阶级方可剔除。而在父权制的扭曲社会中,男人对女人的腋毛也有扭曲的看法。一方面,他们假想面前的女人是尚未长腋毛的小女孩以满足他们的心理需要(何春蕤《为什么他们不告诉你》)。另一方面,因腋毛象征身体的成熟,腋下散发的味道能使人产生性冲动,他们便又赋予腋毛诱发性欲的意味。与李安所说的“性感”不同,腋毛的性吸引力连同被物化的女性,都是男性的“私有财产”。因而,当工业革命激发劳动力的需求,女性走出家庭开始工作,作为“私有财产”的腋毛走入了公共空间,男性便也急得跳脚,直呼“腋毛羞耻”了。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如是狼狈为奸,消费主义继续煽风点火——“购买我们的剃毛刀脱毛膏吧!买了就是优雅的文明的女性!”腋毛羞耻进而被建构为主流意识形态,随着好莱坞(里腋下光洁的女性)横扫欧美,再随着“文化殖民”植入东方,最后,通过social conditioning(进阶版“社会化”)代代相传,成为多数人所认同的腋毛羞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中,“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成为一支响亮的口号。脱腋毛,一个看似的小举动,代表了父权制对于女性的日常压迫。父权制借腋毛规训女人,要她们保持纯真,让她们自我消耗(脱毛所需的时间、金钱和心理能量令人压抑)。这种情况下,不刮腋毛与其说是个人选择,不如说是政治表态,以此批判父权制,挑战男性制定的文化习俗。(其实男性何尝不被规训呢?父权制期望男性的腋毛多多益善,所谓“阳刚的内卷”,腋毛少会则被骂“娘炮”)

然而情况在第三波女权主义运动又发生了转变,这时的女权主义者认为,自由表达自己的女性气质是对被物化的挑战——这让她们跳脱出父权与父权的镜像,而仅仅凝视选择本身。她们可以涂口红、穿性感内衣同时自豪地展示自己的腋毛,也可以不修边幅只修腋毛。于她们而言,拥抱“女性气质”并不表明自己内化了父权制,而是一种自主选择的自我表达,一种自我赋权。
总之,从科学到阶层到父权到女权到选择本身,腋毛,你真的承受了好多!
03
所以,我听不听老妈的?
说实在的,很长时间以来,比起不刮腋毛,更让我觉得“政治不正确”的是刮腋毛。(化妆同理,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自己不想化妆,但每当“啊我想化妆”的念头迸出,我内心都会产生罪恶感)因为我一直把脱毛/化妆当作父权制的审美标准与压迫,而身为女权主义者,应当身体力行地去不合作。然而,脱毛/化妆全然是父权制的压迫吗?有的人确实在脱毛后感受到了安全与舒适,有的人也确实在化妆后感受到了自信与愉悦。问题可能在,就算ta们为着自己的感受而脱毛/化妆,在这个充斥着男性凝视的世界,所有的自我赋权都会被解读为取悦男性——男性凝视只停留在你脱毛/化妆的外表,才不会管你的感受。这种情况下,我,身为女权主义者,是否应当避免做出取悦男性凝视的选择?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因而我也一直留着腋毛。是《有靠之天》与那个女孩让我灵光一闪,突然想通——女权主义是关于自由的。女权主义是为女性(和所有性别)想做的事赋权的。虽然曾经的性别平等可能意味着做和男人一样的事,不做父权制要求的事,但那是在一个女性权利尤其逼仄,女性甚至不能穿裤子的时期。一代又一代、各种各样的女权主义者撑开了女性权利的空间,如今女权主义不是父权的镜像。如果女权主义采纳“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思路,要求女性抵制父权所喜悦的一切,那女权主义就会向父权制靠拢,因为它同样要求了女性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非鼓励女性(和所有性别)做ta们想做的事。你可以爱化妆,同时反抗工作场合要求化妆的硬性标准,你涂着精致美甲的手与你把父权制的蛋蛋扯碎并不矛盾。
我低头看了看吊带下的腋毛,郑重决定:这个夏天,不刮腋毛了。不只是因为我想体验父权制下的小小越轨,身体力行地冒犯别人一把,更因为,我懒且我觉得我的腋毛很可爱。至于以后的春夏秋冬,刮与不刮都只是选择,看我的心情咯。

参考资料:
[1] 《关于“腋毛禁忌”的审美史》,
[2] 《腋毛被嫌弃的一生》,
[3] 《从胡须说到牙齿》,
https://baike.baidu.com/item/从胡须说到牙齿
[4] 何春蕤.《为什么他们不告诉你》.方智出版公司.1990
[5]How Hair Removal Became a Beauty Standard,
https://www.crfashionbook.com/beauty/a32332850/hair-removal-history-waxing-brazilian/
[6]History of women body hair removal,
https://www.allure.com/gallery/history-of-womens-body-hair-removal
[7] Why more women feel pressure to shave,
https://edition.cnn.com/style/article/why-women-feel-pressured-to-shave/index.html
[8] The Politics of Not Shaving in this Patriarchal Dystopia,
https://medium.com/bottoms-up/the-politics-of-not-shaving-my-legs-2600cd7ea23f
[9] The New Feminist Armpit Hair Revolution: Half-Statement, Half-Ornament,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