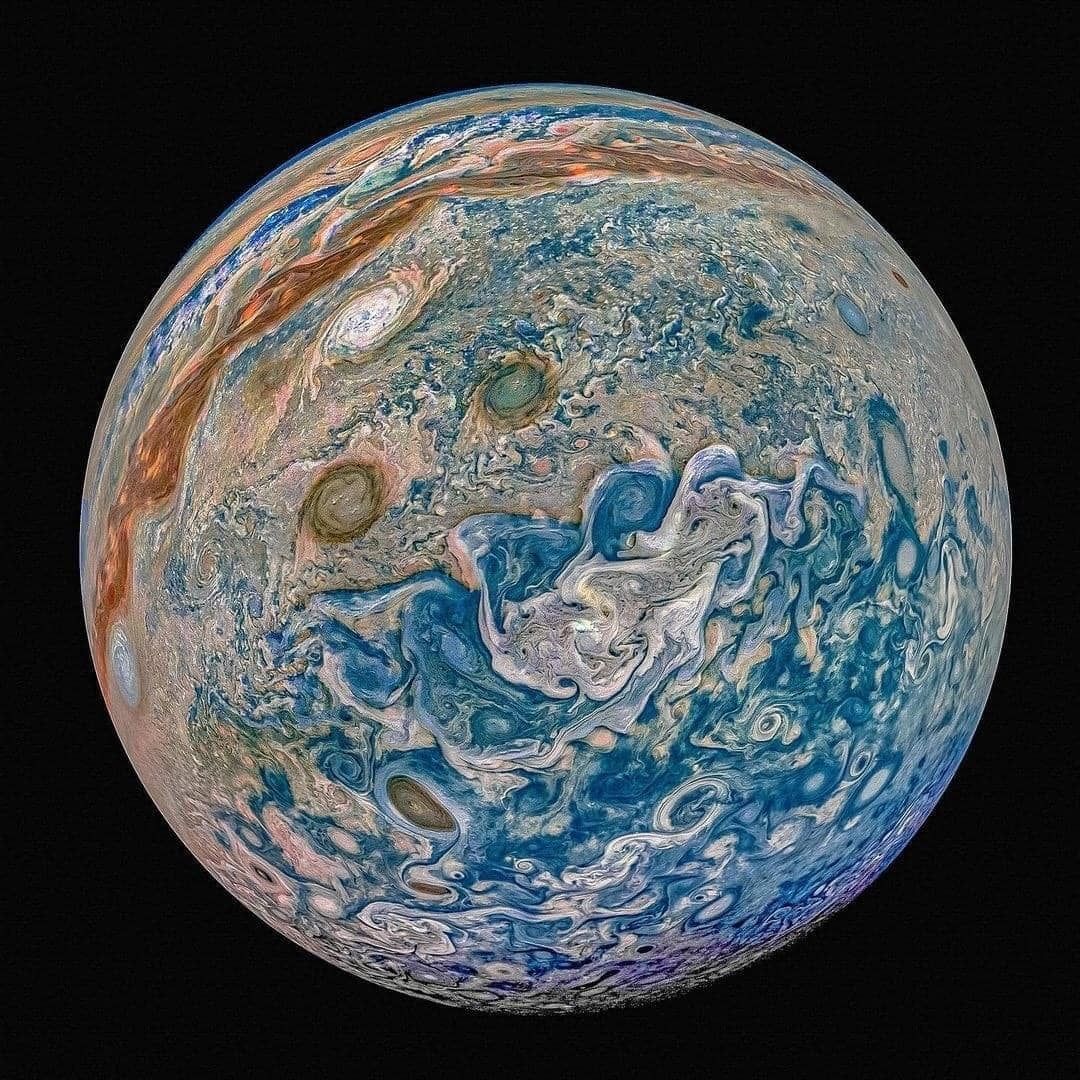複習旅行_四國遍路|高野山

(此文寫作完成後,於2017年1月刊載於印刻文學雜誌。)
參道兩旁的筆直杉木高聳入天,四周靜極;雨水點點打上地面,是唯一的細響。昏黃的常夜燈,將依然漆黑的天色,暖出一圈圈光暈。
突然一聲短促,啪,燈熄了。
秒暗。空氣緩緩滲來磬的低鳴,一聲過一聲。清晨六點。
伸手不見五指,我只得停下腳步,清冷的空氣彷彿也封住我的耳膜。我應該要害怕的。我怕黑怕鬼,現在卻僅能勉強靠聲音辨識方位;且我知道我的周邊,除了千年林木,就是無盡的墓碑與墳場。完全是鬼片場景。
我閉上眼睛,合掌扣齒,唸起南無大師遍照金剛,趁著磬聲繚繞,朝遠方深深鞠躬。那是弘法大師御廟的方向。
早課開始了。
再睜開眼,漆黑依舊漆黑,清冷依舊清冷。常夜燈司職整晚,與尚未升起的太陽交班,原該二十四小時不夜之山,唯有此時隔絕一切人為光亮。我應該要害怕的,而且我還是什麼都看不見。但我腦袋像被抽空,或被凍結,一絲波動都沒有。我重新邁開雙腳,潮濕的石坂道跟隨我的亦步亦趨。我試著將視線看進最黑最遠的那頭,那頭有光。
※
我從不知道什麼叫做聖地,直到上了高野山。
在四國走遍路的時候,遍路者們時常互問的其中一個問題便是「走完遍路後,會上高野山嗎?」得到的答案多半是肯定的,偶爾還會配個「當然啊這還用說嗎」的表情。
四國遍路八十八座寺院,認真說來,起終點都不在遍路道上。出發前,遍路者會先到京都東寺向弘法大師秉告自己準備動身,祈求一路平安。更正式一點的,則會以東寺為起點,步行前往右京區仁和寺、北區西賀茂的神光院,走訪這三座與弘法大師有深厚淵源的寺院,並在寺內拜請菅笠、金剛杖、納札箱這三項遍路基本裝備,稱為「京都三弘法」,算是遍路的行前暖身。而在走完遍路一至八十八番整圈之後,再往位於和歌山縣的高野山,到奧之院秉報結願,整趟遍路才算真正劃下句點。比較有趣的是,我在遍路上幾乎只遇到會不會上高野山這個問題,很少被問「來之前有先去東寺參拜嗎?」
有的人遍路一結束隨即上高野山,有的人會另擇他日再行前去。遍路本就沒有什麼特別規定,所有的「應該這麼做」,多半只是應該。只要不是故意違規甚至刻意破壞,幾乎不會受到干涉或指責,弘法大師也不會託夢懲罰你。
我分別在兩次遍路結束後上高野山:十月下旬,與十二月初,其間相隔兩年;一次楓葉剛紅,一次葉已落盡而初雪未來。可能因為行程太趕,或事前了解太少,或待的時間太短,總之第一次到高野山的記憶,幾乎都是模糊的,唯獨那裡的空氣感刻進腦裡,不曾忘記。
要問怎麼形容高野山,我始終只想得出兩個字:乾淨。
與青森縣恐山、滋賀縣比叡山並列為日本三大靈場的高野山,以可能略帶不敬的物理性質來說,就是個集體墳場。許多歷史名人、企業大家,都期望能與在此入定的弘法大師一同安眠。於是通往奧之院(即弘法大師御廟)的參道兩旁,遍佈著諸多僧人名將達官顯要的墳墓或供養塔,另也有一壟一壟的慰靈碑及無名塚。參道多長,墓園就綿延多廣。上高野山,等同走進墳墓堆。
但不知為何恐懼這兩個字在這裡卻是多餘。平常只要經過墳場,或遇上喪事,我總是後頸一繃,憋住一口氣,目不斜視扣緊牙關快步通過,心裡誦念當下想得到的任何佛號。我惡人沒膽又不知自己八字輕重,只得藉此希望與邂逅的靈體們相互解脫且明白彼此無意冒犯。
上高野山之前我並不知道高野山是什麼模樣,見識淺薄如我,也從沒去過地表任何一個聖地。準確點說,我是在遍路上、在與其他遍路者交談時,才確認「原來大家最後真的都會去高野山啊」這件事。本著「別人都去我也要去」的人云亦云,以及「如果沒去就不完整」的強迫症,在走完遍路後,沒做任何功課,連交通方式都是前一天才查,便上山了。
※
抵達奧之院的時候早課已經開始了。穿廊燈火在未明的清晨下搖曳,誦經聲一點一點地從門縫流洩而出。我有點猶豫地推開門,擔心會否因為遲到不能入內。
堂上正中央與兩旁跪坐著僧人數位。我在堂側脫了鞋,彎身快步覷座。同住在青年旅館的遍路大叔對我招手指指他身邊,我搖搖頭,只想自己窩在角落。
來聽早課的人比我預料的少,算算約莫十人。雖有矮凳,然多數席地而坐。院方貼心地在兩側燃起煤油暖爐,與堂內燈光燭火將整個大堂烘成一片暖。我自知無法長時間跪坐,便將自己盤成一團,倚著暖爐散過來的熱氣,慢慢驅走帶進來的一身寒;線香氣味盈滿,緩和了方才在黑暗中尋路的奔忙。
我時而閉眼,時而看向堂上背對眾人誦念經文的僧人。我不是佛教徒,雖然走了遍路,對日本的佛教依舊無知,我不確定是不是該稱其為住持。以日語誦念的經文聽起來陌生中帶有一絲熟悉,有些發音與中文相近,依稀可以辨識或猜測出應該是什麼字;又或者反正都是聲聲嗡嗡,知不知道究竟誦念的是什麼,可能也不重要。
過不多久,昨晚同宿的另兩名美國女孩也到了。在場有日本人,有美國人,有馬來西亞人,有台灣人;有遍路者,有背包客,有觀光客;有虔心追隨弘法大師的修行者,有單純好奇前來參與儀式的旅人,也有已經走了兩次遍路,卻還老記不全弘法大師俗名與生平的路人如我。
西元八一六年,弘法大師向嵯峨天皇請求賜與高野山,闢為真言密宗的修行道場,迄今一千兩百年。西元八三五年,弘法大師發願於高野山中入定不入滅,等待彌勒菩薩下生,再協助其弘化──這段文字當然不是我坐在御廟內堂裡反覆想著的,是回頭在網路上找到的資訊。坐在御廟內堂裡,耳邊迴盪經文如咒,呼吸吐納的是線香沉厚的木質味,腦袋是空的。前一天從香川搭巴士換渡船轉火車,整日奔波移動的疲憊尚未褪盡,我以為我會在早課時打瞌睡,不意卻全程清醒。沒有醍醐灌頂的靈光洗禮,也沒有法喜充滿的感動涕泣,有的僅是清靜和緩的空白,腦波全數下降,連成一道毫無起伏的水平線。這對我已相當難得。
要說唯一有的想法,應該是當我偶爾左顧右盼,看向身邊從世界各地而來的人們時,我總不免好奇,一千兩百餘年前的弘法大師,在踏出修行之路的第一步時,是否想過會有這麼多的人從四面八方匯聚而來,跟在他後方?若有,他是以什麼樣的心情,為這些後世之人布置規劃;若無,又是什麼樣的力量讓他持續?而這十幾世紀以來,之於這些跟隨著他的人們,他會想說什麼?
他會不會說:你們不要一直跟著我,你們應該去走你們自己的遍路。你們自己的。
※
若走最長的參道,約莫兩公里。抵達奧之院前會先經過三座橋:一之橋、中之橋、御廟橋。一之橋是參道起點,行過一之橋,便踏入靈場(墓園)區。整段路途除了御廟橋之後不能拍照,部分區域也有這裡那裡豎著禁止攝影的告示牌。我對拍照一事原本就懶,如今置身墓園,看遠看近都是墳;縱是如豐臣秀吉、織田信長、武田信玄、上杉謙信、伊達政宗等已成景點的古代名將安息地,也覺得還是不要打擾人家比較好,便樂得連手機都不想拿出來。死了本該落個清靜吧,結果鎮日有人在跟前來來回回還指指點點的,想想也夠煩的了。
但還是有些墓園的規劃十分……有趣,特別是企業墓園,有些會直接開宗明義地將該企業的代表物設計為墓碑,讓人一目了然。例如UCC上島咖啡的社墓前方就老大一尊刻著UCC字樣的咖啡杯;新明和工業株式會社則豎著一座蓄勢待發的火箭,便可知道這家企業與航太產業有關。而讓我瞬間失禮噴笑的是養樂多企業的慰靈碑,就是一瓶大理石鑄的養樂多胖墩墩地立在那裡──這輩子從沒想過會用可愛來形容墓園啊。
兩公里的參道,理論上半小時最多四十分鐘就能走完。但可能是被這些創意十足的企業墓園吸引,或整座高野山肅穆沉靜的氣氛讓人不自覺把腳步放慢再放慢,停停走走竟也拖沓了一個多小時。河川為界,行過中之橋,便進入了冥界;再過御廟橋,便是弘法大師所在。傳說弘法大師會現身在御廟橋那端迎接來者,所以上橋之前要先在這頭合掌禮拜,表達感謝與尊敬之意。
四國人對遍路者十分禮遇。在四國走遍路時,過往行人不分男女老幼,幾乎都會與遍路者行禮問候;離開了遍路,就算你將所有裝備穿戴上身,也不會再有這種待遇。然在高野山上,無論是身穿白衣,或手持金剛杖,或頭戴菅笠,只要能夠辨識出是前來結願的遍路者,陌生的溫暖招呼又會重現。不只在遍路者之間,有時一般旅客也會送上一句「辛苦了」。一段短短的參道,彷彿成了四國遍路的延伸。
※
早課在七點結束。
跪坐的僧人們接連起身,向本堂中央行禮,與前來參與早課的人們一一行禮,隨後離開。燈光燭火依然搖曳,線香氣息仍舊繚繞,門外透入一絲絲日光。天開始亮了。
所有人都走了我才起來,移到堂中央前,擰了一小撮淨香到香爐裡,跪坐放空了好半晌。我想著是不是應該跟大師說些什麼,拿不定該謝謝還是許願還是立志,又好像說什麼都多餘。
我走到堂側摸出鞋子穿上。早課人們散去,參訪的遊人還沒抵達。寺院門已打開,承接各業務單位的僧人們尚未就座。納經所還關著,我得等等再來。
我走出奧之院大門,看著自階梯而下延伸向前的參道,想不起上一次來時是什麼心情、什麼光景。我想著不過一小時前我才置身於黑暗當中,為什麼我不會害怕。是我認為即便自己不及格,但終究還是個鬼怪不欺的遍路者?還是我相信無論如何弘法大師都會保護我,一如在遍路時?或者總之這裡整片都是大師的地盤,既是聖地,哪容得下什麼來造次,根本想都不用想。
我想著當我的朋友們透過照片看我走在那些荒蕪的偏僻的空無一人的山路,總是語帶擔憂地問:「妳一個人不會怕嗎?」抑或有時遍路者們交換心得,偶爾濫情地來上一句:「一個人走,不寂寞嗎?」每當此時,我都會想起有次一個阿伯的回答。他說:
「不會啊,有大師一起。」
那是我至今得過最能安定心神的一句話。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