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育臣 | 做电影是把自己切碎了,抛出去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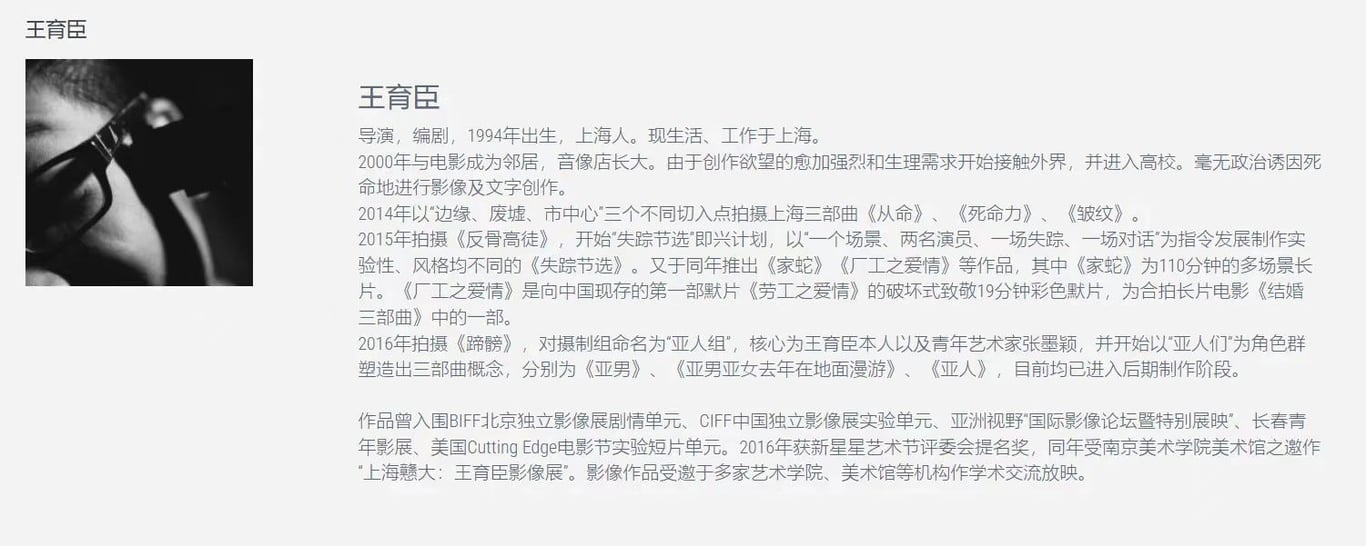
王育臣影片观影链接
/
我的剧组像是一个作坊
Q:你有非常多影片在cathayplay上可以看到,这些片子对演员、摄影指导和美术指导都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很多人毕业以后就遇不到这样强烈的剧本了。
W:对,毕业以后可能职业方向变化。我找工作人员也确实比较容易一拍即合。
Q:那拍摄前期你和组员会有详细的方案吗?
W:未必,看当天或者当地的情况。
Q:那堪景呢?
W:自己做dp的项目我自己看。有dp就一起。
Q:基本都是你自己完成。
W:分情况。如果摄影指导是我自己,那我不用和任何人过多交代分镜。如果我和dp合作,比如最近我的一个片子,和dp是第一次合作,那我会出分镜表和每天的镜头序列。
Q:你的拍摄肯定不如工业组那样完善,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要把自己从一些已定的繁文缛节中解放出来?

W:我没有那么生硬的转变,分情况,看我做什么片子,有些影片还真得踏踏实实走工业流。
看表达意图,比如我的新片《缺角镇》有一场密林的戏,它的意图是在全场过曝的炙热的阳光下,让每个人的症状呈现出来;就光这一句话,它就可以让我寻求合适的方式去成立。在《缺角镇》里方式是自然光。
每部戏看创作初衷。我觉得不存在解放与否,只是面对不同项目有不同做法。
如果现在有人找我拍网大,我也会按照网大的规矩一条一条跟下来,这是职业规范。
我目前最大的盲区是发行,而不是前期制作。我长期的限制点是认为拍摄电影本身更重要而不是用电影去干嘛。
当然近况或许是,连所谓独立电影创作里,导演都变成了某个人为了达到社会面成功的一个捷径。我个人无法理解,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他们TM脑子有病。做电影是一个把自己切碎了,抛出去的一个事情,怎么会变成吸纳个人利益的方式呢。“想出名”这个逻辑对我来说也蛮有特色的。
我不相信任何一个电影产业相对成熟的地区会是现在这样。扯远了,我当然知道剧组会是良好的练习,如果让你来参与,你肯定也是舒服的。但我总是觉得不应该只有少数人在这样执行剧组属于大家这个概念。

Q:那你平时会接烂活吗?
W:活就是活没有好坏,但如果你指的是一些重复别人广告创意的东西那我确实很少接这些。
最近我去山西,帮两位作者拍摄自己的长片首作,我做摄影指导。这个影片有关鬼魂的抓取,她们希望在外婆去世后抓取鬼魂,呈现这样一种感觉。像这样所谓的独立电影的创作,我会仔细和导演聊她们的意图,我能否做到我都如实和她们讲。这种我也当作“活”,但是投入精力和自己的作品也没差,工种不同而已。
Q:这类作品,其实作为摄影指导和美术指导挺好找工作的,有一定市场,这算是个玄机吗?
W:我倒也没有发现这个“玄机”吧。别人如果找我的话,他们一般都是觉得我除了摄影,或许现场的一些执行以及后期也能在剪辑方面帮助他们一些,他们也经常遇到预算有限的情况,一个人必须当多个人用。
Q:那你在剪辑的时候,面对素材会大幅调整吗?
W:因为本身就有剧本,所以肯定有原本的路径。在时间线铺完以后,在每一个段落里做个取舍。我和大多数人的剪辑模式差不多。
Q:那剪辑花费的时间多吗?
W:会,拍完后到剪辑前的时间是用来休息的。我得让自己回到客观状态,然后在实际剪辑的过程中,就会享受。
Q:你在一些影片里用过既定影像,就是一些老的录像带。
W:不同介质的魅力。
Q:你把录像带放进影片,同期的声音有做过?
W:声音是做的,我把它们嫁接在一起。
Q:你觉得你的片子的剧情成份、实验成份,哪一个多一些?
W:我从来没有实验。
Q:如果实验的成分上去了,共情可能会下来。
W:关我什么事。
Q:你会嗨爽。
W:我也没有嗨爽。素材的累积,和素材的配合,直接还是留白等等,虽然都是我个人主观的选择。但我在选择这种方式时,其实也是看客的角度。可能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公式,不管是不是广义上的剧情片,但我肯定是讲故事的,这个故事方式比较没那么公式化的时候,看与不看,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是个人的选择问题。
现在我的影片,每一场放映,至少总有几个人是共振的。踏踏实实说,实验片这几年在国际上也是一个蛮限制的东西,实验电影几乎可以像《一条安达鲁狗》这样的范本,或者私影像这样的东西,把自己框死。我很讨厌这样,如果实验真的如同实验所说代表一些自由倾向,那我理解;如果这些都是为了归类的话,那我一定什么都不选。现在如果你说我不是一个电影工作者,我也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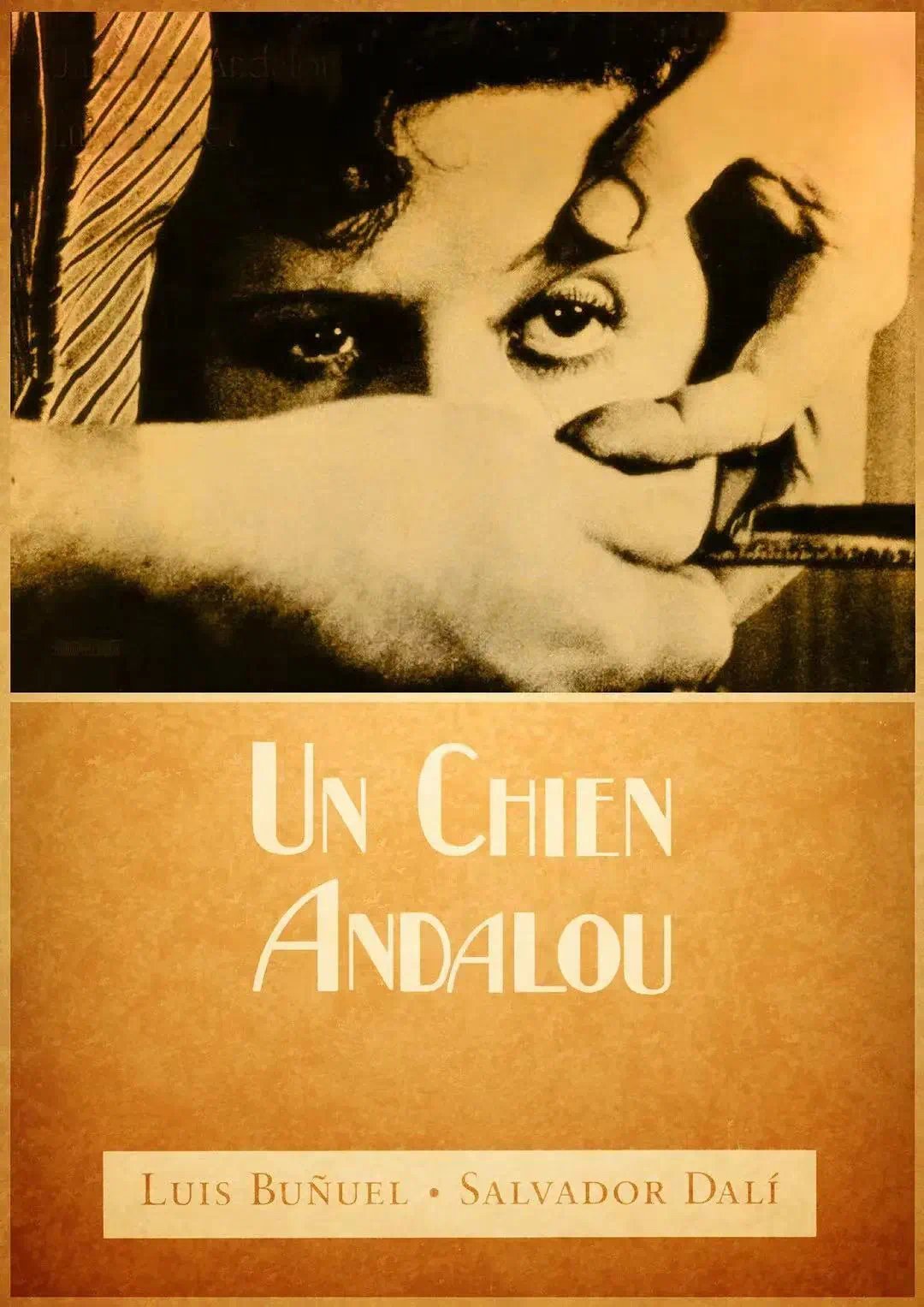
Q:你觉得你是亚逼吗?你的电影是亚逼电影吗?
W:我很难说是,我内心的外化就是一个屌丝而已。我拍的东西根本不是亚逼电影,亚字不是那个意思,是汉子里“亚”本身的多义性,亚健康、亚类型;哑巴的哑去口,恶心的恶去掉心字底,我用“亚”这个概念最早的意思就是“无心作恶无口作哑”,无力的现状嘛。或者你也可以说是亚洲人,包括“亚男”这个非常中国特色的名字。
但我自己的感受,在一些放映中有些比较外化的边缘群体,他们好像比较容易共情。虽然我不理解他们,但他们可以get到一些东西,我真的蛮开心的,某种程度我也确实试图为他们说些什么。
Q:你这些年拍摄的类型也变多了,比如拍了MV,那也是一个很有个性音乐人的MV。
W:互相尊重。你看到那种个性特别强的艺术家,他们和我合作的一瞬间,就直接达成了信任度。这也是我特别喜欢一些类似艺术家的原因。
Q:你自己的影片也涉猎了LGBT题材,这是出于纯粹的创作,还是根据大环境市场有调整?
W:我们没有市场。外面的市场和我无关,我也从来没有进入市场。当然,也一定为人群有所表达,在我的世界里从来没有性多数性少数。也会给素人演员量身定做角色等等,这毫无疑问。
Q:这是你为演员们的付出。
W:当然要为他们付出,你在说什么?(笑)张植绿我给他写过一个比较满意的角色,叫亚男。他为了角色看了大量素材,很多观念意识都有变化,这个角色和他合为一体,他在角色中呈现了自己内心中非常敏感柔软的部分。这是非常正向的有趣反馈。
Q:我能问下是怎样的素材吗?
W:(笑)这个你去问他。我只管结果。
/
张植绿是我的muse

Q:那我们简单聊一下张植绿。他那么多年作为你的御用演员,这些年也有些变化,从童星变成演了很多古装剧的演员。
W:对,我小时候看过所有的“龙儿”都是他演的。
Q:我搜了他最近的一些片子,都是些网大。这些是他赖以生存的工作,和你的影片完全两个世界。你了解他内心关于这些的想法吗?
W: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在我们的片场可以带来更松弛的状态,而可能工业体系中他的部分就是用“职业”去应对,有时候表演的快感不多但是他都会认真对待。
其实我的剧组虽然他演得很爽,但我一直愧疚于我和他合作的十年,我始终没法把他带到观众那里。而演员其实很脆弱,大多数演员其实需要很多很多观众一起告诉你,你演的真好,才能真正获得最直观的演员的自豪感。我剧组其实还有其他演员也都是10年的合作关系。他们可能相对职业都比较各异,有些属于职业演员的困惑就不太会影响他们。
/
上海等同于繁花吗?是观众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Q:你的影片都有关上海,可能观众如果要代入,就必须对上海熟悉,或者对长三角熟悉?有一些地缘的问题。
W:地缘很重要。但这个问题先放一边,不妨还是交给不同语言体系的观众去看吧。哪怕我的片子在上海,也有人说一看就不是上海的作者做出来的,大量的上海人也是没办法接受我拍摄的上海的。地缘对创作很重要,但我认为我戏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是人的情绪。对个体情绪比较重视的人,敏感的人,这样的人可能更容易接受我的片子。
Q:你喜欢今村昌平,他的东西有些人类学的痕迹;你都拍上海,也可以认为是有些人类学。从今村身上,你觉得最大可以吸取的点是什么?
W:这种深入的影响是不自觉的。
Q:但你拍上海市区其实越来越少了。
W:县和市区的差别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
Q:我指的是绚丽多彩的一面。大家以为的上海是小时代、或者繁花。
W:你觉得是我的问题,还是他们的问题?(笑)
Q:我研究了你过去几部拍摄上海的地方,你基本上喜欢集中在南片的乡镇,比如南汇、松江,北片比如偏重工业的宝山之类的,你没有拍过。所以还是想多保留一些江南水乡特色吗?
W:偷偷的告诉你,我有些地方取景甚至到了嘉兴。场地其实还是根据需要去找的。场地和空间的连续性,对我来说大于时间和确凿的支点。
Q:有时候你选定了一个地方,你就觉得必须在那拍。
W:对。你看到我的影片中,也出现过东方明珠。如果东方明珠是一个能够让我自由出入的地方,比如可以让我十年如一日的在那打游击,那我会拍它。但它不是,它甚至只有游客会出入。东方明珠对上海人来说也是一个有距离的地方。
Q:你有想过王家卫是否会有兴趣来看你这样的上海独立影像。
W:我没想过。
Q:你祖籍是上海吗?
W:我祖籍就是上海。我生在莘庄。
Q:那你说的是上海话,本地话,还是莘庄话?
W:我家里都说上海话,但我中小学老师都是北方人。社会又推普,我们又特别配合,导致我只说普通话。
Q:你应该还是会上海话吧?
W:我洋泾浜。只能听,你是杭州人,可能上海话都会比我好。
/
什么是正统?什么是主流?
Q:再回到你的影片,每一年你会要求自己进步一些吗?我指的对创作内在的进步。
W:我不刻意想这个问题。完成更加重要,进步与否是别人说的。我没有资格说我有没有进步。
Q:那你有没有什么目标,不是外界的目标?
W:内在目标确实是有,比如内核要再强硬一点。比如,我可以不要再借助血浆、暴力等来表达焦虑。
Q:那你曾经有机会,或者有想法想走一下“正统”之路吗,比如创投?
W:我怎么主动去弄??我已经每年主动拍那么多片子了,本能就是这样。项目化的东西,我能力问题没法主导。当然,如果有人来找我,开这扇门给我,我当然ok,我也非常清楚能帮到别人多少,但是没人找我呀。
Q: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你曾经和陈小雨导演有过紧密的合作。他的新片从创投到上映,是一条很正统的路。
W:他最夸张的天赋就是,他把许多制片发行的活也干了。从发行到包装,我看到的作者里只有他一个人是这样自己做还做得很好的。对你这样的创作者来说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
Q:一定是。他是一条路,你也是一条路。
W:我不是哈哈哈,我是死路。
Q:因为你没有一项可以长期坚持的路?
W:我长期的事就是创作。
Q:我指的拍片之外。因为现在很多人不把拍片当作一条路。
W:这是对的,因为电影没有那么重要,这是这个时代的现状。小红书之类的媒介重要性还在稳步上升,我自己也常看那些分享。给你的一点建议是如果你要商业化就一定记住你做的是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可以是短视频,可以是电影。
/
无题
Q:你以前办个展是怎么个缘由?
W:策展人郑闻看得上,以及美术馆非常保护我。
Q:那几年独立电影的状况比现在好很多。
W:我个人也很感激那几年美术馆的庇佑。其实那时候因为影展的停办,打击独立电影已经在进行了。
Q:现在还有类似的美术馆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吗?
W:要愿意的话也可以,但我近期不太想麻烦别人。
Q:也有勇者,比如《备忘录》。
W:这是一个优秀的作者视角的作品,截取了他自己有关疫情的文献。这个文献其实需要通过大量作者各个角度进行的。
Q:但两年过去了,不可能形成了。
W:因为这个东西不会让你成功,只会让你受伤害。现在做电影大家普遍的目标是成功,而不是留下一些东西。所以你为什么要求他们做无利可图甚至会带来不必要麻烦的东西?甚至指望他们和小市民们共情?别逗了!
Q:但发自内心想做这样事情的人好像也在变少?
W:我个人认为在变少。在电影这样一个夕阳产业,独立电影这样一个不存在的产业中,创作者就是拧巴的,因为他必须做一些现在没人看的东西且坚信价值。
Q:你现在的片子比以前已经压下去很多了,是你自己的状态决定的吗?
W:是。
Q:你担心你年龄继续往上走,会越来越不先锋吗?
W:我不在乎。对我来说不存在往上走、往下走一说。电影不能改变世界,我也不能。但我能干预我的存在,使我的存在更加体恤身边的人。
Q:有没有新作可以分享下?
W:有一部拍完了没剪,叫《五至十二日的锦江乐园》,一个中阴身游荡的故事。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and clap, let me know that you are with me on the road of creation. Keep this enthusiasm toge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