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 | 以身体艺术之名 | 弗雷勒的地平线(IV)

许多朋友了解到弗雷勒的机缘是波瓦的“受压迫者剧场”,这一方面充分说明了剧场艺术的时代性,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弗雷勒教育学远不止“识字”,而是“识世”,认识到世界的问题并以身介入。
本文为这次弗雷勒集体纪念写作第四辑,来自永舞团的Myra,永舞团近期同样在纪念弗雷勒。这一纪念不仅以身体艺术之名,且多以跨时空对话的方式推进,对话的对象不仅是弗雷勒,有她在印度、山东和湾区遇到的舞者,也包括身在世界之中的你我。前三辑请看:
第一辑“一次集体纪念”
第二辑“容器的艺术”
第三辑“原来都是骗局”
适逢批判教育学者保罗·弗雷勒百年诞辰(见此前结绳志编译的纪念),在中国深受弗雷勒思想濡染的写作者和行动者,以集体写作的方式纪念了这位曾带给我们不断攀升的勇气与希望的实践哲学家。在相互的书写和对看中,我们觉知到弗雷勒思想所能触及之地如此广阔,正如他在教育运动中所不断怀抱着的——对世上所有受压迫者对话的信任,对所有[存有之物]流动性的信任。
这一系列纪念写作中,我们能看见弗雷勒思想扎根之处所生成的触角:解放心理学,受压迫者剧场,行为艺术中的雕塑,社区教育以及一种对话式的写作的愿景。虽然其中有的方法论或许尚未成熟,但因其将在实践中不断地反思、修正,而保留着成熟的可能性和未来应用的价值。关于受压迫者的概念体系如何在第三世界永恒地回荡,在行动者网络中如何保持一种广远的联结,是这次集体写作所能带来的一些启示。如同友人多好的书写:即使世界并未完全舒展,我们仍旧在相互的言说和行动中推进着地平线。
作者 / Myra Chu
特约编辑 / 可仔
01
数年前,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一座小村庄里,我协助教授“受压迫者剧场”深度课程。参与的人中有一位年轻人,面相平和低调,几乎没什么存在感。某天的课程中,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放松练习,之后是休息阶段,这位年轻人坐在冰凉的地上,突然泪涌不止,呼吸不断加速,身体开始颤抖,口水因失控而不断流出来,如此长达十分钟后,他才终于平复。之后的课程中,他好像变了个人,更放得开,也更享受其中。
在我的经验里,明白那是深度创伤在身体内不断累积的一场爆发,彼时我虽然已经是“民众剧场”的教授者,也遭遇过参与者各种不同的身体状况,但这位印度年轻人不断颤抖身体的画面仍然让我震惊。我没有去询问他遭遇过些什么,但可以想见,某些经历给他留下了非常深重的创痛。人所有历经的苦,即使抛诸脑后,身体也都记得。
两年后,我在中国大陆教授素人舞动哲学,遇到另一个年轻人。他平日很爱跳舞,旋转腾跃几与专业舞者无异。一日课上,自由舞动练习时,忽然见他掩面而泣,角落中抱住膝盖,像是兀自取暖。事后他告诉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哭,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舞蹈于他向来是种享受与乐趣,而在那次课堂上,他第一次在舞中落泪,好像连接到了真实的自己。这些莫名出现的感受和无以名状的情绪,无法用语言描述,能帮我们承载并表达出来的,唯身体而已。
02
更久以前,一个极度炎热的盛夏,我首次修习“受压迫者剧场”(Theatre of the Oppressed),彼时并不知道“受压迫者”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它能和剧场有什么关联。银发飘逸的导师在一束光中坐立着,语气温和地说:Everybody can do theatre, even the professional actors.(人人都可以做剧场,即使是专业演员)。笑声四起。
我知道这不止是一句诙谐的调剂,而是有其深意。之后看书,发现“受压迫者剧场”的创立者奥古斯都·波瓦(Augusto Boal)是个神奇的人,他一生从事剧场工作,但不为权贵阶级做售票式的华丽演出。相反,1960年代,当巴西在军事政府统治时期民不聊生之时,他在街头演政治讽刺剧,被抓进牢中,大刑伺候,双膝落下终生的损伤。后流亡美国等地,成为民众戏剧的开山鼻祖。细观其艺术实践,难以找到风格一致的艺承。他甚至从未推崇过布莱希特或亚陶(陆译:阿尔托),反而字字铿锵:保罗·弗雷勒是我的第二父亲。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这个名字,也才明白“受压迫者剧场”不单要以戏剧艺术的眼光去看,也要以教育学的关切与胸襟。

读毕保罗·弗雷勒的巨著《受压迫者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才了解波瓦创立“受压迫者剧场”的深意与雄心。弗雷勒在这本书中创造性地提出“提问式教育”(problem-posing education),并对长期以来服务于特定意识形态的“囤积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予以批评。他认为教学不应该是机械性的、由教师把学习内容传输给被动等着接收的温顺学生。那是一种他称之为垂直式的、充满精英意识形态的威权主义教育。
而身为一个进步主义的教育者,尽管必须对(to)群众演说,但也必须与(with)群众处在同一阵线上,也就是说必须尊重生活经验的知识(knowledge of living experience)。在平等的教与学关系之中,教师与学生对事物的好奇心得以展开、交流、激荡。受教者透过了解事物发生的成因、摄取所教授内容的深层意义,再通过受教者自身的认知经验,来重塑他/她的认知世界。
当波瓦满世界游走,跟不同国家地区的社会工作者、医生、农民、工人进行剧场实践,而不是拼了命去城市中心的舞台上演出,所秉持的,大概就是弗雷勒思想中的这一份确信。
03
一九六四年,巴西军政府上台,弗雷勒立刻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要在巴西搞“布尔什维克”主义,是颠覆性的“危险分子”,而被迫流亡海外十六年。
流亡前后,他发起识字运动,教南美洲甘蔗园里没日没夜干活的农民和黑奴学习认字,采取的不是传统语言学习中的死记硬背法,而是通过对话行动(dialogical action),从受教者的处境着手,而非以教授者的标准出发,尊重受教者从生活经验累积而得的知识。他提出识字(read the word)之前先要识世(read the world),两者同等重要。
弗雷勒称其要达成的目标之一,是指导普罗阶级发展他们自己的语言,而不是教育者权威偏狭的官腔,以大众自己的观点来发声,从他们的世界出发,也回归到他们的问题;以他们自己的语言描绘、设计出他们向往的新世界。
而当波瓦以此为基石建造了“受压迫者剧场”这座艺术圣殿,并喊出: Our body is the first word of human language,已然将弗雷勒的思想拓展进入了一个新的维度。波瓦认为,人的身体是一门语言,在剧场这个实验室中,他尝试令人们发展出他们自身天然的语汇,并在剧场空间中与他者交汇,形成身体的对话交流。与弗雷勒相同,波瓦也坚持“对话行动”,他创造了“论坛剧场”(Forum Theatre),以开放式的发问来引导观者介入、试图改变戏剧走向与帮扶受压迫者,而非奉献一出结局完整的戏剧,以娱乐大众收场。
若干年后,当我开始教授“受压迫者剧场”,很快发现“论坛剧场”是最受学生喜欢的形式,也是应对许多棘手现实困境的有效途径。在一次工作坊中,我需要在短短两三小时内,训练几位大学生从互不相识到完成一出关于环境保护议题的论坛剧场练习。或许是年轻人好奇又好学,我们推进地很快,从基础的打开身体练习进入到了议题讨论,最后他们以极其幽默的风格完成了这个论坛剧场,就好像已经排演了许久一般。当我们以身体介入环境议题的时候,即使只是在剧场空间里进行实验,也仍然已经是一个个行动者,而非只是看客或用嘴巴空谈环保的人。
如文字语言一样,身体语言也有识字(read the word)与识世(read the world)两个面向。剧场艺术,准确地说是“受压迫者剧场”,在这个意义上,不只是对身体语汇之可能性的探索思考,更完成了每个个体心灵深处的意识觉醒,包括生命意识的觉醒与社会意识的觉醒,它同时具有内在性与社会性两个面向,缺少任何一个,都无法构成这项工作。
如此再回看波瓦的那句“人人都可做剧场,即使是专业演员”,才知其严肃性与深意,竟深刻至此。
04
三年前,在山东潍坊一个叫牟家院的村子,我和当地的孩子们一起创作。彼时山东刚受到严重洪水的侵蚀,伤亡损失惨重。我们以此为主题编创舞蹈,就在村子里的晾晒玉米地上演出。一起工作的两天,我没有教她们任何动作或舞蹈技巧,而是反过来,请她们教我:村子里的生活是怎样的?什么庄稼要勤浇水?家里的农具要怎么存放,出现灾情可以如何求生防灾?这些稀松日常,她们再熟悉不过,我引导她们由此编出自己的动作,作为重要的内容放在舞作中。
孩子们一直很闹腾,但当我们去思考邻村受灾之惨烈,以及将心比心,要如何才能重建家园,每个孩子都非常认真,她们的同理心和创造力,超乎我的预期。后来我们一起表演给前来的村民和朋友们看,结束后我问她们,这次创作经历有什么感受?不止一个孩子回答:学校的老师经常会批评动作不标准,我们不知道舞蹈还可以是自己创作的。

之后这几年,我经常从“身体语言教育”的角度出发,与“未经训练的身体”一起工作。和素人身体的工作并非永远顺利,因为“未经训练”并不意味着“未经规训”。和孩子们不同,当与成人进行教学或创作时,时常会碰到僵硬或“失联”的身体,所谓失联,如用弗雷勒的话说,就是其情感存有(Affective Existence) 已然出现失序和断裂,抑或是意识窒息与情感窒息(Suffoc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and the Expressiveness )状态。以至于他们不能够自如地“识字”与“识世”,更无法自由地参与世界。这样的状况,往往需要缓慢和长期的工作,才能重新建立并找回与自身之连结。
出现失联的原因非常多样,有时是因为长期过度的身体劳顿与压迫,有时是巨大的意识形态裹挟所致,有时可能只是旧有的一场深刻创伤。当创伤无法释放,就会造成失联,而大部分人们对于自己所受的创伤,其实完全不自知。只有当特定的情形下,或进行解放身体的练习时,才会显现。
因全球性疫情的影响,去年以来,我被迫转为线上教学。在今年的一场线上教学中,有一位来自夏威夷的美国原住民参与,目前在旧金山湾区生活。和这个国家的许多人一样,她饱受肥胖症的困扰,不仅导致行为的不便,甚至也造成了严重的健康状况。当我们请每个人生发出自己的动作,轮到她的时候,她第一次站立起来,那个沉重的身体带给她的痛苦几乎冲出屏幕而来。她的动作幅度非常小,几乎看不出,但当我们给予反馈与支持的时候,她几乎流下眼泪。能看得出,她曾因为体态问题遭受过许多歧视与伤害。而在我们的工作中,任何形态的身体都是合理的,都具有原初之美。不会因其不符合大众标准就将其归入异化(alienation)的情境中。
弗雷勒曾提及一个词叫“身体的禁制”(Interdiction of the Body) ,在不同文化与宗教语境中,它呈现出不同形态的压制与禁忌。我喜欢借用这个概念,因为在我有限的教学经验中,从亚洲到美洲,这样的“身体禁制”无处不在,因着各个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对人们产生不同的影响。这看似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复杂困境,而我却在实践中看到了希望。
其中一个希望的来源,是当我们从文字语言转移到身体语言,亦完成了由二维平面向三维(或三维半)世界的转换。语言不再局限于咬文嚼字的龃龉,而有了立身行动之条件。伴随维度提升的,是一个更大的探索时空,和更多已经或尚未发生的可能。那里有治愈我们普遍性身心顽疾的法门吗?
05
弗雷勒曾在著作中一再强调教授者的谦逊品质,避免出现垂直式的灌输教育——那样的教育者便与威权主义者无异。而他也同时说明,从受教者的知识出发,不意味着必须永远绕着这些知识打转。出发(starting out)的意思是要从起点动身。从这点前往另一点,而不是指滞留(sticking)或固守(staying)。“我从没说过我们应该像飞蛾绕着灯泡打转一样包围在受教者的知识周围。从已有的经验知识出发,是为了超越,而不是为了固守这些知识。”
重点在于“超越”二字。从印度深受创伤的年轻人到夏威夷因体态苦恼的女性,我不仅看到了他们“识字”“识世”的意愿,也看到了超越自身限制的可能。在弗雷勒的历史观中,一切都被理解为是充满机会的,而不是决定论的。我们之所以能学会跃进,不是透过天生(the innate),也不单只有后天(the acquired),而是两者之间相互激荡而来。这是一个从生理、智能、道德观、形塑一场生命的过程。
当我进行民众戏剧或舞动艺术的教学与实践时,遇到过许多不同的人们:白领、建筑工人、清洁阿姨、阿尔兹海默症老者、智力障碍的孩童……我总会带领他们重新回到身体的原点,由零开始去细寻其脉络,生发出属于自己的身体语汇,如弗雷勒所说对一切指意符号(significates)重新定义,而非被迫接受任何意识形态中强加的知识与伦理。在此过程中,教授者亦为学习者,学习者亦分享其经验智慧,我们共同成为指意者 (significator),拥有权利去探索更多重建世界与己身的可能。并将我们所面临的困窘与束缚,透过身体艺术,转化为勃勃生机。
这过程中仰仗的,除了教授者言行一致的传授方式和坚实的民主意识之本心,便是我们这具三维半时空维度里的身体。它所隐含的秘密与智慧深远难测,随着年岁的增长,体态与感知不同,过往的范式与惯性被推翻,又被授予了新的机会重新去了解这一场生命馈赠给我们的奥妙惊喜。
另一个与文字语言的显著不同,是身体语言乃是普世性的。世界上没有哪个人种会读不懂另一个人种的身体语言,这种交流不仅发生在不同肤色的男人、女人、神祇与祖先之间,也发生在所有其他的生命形式中,包括了树木、动物、走兽、飞禽、整片土地、河流与海洋——当我们抱住一棵树,所感受到的踏实与安稳是如此真实,这也从科学的角度得到过验证。因此,这不分肤色、不分民族、不分种类的普世性的身体语言艺术,我称之为“众生的言语”。
它是根本性的,是迷宫,是深渊,是梅洛-庞蒂所称“身体是世界存有之容器”,是海德格尔哲学中所谓“大地式的存在”。
而在弗雷勒思想影响下进步教育体系的身体艺术中,我想要再度强调这一点:它并非机械性地学习某种知识技能,亦不为娱乐或达到某种美学标准而存在,而是每一个有情众生阅世、阅己的根本。也唯有真正自由、摆脱规训的身体,才有可能带来头脑和灵魂的终极解放。这是一条愉悦而漫长的道路。
我对于身体艺术的解放道路之笃定,或许是弗雷勒所说“未经检证的可行性”(untested feasibility)。 它包含了对于可能梦想(possible dream)完全的信仰——只要那些满怀希望的人能够去创造自己的历史,理想国度终将实现。
也许弗雷勒是比我更加顽固的理想主义者吧,看看他说的:“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创造,也再造自我,成为主体与客体,成为人,成为嵌入世界的存有,而不是适应世界的存有。最终,我们应该拥有梦想及推动历史的动力。没有梦想就不会有改变,没有希望就没有梦想。”
06
身体艺术作为进步教育者的传授与实践,某种程度上说,是筚路蓝缕,没有先迹可循。然而波瓦说,剧场艺术无法陡然精进,唯有“Learn by doing”。作为一个教授者,没办法,只能一步一脚印,如弗雷勒所说,像“金钉子”(golden spike)一样,把现在和过去做连接,深入每个事实行动及动作的表象,融合所学,将各个点连接成线,再成面,重新认知世界与己知。不断推翻,又不断重建。
这个过程里,弗雷勒像是身边一位耳提面命的尊者,时刻告诫你:警惕对知识的占有与自傲。他曾谈及一些虚伪的教育者,当声称要给学生授权时,实际上是在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
“我们能否创造出让社区成员自我授权的结构,取决于这些社区能在何种程度上应拥有自己的技能,而不再需要我们的存在和技能,从而防止了新殖民主义的出现。”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身体艺术不应有权威或认证的存在。我们有且仅有的,是每个人独特的身体,能教授我们的,只有它本身的智慧。
弗雷勒对此用了一个词,翻译过来,是四个字:戒慎恐惧。“进步派教育工作者的伦理,要求他们坚持自己的民主梦想,尊重受教者。因此,不会去操控受教者。进步派教育工作者应保持戒慎恐惧的态度,进行他们的教育实践,必须时时张大眼睛,以全身的精神气力警戒自己,也必须要求自己变得越来越开放、率真,越来越有批判意识和好奇心。”
瞧,他就是这样不近人情的理想主义者,不仅引领你去反思探索,也时刻警醒你不要沦为你最初所反对的人。可是,我们是如此庆幸拥有弗雷勒,在充斥专制威权之压迫、菁英论述之持续诱惑的世界中,他竭尽所能点了一盏灯,让我们在对平等、自由、公平、善意的追寻之路上,不至暗淡无光。
我们此刻身处的状况之艰险恶劣也许尤甚弗雷勒的时代所面对的:这是一个不符合既定章程规范就可能被嘲弄和打压的世界;是一个强调效益工具性远胜于价值与体悟的世界;一个崇尚消费快感而漠视彼此身心连结与扶持的世界——如果不努力拥有万千元的化妆品,你就不可能是美的。在被动强加的欲望的驱动下,彻底失去与自我、他者及万物的连结与依存,成为原子化孤立羸弱的个体。
弗雷勒百年以来,世界并没有按他希望的方向发展。我们如今怀念他,不靠神化他的理论或推崇他的话语,而是在每一个细微的举动中,辉映弗雷勒思想的烛照,在重建世界与恢复人性的过程中,努力维持共同“希望”之不灭。那也是他最终的愿望。
“进步的教育实践永远都在进行揭露真相的历险,它永远是一种显现真理的实践。”既是历险,谈何容易呢?
可他好像睁着那对有神的大眼睛,就这样看着你,看你是否言行一致、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坚持、是否最后选择了更轻易的路。然而他似乎就是有股力量,让你不忍令其失望。
“我一直充满着希望,希望他们没受到那些务实论的诱惑,而顺应了这个世界。”
他的希望,便是那股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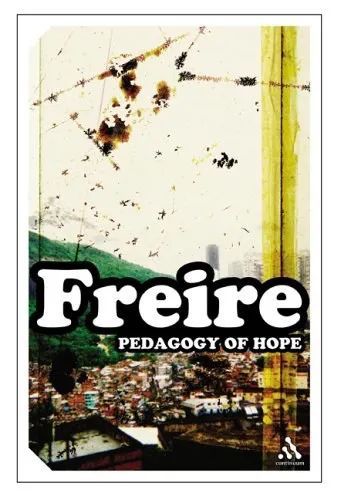
做身体艺术的教学探索,孤独而艰难,时常碰到一些犹疑困惑,然念天地之悠悠,无人可予诉说。便假想如果能够请教弗雷勒,他会如何回答。读完他的最后一本著作《希望教育学》后,我想我已经知道了他的答案。
“教育是一种政治行动,一种爱和洞察的行动,仅有同情心是不够的。”
小老头抿了抿嘴,扶了一下眼镜,深邃的眸子望着我:
“它是这样一种工作,要求那些从事教育活动的人培养特定的爱,不仅爱他人,更要爱教学所包含的过程。没有爱的勇气,没有不轻言放弃的勇气,就不可能有教育。”
致敬保罗·弗雷勒。
作者和特约编辑介绍
Myra Chu:旅美身体工作者,民众剧场实践者,素人舞蹈艺术家。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学硕士,曾任深度调查新闻记者,获有亚洲普利策奖之称的“亚洲出版业协会”等新闻奖项。后从事身体艺术的教育与创作,以“受压迫者剧场”连结和服务不同群体,实现个体生命的压迫疗愈和转化。独创“生机舞动”的素人舞蹈哲学,以期通过身体艺术的探索,实现生命意志的追寻与解放。公众号:Wingdancetheatre。
可仔:写作者,行动者,运煤工与面包师的女儿。
Posted in 教育
最新文章(持续更新)
176. 教学法何以成为一个人类学问题
177. 书讯 | 英文人类学新著 | 2021年9-10月
179. 为结绳小编们发电
180. 人类学的波拉尼奥:费尔南多·克罗尼尔和他的自然与国家之书
183. 深度访谈|行走阿富汗的人类学家:塔利班是一个被动接受的选项
184. 以身体艺术之名 | 弗雷勒的地平线(IV)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