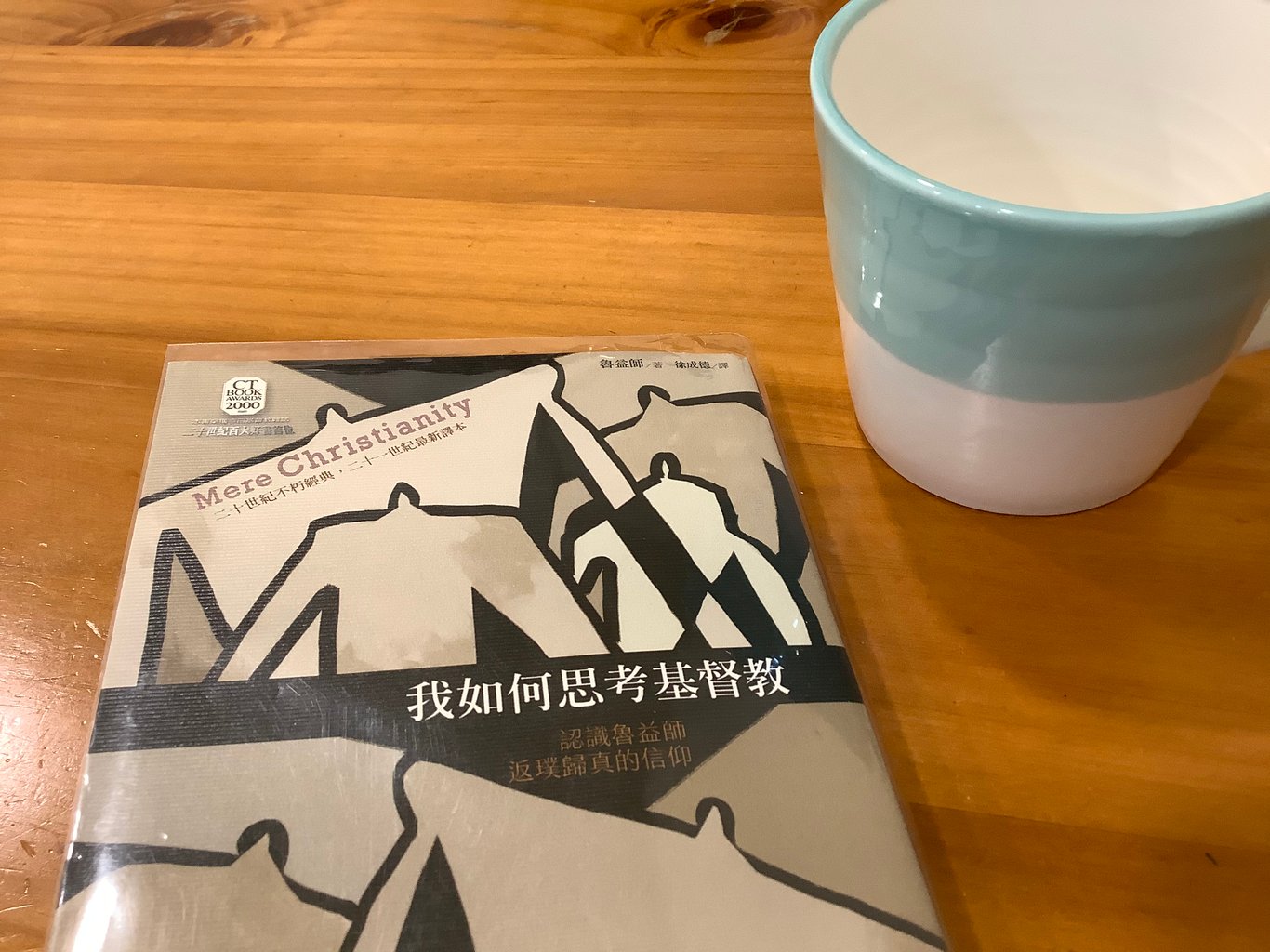當這個世界被區分為「我們」和「他們」
「我們為什麼製造出玻璃心世代?」這本在2020年出版的書特別之處,在於它並不如同其他的心理學書籍,只從個體心理學的角度來探討健康的心理成長所需要的因素,這本書從社會學、道德倫理學、政治學等等的角度,思索現在正在成長的年輕世代,他們在心理上的共同傾向,是什麼使他們(以作者的角度而言)「更加脆弱」呢?
年輕世代的脆弱,果然是被過度保護的結果嗎?那麼,什麼是「過度了」的保護呢?在這本書裡,並不是企圖在親職教養上,畫出實際的行為界線,而是在學說理論上,探討這個「過度保護」的思想根源。
二十世紀蓬勃發展的心理學,是否過分灌輸了我們一個觀念:「失敗、羞辱和痛苦經驗,會讓自己永遠受損。」我們被教導要修復這些損傷,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與金錢,還不一定能收到成效。如果我們接受了這個前提,那麼「如何避免任何可能造成創傷的情境出現」,這種極端重視安全的教育思維,就有可能勝過其他我們想要教給孩子的能力:包括如何從失敗中重新站起來、如何以正向的態度面對負面的經驗,如何不「過度推論」所發生的負面事件。
作者歸納出幾個我們不自覺正在教給孩子的思想模式,而這些有可能使他們「更加脆弱」。包括情緒推理與災難性思考、以偏概全、二分思考、標籤化,以及歸咎他人。簡而言之,就是一種:把自己的感覺放大,並且做出過度推論的思考習慣。
這些思考模式當中,最具傷害性的,應該是「受害者」的思考傾向。”他們的基模已有兩個空格準備填上,一個是「受害者」,另一個是「壓迫者」,而每一個人都能帶入其中一個。”
書裡的一個例子,是卡莉絲福斯特的經驗,卡莉絲是黑人女性,她先生是白人。有一次先生車禍住院,她著急地想要向醫院的醫護人員說明先生的情況,但是卻感到自己被忽略,不被當一回事。在憤怒的情緒裡,她解讀醫院的工作人員,一定是因為她的種族膚色,所以才不理會她說的話。在理智快要斷線的當下,她差一點就要破口大罵:「這都什麼時候了?我還得應付這些狗屁種族歧視嗎?」
但是她並沒有讓自己的情緒繼續推論下去,她先深吸了一口氣,意識到自己的壓力太大,整個人被情緒淹沒,所以才會把醫生護士一股腦地當作種族主義者。如果不是在這麼大的壓力和情緒中,她不會這麼想事情。奇妙的是,當她開始改變緊繃的敵視態度,醫護人員對待她的方式也開始改變。她才忽然醒悟,原來並沒有人因為她是黑人就看她不順眼。
可惜的是在現實中,「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往往加強我們原本已有的部落主義傾向。我們在思想上,被植入了「我們」和「他們」的思考模式,而選擇在一切的議題上對立。
不同族群的對立被激化,一開始的時候,或許是為受壓迫的一方爭取權益,但是當它被過度操作的時候,似乎也有可能演變為這當中沒有任何一方得益,唯一得到利益的是背後的操盤手。
“用這種方式思考,很快會把世界切成圈內和圈外---一邊是信徒,一邊是異端;一邊是好人,一邊是壞人……………我在這種團體時發現每個人的看法都一模一樣,立場一致的議題多到可疑。”
但是「共同人性認同政治」,比「共同敵人認同政治」有更好的效益,更能形成能夠改革社會的力量,作者以馬丁路德金恩為例子,馬丁路德將各種族和宗教的人稱為「兄弟」和「姊妹」。他的演講,和政治訴求,能激發起人的心裡對愛與寬恕的渴望與信念,
美國的民權運動者寶莉莫瑞,在一九四五年寫下一句話:
“我願以正向包容的方式拆去隔離…………..當我的弟兄試圖畫個圈子排擠我,我願畫更大的圈納入他們。當他們為少數人的特權出聲,我願為全人類的權力吶喊。”
當我們不再把自己定位成「受害者」,或許才能夠擁有為自己爭取權益的力量。敵人並不是「壓迫者」,而是造成壓迫的制度本身。將世界劃分成「我們」和「他們」是很容易的,因為人心原本就具有部落主義的傾向。如何能將「他們」變成「我們」,才是那個值得去努力的目標。
聖經上說,要愛你的仇敵,為逼迫你的人禱告,或許是看見了這個真理。因為壓迫者也是受害者,同樣受害於一個不夠公義的社會型態。
書裡提到馬庫色在一九六五年的文章「壓抑性容忍」。這篇可怕的文章說要讓受壓迫的多數獲得他們應有的權利,可以用「壓制和灌輸思想」的方式來達到目的。為了平衡原本強弱失衡的社會現況,必須反過來「壓抑」原本站在壓迫的一方。他說:「如果路被有系統的壓迫和思想灌輸阻礙,重新開路或許需要顯然不民主的手段。」「要讓世上受壓迫的人得到解放,必須先壓制他們的舊主人和新主人。」
馬庫色的這篇文章,令人不寒而慄的想到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所發生的事。這段歷史,或許可以作為馬庫斯革命理論的演繹。
類似這樣激發仇恨與對立的操作模式,我們是否可以說,直到今日,仍然在政治、網路輿論的領域可以看見它們的存在呢?這兩個領域的共通點,就是個體性的模糊不清。去個人化削弱了自制,讓嗆聲文化橫行無阻。
反脆弱需要脫離受害者的心態,不讓負面念頭掀起強烈的負面感受,因為負面感受會回過頭來激化負面念頭的推理,陷入回饋循環裡。分析悲傷的源頭有時會有幫助,但其他時候,直接讓那個呻吟不已的聲音停下來,是更好的做法。我們並非受害者,因為我們並非沒有選擇。”除非你認定一件事悲慘,沒有一件事是悲慘的。除非你為一件事滿足,沒有任何事能帶給你幸福。”
我們可以教給下一代的,或許不只是如何避免傷害的發生而已。停止受害者的思維模式,能夠停止對抗性的思維,也更有利於建立一個具有包容性的社會。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