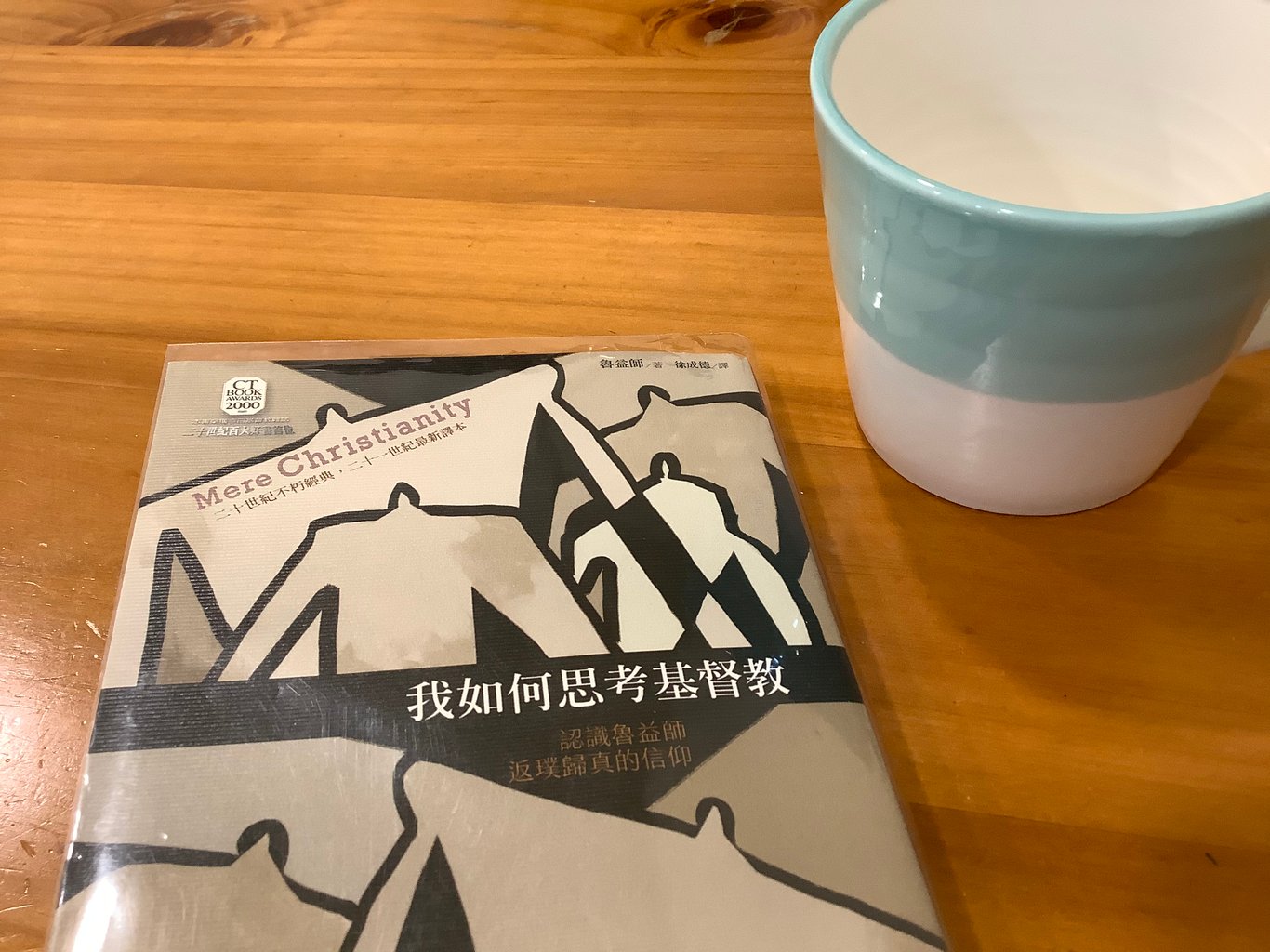平野啟一郎《日間演奏會散場時》

蒔野聰史和小峰洋子相遇的時候,並不是一個適當的時機。蒔野在演奏生涯不為人知的低谷,而洋子已經有了未婚夫。
但是兩個人對此次的相遇印象深刻,原本他們可以就此成為在彼此人生中的過客,但初次見面所留下的印象,如同一個巨大的阻礙,矗立在各自原本的人生藍圖前方。
就好像是在規劃的旅途中,在旁邊突然出現的一道門,如果打開那道門,自己的人生會變成什麼樣呢?這或許是每個人都曾經想過、無法放下的問題:如果那個時候、打開了那道門⋯
蒔野和洋子都因為種種原因錯過了那道門,也因此彼此都成為對方的生命中,那個獨一無二、最珍貴的存在。那些未能擁有的回憶,或許才是最珍貴的。沒有機會相愛的戀人,於是成為內心深處的最愛。
這個故事讓我想起平野啟一郎的另一部作品「那個男人」,講的都是那些沒有機會經歷的人生。我們只有一次機會,沒有選擇重新來過,於是作者筆下步入中年的主角們,都在某一個時點,突然意識到「在另一個選擇中,另一個地方的自己」。現在的「我」真的是自己真正的樣貌嗎?又或者本來有另一種可能,「我可以活得“更像自己”?」
從年輕的時候就往著一個地方前進,然而卻在某一個時間點,警覺自己「正在偏離正軌」。
在眾人面前表演的笑話,只有她知道自己真實的想法。一場所有人都讚不絕口的演奏會,只有自己知道演出已經到達瓶頸。
但所有這些的「說不出口」,只能期待有「什麼人」了解,唯有這個想法能成為救贖。
對於蒔野來說,洋子就是一個這樣救贖般的存在,可以從四十年來構築的生存方式底下,看見那個真實的自我。
因為連自己也漸漸看不清了,那個真實自我的樣子。會不會就這樣,一直彷彿過著他人的生活而活下去。
洋子究竟是不是蒔野生命中的最愛呢?這個問題或許牽涉到「什麼是生命」。在閱讀這個故事時,我忍不住思索,在「人」這個存在裡面的分裂與拉扯,人似乎由許多面向構成,有身為天才音樂家的蒔野,但也有一個普通的中年男子蒔野,不同的蒔野的需求都不同,無法判定洋子就是最適合他的伴侶。蒔野也感受到,經紀人兼妻子的三谷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妻子對他信仰堅定的愛,支持他度過演奏的低潮,但是對於蒔野來說,有一件事仍然是如同真理一般無法否認的:那就是他的生命如果沒有洋子,永遠也無法完整。
對於洋子來說或許也是如此,在遇到蒔野之前,她的生命看似完整,但是蒔野使她意識到那個她沒有正視過的自己,那個陌生的身為影像創作者,充滿人道關懷的父親,究竟在自己的生命中留下什麼影響,是她不曾認真想過的。四十年來,她努力活的是沒有父親的自己,假裝已經擁有的一切已經足夠,相處得來的戀人、充實的記者工作⋯但是蒔野用一種特別的眼光看她—是那位創作出「幸福的硬幣」、和「達爾馬提亞的旭日」這些傑作導演的女兒。
這部小說很巧的是,和上一本看的小說「寂寞終站」一樣,也引用了德國詩人里爾克那些充滿死亡預感的詩句。洋子在伊拉克採訪遭遇恐攻時差點喪命,作者用「魂斷威尼斯症候群」解釋兩個人陷入戀愛情感的原因,就是這個瀕臨死亡的經歷,使兩個人突然從「習以為常喧囂的日常」中安靜下來,而另一個自己,那個必須在死亡的面前,才會赤裸坦承的自我得以發聲。
回過神來,我們生命的真相,一直都有一個尖銳的刀劍抵住胸口,藝術家因為意識到此一生命的真實而創作,在兩者之間,同時呈現生與死之真實。為要更真實的活著、更真實的創作—還有更真實的去愛。
日間演奏會是特別的。從喧囂的白日開始,進入白日夢般的精神領域,但是演奏會結束之後,走入外面白晃晃的世界,你忽然覺得,剛剛那些在精神上翻天覆地的革命彷彿沒有發生過,一切如常,前一刻如此真實的事物已然消失無蹤。甚至會有一種不知如何活下去的茫然感。
在那個時候,如果有一個知道你此刻所在的狀態的人,溫柔的握住你的手,如果有這樣的人存在,那應該是可以一起度過一輩子的對象吧;可以一起度過感覺虛假的生活、一起面對太過真實的死亡。
這個故事適合一邊聽著有些感傷的吉他一邊閱讀,不只是因為故事裡的主角是吉他手,而是吉他的旋律與音色,無疑是這個故事的基調。
平野啟一郎的小說具有很濃的音樂性,他的另一個作品「那個男人」裡也有許多關於音樂的描寫,令人印象深刻。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文字與故事的旋律。
書寫的時候我也習慣聽音樂,一邊思索著想寫的東西,一邊尋找適合的「聲音」。是不是因為文字雖然不同於語言,似乎是安靜的,但是在安靜當中,也有自己的「聲音」。
有的時候就是需要那個「聲音」,才能打開心裡故事的旋律。
最近讀的小說,石黑一雄的「夜曲」,序的作者本身也是小說家的吳明益,建議讀者們可以一邊聽書裡提到的歌,一邊閱讀。
實際上讀了夜曲就明白為什麼了,因為這裡面每一個故事,都是從歌裡創作出來的:《By the Time I Get to Phoenix》、《I Fall in Love Too Easily》、《One for my Baby》⋯
以這些歌為中心,作者以文字編織故事,這是由音樂誕生的故事與文字。
據說石黑一雄在寫「長日將盡」時,是聽了Tom Waits的「Ruby’ arms」,而決定了小說的結局,故事的基調在說,我們的人生就是會失去一些真正珍貴的事物,而毫無挽回的機會。這些是本來可以不必的,但也是命定的失落。
平野啟一郎的「日間演奏會散場時」,蒔野和洋子最後還是在一起了。但我不知為何覺得,這並不是作者在創作起初所預設的結局。我覺得作者原本想寫的,應該是像石黑一雄的「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那樣的故事。蒔野與洋子錯失了對方,成為彼此生命中無法放下的核心。
如果蒔野和洋子終究沒有重逢,這會是一個比較好的結局嗎?我只知道,那一定會使這個故事,成為另一種調性的歌。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