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明取態、藝術節制、成就解鎖——與卓亦謙、盧鎮業談《年少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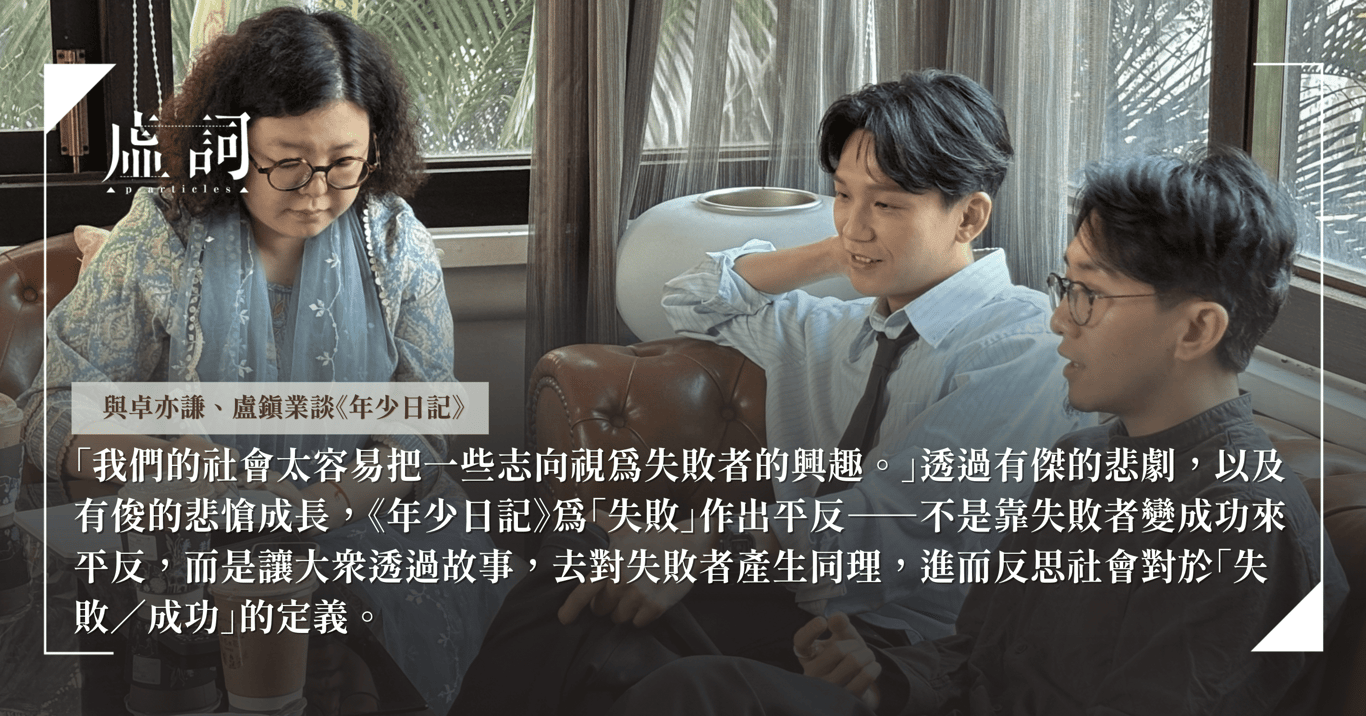
文|鄧小樺
《年少日記》(下稱《年》)走到今日,香港票房已逾二千七百萬,台灣票房也成為電影公司歷來最賣座電影,摘下金馬獎「最佳新導演」及「觀眾票選最佳影片」;並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十二項提名,團隊正赴各地電影節巡迴放映。看到電影能平安獲得各樣佳績,總算放下心頭大石;猶記得初在台灣看到電影時,哭到口腫鼻腫之餘,更曾莫名其妙地擔憂——是怕這個年頭,愈美好的東西愈可能遭遇不虞。當時不敢多談,當沉默是一種祝福。想來我也有隱藏的PTSD。
推動議題而非消費生命
香港近年多有關懷弱勢社群與社會問題的電影,正常來說這類電影的重點,在票房以外,更重引起社會談論與關懷,推動社會人心與制度的變革。《年》觸及兒時創傷、成長壓力、家庭關係與學童自殺問題,最後一項尤其是近年頻繁出現、揪動人心而未能好好處理的社會現象。由於擔心引起漣漪效應,在媒體上談及自殺一向存有禁忌,這也是我擔心之處。我在台北也向卓亦謙及盧鎮業坦言自己的擔心,而卓亦謙則直言(他應該想過這個問題千百遍了),他認為不討論才是問題的根源,不討論才會令事情變壞。這個鮮明大膽的立場與取態,我想就是電影力量的關鍵。
而盧鎮業,則很微觀地了解並參與事情的整體:他談及他的藝術治療師朋友GIGI,看了電影之後,在自己關懷心理健康的IG頁面,組織了多次分享的深談工作坊,讓到來的朋友坦誠分享——一切恰如其份,沒有失控,想談的人一起談,想找人分擔的人找到願意分擔的人——彷彿電影中的鄭sir找到一同肩負關心學生的同工。電影與現實之間,也確能有美好的互動。
卓盧二人同樣非常關心「消費議題」的問題,不,卓亦謙使用的措辭更為強烈,他說「如何才不是消費了死者」。我想「消費」的意思並非指事件中有人得到名利或滿足,而是在於參與者如何付出自己的心力與情感;同時關注不止停留於表層或一點,而是尋求深掘與擴散;目的同時包含思考他人的福祉。聽著卓盧二人滔滔的談論,我想他們確如自己所言,「守住了那個立足點」,絕非消費議題或任何人——而看過《年》的人,也可被感染而做得到「拒絕消費」。

鮮明大膽的取態
《年》成功引起大量討論,綜觀各處影評和觀後感,似乎年輕一代對於電影有著最強烈的認同,而年長的父母輩則多有稍嫌鄭氏父母的角色營造不夠完整,心理轉折交代不夠清晰;而像夾在中間的中年一代的筆者,則更多地接近鄭sir的所思所行。如此看來,可否說《年》是鮮明地站在了年少的視角,對於成年人及社會成規提出控訴?
卓亦謙的取態永遠是鮮明斬截的,像認識他的陳偉霖william 所形容,「講得很少,但整個人都是核爆的能量」。他提出的論點(也是電影的論點)有二:一是,許多人年少時受到家庭、學業、社會等壓力,被迫放棄自己的興趣,以致許多人長大之後,就算很成功成為專業人士,卻不知道自己最想做的是什麼,也不懂表達自己的感受,人生是蒼白的。「我們的社會太容易把一些志向視為失敗者的興趣。」透過有傑的悲劇,以及有俊的悲愴成長,《年》為「失敗」作出平反——不是靠失敗者變成功來平反,而是讓大眾透過故事,去對失敗者產生同理,進而反思社會對於「失敗/成功」的定義。
另一個重要論點:自殺的成因是複雜的,不能單一概括為某一原因。卓亦謙言及看見媒體報導自殺是「為情自殺」、「一時衝動」等,都覺得把死者平板化了、「不是這樣的」。他說來有種由衷的忿然。卓亦謙在多個訪問中都有提及,他自身的重度憂鬱經歷,及友人的自殺故事。我想他的取態,有著自己的獨特角度,是不願自己及友人被抹平——被抹平,然後就是遺忘。遺忘之後,就是悲劇的重複發生。我記得游靜寫過,你以為墜落地上一灘血身首分離才叫死嗎?不是,一個個人在城巿裡沒有靈魂地刻板生活,也是一種死。
(訪問時我又遲到了——在梯間與未曾相識的卓亦謙擦身而過。我記得他身上散發出,一種垮掉過的氣息。垮掉過的人可以嗅出來。)
而卓亦謙說,電影並非要控訴任何人,而是思考的是活下去的人如何活下去。不遺忘、帶著創傷而活下去,可能嗎?卓亦謙說,他自殺的友人留給他一封信,讓他多活了十年,才有《年》的出現。


卓亦謙的節制也是拯救
雖然電影賺人的熱淚加起來可以製造一場海嘯,但我最留意的卻是電影的節制。雖然傳聞導演自己在片場幾乎每場戲都哭,但在整個悲劇性強的故事結構之下,電影的語言卻是節制的,難以察覺到什麼強制催淚的手段。卓亦謙剪走了許多哭戲,也把鄭氏父子在醫院中牽手的戲剪掉了,都是出於「覺得夠了」,避免煽情。卓亦謙說他完全沒有思考如何要讓觀眾哭,「唯一用心想的是那個轉折,因為覺得需要一個扭轉的力量。」的確,需要意想不到的一下子,讓苦難的真實降臨到觀眾頭上,與劇中角色心情同步。
我提到其實最可怕的是日常發生的家庭暴力,鄭中基飾演的鄭正雄在家裡暴躁打妻子打孩子。前景聚焦有俊在飯廳做功課,後面客廳是有傑被暴打哭叫沙發亂跳,震撼卻模糊。卓亦謙微一沉吟,說那根本是有傑和有俊的日常,「不用放大頭的,日日都係咁架;但阿媽話佢偷嘢,是唯一一次,是特別的,就要大頭。我總是提醒自己,要回過頭來,看每一場戲在整部電影中的位置,有沒有太重或是太輕,必須從整體來看。」在卓那微一沉吟的眼神中,流露出非常理性的藝術思考,冷靜毫無情緒。我馬上理解到,他一開始所說的,藝術拯救了他。那是極端張力拉扯之下,造成的平衡。

盧鎮業成就解鎖的秘密
像我這樣迷戀平衡與節制的人,最喜歡的一幕是鄭SIR看見網上留言有人批評自殺者懦弱、不為他人著想,本來憤怒地要留言大罵「你班仆街有無人性」,轉念還是DELETE,用語音輸入提出正面的反駁:「抑鬱不是一種選擇,他已經沒有自理能力,還要求他想及別人感受,你們會不會太過苛刻?」由粗口到書面語,由罵人到反詰,這裡呈現了一種由互相抛擲情緒的發洩到提出論據來達致反思的提升,也讓電影提出一種正面的討論力量。而因為是語音輸入,連逗號和問號都會唸出來,反而加強了力量,可稱是目前最正面處理語音輸入這一新溝通形式的電影一幕。不過卓亦謙說,如果是他自己,會選擇激烈的表達方式。創作的拯救力量,有時在於讓創作者轉化為他人。
整部電影的節制力量,我想也要歸功於盧鎮業的演出,我當時已說至少可以得到最佳男主角提名。卓亦謙在別的訪問中曾有一個準確的形容,盧鎮業「有一種飄逸感」——但以往很少電影能捕捉到這一點。鄭SIR也不是特別藝術型的角色,但盧鎮業卻很好地呈現了一種創傷與沉思的氣質,內斂而具說服力,與電影灰淡的賦色融為一體。在天台上,鄭SIR望向一角,彷彿見到年少的哥哥有傑望向自己,那個有點迷離的複雜眼神,我覺得是盧鎮業從演以來最深刻的一個眼神。而內幕是,那場戲裡本來還有陳漢娜,但最後剪走了——二人都將那個鏡頭與眼神的成功,歸功於突然吹過的一陣風。
從以往跟盧鎮業的私人聊天中,他說過自己是以「減法」演出的,即是削去不需要的枝節,傾向內斂與集中。而眾所周知,盧鎮業素來真誠而努力,卻常和電影存在微微的脫離感,他有進入角色,角色卻未能全然融入電影,好像永遠微微的搖晃著。不過在《年》中,盧鎮業的鄭SIR卻是完全融入電影,甚至帶領電影的氛圍與說服力。盧鎮業在許多訪問中都說過,這是因為《一念無明》的導演黃進,跟他分享了一些黃進自己上演技課所獲得的心得及知識,讓沒有系統地學過演戲的盧鎮業覺得茅塞頓開。「他說,只要你真誠去演,演技再拙劣都會好看的。重點是,真心地成為那個人。『真心地成為那個人』並不是把自己以往的經驗代入劇本(這本是許多演員的慣常做法),例如並非把自己小時候被爸爸打的經驗代入,那只是你用回自己的經驗、做回自己,而且這種自我挖掘會『收唔返』。」盧鎮業深覺有理,便從這裡開始思考演繹鄭有俊。
「結果我想起了,小時讀的馬克思的一句話: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我心想屌咪就係咁囉!」盧鎮業指出,鄭SIR 本身其實不知道自己想怎樣,角色本身是創傷而迷茫的;要把握這個角色,就要進入他的社會關係的總和,不止是童年的他,還有他童年與所有人的關係,他當下的職業以及與學生的關係,他與妻子的關係,他被所有這些社會關係夾在一起,這才是他的內在。這是一個非常巧妙的過程:拉遠一點、宏觀一點,才能進入角色的真實內在。「有了這樣整體關係的理解,東西就自然出來了,不用再想加還是減、多不多、哭不哭,也沒有之後『無法出戲』的問題。」旁邊的卓亦謙說,這個真的沒有聽你說起過;盧鎮業承認是第一次對人講,然後指著我說,因為我知她會完全明白。
「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克思《費爾巴哈論綱》)說完的盧鎮業顯得極其輕鬆,由衷的快樂。一種所學者與所從事者終於接合的快樂;他的臉上有著微微的光彩,那是突破了一個層次,超越一個峰嶺的快樂。成就解鎖,人馬座的盧鎮業,需要更高遠的存在才能如魚得水。我呼一口氣緩解自己的激動。勢估唔到是馬克思讓盧鎮業得到金像獎最佳男主角提名——馬大鬍子乾脆多做一步讓小野稱帝啦。


電影所打開的討論空間
近日中大醫學院發表歷時五年的青少年精神健康調查,發現有四份之一的受訪者有嚴重抑鬱的癥狀,而來源主要是學業壓力。這呼應了《年》中提出的,對精英主義社會價值觀的反思,刻不容緩。《年》從時下青年的角度,提出了不少提醒,值得記住:要學懂表達自己的感受;不要對抑鬱者隨口講加油;不要指示,不要指望自己幫憂鬱者解決所有問題,重要的是「陪伴」,這就是最重要的承擔感。我們曾經為了他人的自殺而產生過一種奮不顧身的承擔感,願意四出奔走去尋找他們,或者有些人還會記得。電影中鄭SIR被學生遺書所觸動的一句話是「我不是甚麼重要的人」,而回答這句話,似乎需要一把外在聲音,說我重視你,你無論如何都是重要的人。
回到《年》,我當時就覺得這部電影會帶來相當的成功,曾想著問卓亦謙與盧鎮業,你們現在是三十五歲和三十六歲,會不會對自己的角色、目標和社會責任有新的理解?覺得自己有什麼可能性?想做到什麼事?但後來認識卓亦謙的陳偉霖警告我,不要把太重的期許放在卓亦謙身上以免壓垮他,別當他成功人士。的確,這電影的重點不是成功,而是對失敗者的關懷。《年》在港上映十餘週,希望大家都能記住電影所打開的討論空間:我們可以好好談論自己的感受,可以不用強迫自己加油,可以被深深重視,也可以關懷他人的生命並表達承擔。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